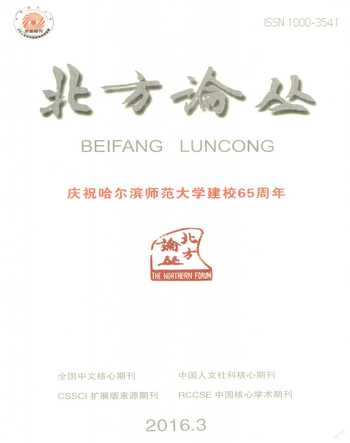“高郵二王”學術再討論
吳明剛
[摘 要]任何學術流派都有其相當影響,且獨樹一幟的學術內容和被同行學友、門人等擁戴的標志性人物。揚州學派的代表人物“高郵二王”(即王念孫、王引之)于音韻、訓詁、校勘的成就,足掩前哲,竦桀時代,成為一座學術高峰。其學術淵源來源于乾嘉漢學,特別是直接衍承其師戴震;其治學宗旨為“實事求是,研經求道”;其學術風格為“求真務實、勇于創新、恥于蹈襲”;主要的學術表征是“實事求是,無征不信”、“廣博精深,綜貫會通”、“好學深思,創新兼容”。“二王”的學術思想、學術淵源、學術風格、學術表征引領時代,成為時代的風向標。
[關鍵詞]“高郵二王”;學術思想;學術淵源;學術風格;學術表征
[中圖分類號]K24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3541(2016)03-0089-04
中國傳統之學術,雖然范圍很廣,但始終處于核心地位的是對儒學經典的研究。自漢武帝立五經博士,授今文經學,劉歆欲以古文經學立于館,便有今古文經學學派之論爭;自東漢馬融、鄭玄等以文字訓詁為主治經始,便有了治經的不同學術形態,至宋明而理學,清代而樸學。清代學術“吳學最專、徽學最精、揚州之學最通” [1](p.213),揚州之學以“玉裁、念孫、引之最能廣大震學”[2] (p.145)。乾隆六十年(1795年),古學日起,“高郵王黃門念孫……倡導其始” [3] (p.288),“小學則若膺及足下父子”[4] (p.98),“高郵王懷祖公正通達……大約王為首”[5] (p.57)。王氏“卓絕一時,而獨開百年來治學之風氣者也!”[6] (p.234)長沙后學何澤瀚贊云:“不皖不吳獨開一派,是父是子同有千秋。” 可見, 學林之中,高郵王氏(王念孫、王引之)最為翹楚,公推領袖,王氏父子,眾望所歸。其學術成就值得總結,學術淵源、學術旨歸值得探討,學術風格、治學方法值得學習。
一、“高郵二王”的學術成就與淵源
王氏父子皆自幼篤志于學,勤奮讀書,學問功底極為深厚,在諸多學術領域成就突出。
文字學方面。段玉裁《說文解字注》雖以文字兼聲音、訓詁,發明許書條例,研究詞義演變,將許學推向高峰,其澤甚遠,然而,王念孫的文字學功底也不在段氏之下。王念孫文字學成就主要集中在研究《說文》,其成就有:《讀說文記》一卷,《說文諧聲譜》一卷,《說文段注簽記》一卷,《說文解字校勘記》一卷,《桂未谷說文系統圖跋》一篇,《段若膺說文解字序》一篇,代朱筠《重刊說文解字序》一篇;《康熙字典考正》12卷(與王引之合撰),《漢書古字》一卷,《漢隸拾遺》一卷,《群經字類》二卷,《宋質夫印譜序》一篇。
音韻學方面。王國維說:“自漢以后,學術之盛,莫過于近三百年”,而“古韻之學,自昆山顧氏而婺源江氏,而休寧戴氏,而金壇段式,而曲阜孔氏,而高郵王氏,而歙縣江氏,作者不過七人,然古音廿二補之目,遂令后世無可增損。”[7] (p.453)將高郵王氏列入清代古音學卓絕七大家之一,足見其在音韻學上的地位。
王念孫的古音學成就主要見諸于《古韻譜》和其子王引之《經義述聞》卷三十一,分古韻二十一部(晚年《合韻譜》更別“冬”于“東”,為二十二部)[8] (p.2)。王氏之特色在于“分古音為無入、有入二大類,與戴、孔二君同,而不用其異平同入及陰陽對轉之說。分支、脂、之為三尤、侯為二,真、諄為二,與段君同,又以尤之入聲之半屬侯,與孔君同。而增至、祭二部,則為段、孔二君之所未及。”[9] (p.87)王國維比較王念孫與江有誥分部之異同,指出二者很相近,認為古韻分部至王、江二家,二十二部之說已極周密(今天研究證明,王觀堂之說雖有局限,然從考古方法分部,王、江已極周密,仍具有一定道理,其余皆蛇足了)。
反映王氏古音見解的還有:高郵王氏遺稿《詩經群經楚辭韻譜》《周秦韻譜》《西漢韻譜》《詩經群經楚辭合韻譜》《周秦合韻譜》《西漢合韻譜》《諧聲譜》等,扎取經典中的韻字于同韻合韻字。其遺稿價值“五家之書(顧炎武、江永、戴震、段玉裁、孔廣森)先后行世,獨先生說,學者謹從《經義述聞》卷三十一所載古音二十一部表窺其崖略。今遺稿燦然,出于百年之后,亦可謂學者之幸矣。” 其治學“先生之精密,要在戴、段二家之上也。”[9] (p.78)
反映其古音研究成果的資料還有:《疊韻轉語》;書信,如《與李方伯書》《與段玉裁書》《與陳碩甫書》等;序跋,如《六書音韻表書后》《重修古今韻略凡例》《書錢氏〈答問〉地字音后》等;學術專著,如《廣雅疏證》10卷、《讀書雜志》80卷、《經義述聞》15卷、《經傳釋詞》10卷中涉及的古音文字資料;弟子和后學的著述,如王國維《補高郵王氏〈說文諧聲譜〉》、宋小城《諧聲補逸》、劉盼遂《高郵王氏父子著述考》等。要言之,音韻學方面,王念孫古韻二十二部說,細密合理,使清代古韻學定于一尊;確認古音二十三紐說,見解卓識;四聲之說,成一家之言;音轉之論,響澤后世。
訓詁學方面。高郵王氏之訓詁事功顯赫,無與倫比。“小學之中,如高郵王氏、棲霞郝氏之于訓詁,歙縣程氏之于名物,金壇段氏之于《說文》,皆足以上掩前哲。”王氏父子位居榜首。“如果說段玉裁在文字學上坐第一把交椅的話,王念孫則在訓詁學上坐第一把交椅。”[10] (p.386)
《廣雅疏證》10卷,念孫殫精竭慮,化十年心血撰成,又有名作《讀書雜志》80卷;其子王引之繼承家學,撰作《經義述聞》15卷、《經傳釋詞》10卷,此高郵王氏父子四大著作。《廣雅疏證》在《高郵王氏四種》中最為精密,“其發明以聲音穿串訓詁之法,則繼往開來,成小學中不祧之柤。”[11] (p.143)乃“中國語言學史上一大轉折點的標志”[12](p.87)。《經義述聞》在糾正前人誤釋方面,成就空前,薈萃了校經的成果。清人方東樹說:“高郵王氏《經義述聞》,實足令鄭、朱俯首。漢唐以來,未有其比。”[13] (p.45) “凡古儒所誤釋者,無不旁征曲喻,而得其本義之所在。使古圣賢見之,必解頤曰:‘吾言固如是,數千年誤解之,今得明矣。”[14] (p.4) “今日讀王氏父子書,只覺其條條皆然有當于吾心。前此之誤解,乃一旦煥然冰釋也。”[2](p.27)《經傳釋詞》作為一部系統研究上古漢語虛詞詞典,備受推崇,公認為古漢語虛詞研究的巔峰之作。阮元作序贊道:“恨不能起毛、孔、鄭諸儒而共證此快也。”[15] (p.167)其編撰方法和獨到的見解,后世學人無不視為圭臬。《讀書雜志》對先秦兩漢常見的子史做了精密的校勘,為“校釋群書的典范之作”[16] (p.7),后世學者就校訂諸子整體而言,無出于念孫之右。王國維說:“治經,首先要讀高郵二王四大著作。”[17] (p.67)其“本非經學,而為史學,其治諸經,以經傳為古史料之淵藪也。”[18] (p.87)這種卓越斷識是對高郵王氏的睿識,確實高人一籌。
高郵王氏的成功足掩前哲,竦桀時代,成為一座學術高峰,其學術淵源直接源于乾嘉漢學,特別是家法師承,直接衍承皖派戴震。清代學者劉壽曾說:“戴氏弟子,以揚州為盛。高郵王氏,傳其形聲訓詁治學。”[19] (p.214)王氏先祖素貧,以詩書起家,其父王安國嚴謹方正的家風奠定了高郵王氏的顯赫地位。念孫尚幼,父便教之以句讀、章句,奠定了他堅實的幼學基礎;骨立嚴正的品格,對他影響也極大。王念孫教子也是“幼朱子、小學,長以經義” [20] (p.46) 。其次,父子二人是在名重一時的經學大師熏陶下,步入治學門庭的。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念孫12歲便受業于戴震,在文字聲音訓詁方面,接受了戴氏嚴格訓練。至于王引之,是推廣庭訓,傳其父學的,同時又受業于長他兩歲的阮元。阮元聰慧,學識淵博,又受業于王念孫。他們之間是父子相傳,師弟相授,治學門徑是相通的。世代相傳,師徒相授,一門群從,皆治古學,良好的環境,成為“二王”取得輝煌成就的基礎。
“二王”取得輝煌成就也是時代的惠予,古音學的發展是乾嘉語言學興旺發達的決定因素,古韻學至“高郵王氏”時已建立起一套科學完整的體系。
早在宋末元初戴侗就已經闡述古音與古義的關系,指出:“訓詁之士,知因文以求義矣,未知因聲以求義也。夫文字之用莫博于諧聲,莫變于假借,因文以求義而不因聲以求義,吾未見其能盡文字之情也。”[21] (p.243)明末方以智也說:“欲通古義,先通古音。”“因聲求義,知義而得聲。”[22] (p.189)清戴震說:“疑于義者,以聲求之,疑于聲者,以義正之”、“因聲而知義”。后來,朱筠、錢大昕、段玉裁受到影響,接受了這些觀點,到了乾嘉解決古音問題完全成熟。顧炎武之后江永分古韻為13部、乾隆中段玉裁分17部、王念孫分古韻22部,戴震、孔廣森古音對轉理論也出現了。古音問題基本解決,這一成果立即被運用到古義研究中來,從此,因聲得義才有了可靠地科學的依據,到乾隆后期,嘉慶年間才產生一批訓詁名著。查考這一過程可知,乾隆時期語言研究的主要成就是解決上古音的問題,嘉慶時代語言研究的成果主要是古義方面。沒有乾隆年間古音問題的解決,就沒有嘉慶時代的訓詁成果。先治古音,后治古義,這個過程正是順應當時古漢語研究的規律。順應了這一規律,并按這一規律辦事,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正是在這種條件下, “高郵二王”自覺、主動地覃究古音,又溝通訓詁,開拓了訓詁學的新境界,從而完成了一次偉大的超越。
二、“二王”的學術宗旨與風格
針對經學的荒疏,乾嘉時期,以惠棟為代表的“吳派”搜集漢儒經說,加以疏通證明,“惟漢是信”,率先倡導以求古義的辦法來克服宋人的玄言解經,把“信古”作為“求是”之路。“一尊漢經”是他們的學術宗旨。以戴震為代表的“皖派”打出“實事求是”的旗幟,尖銳而有力地批判了“吳派”墨守漢儒的“求是”之弊。戴震說:“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君子務在聞道。”“我輩讀書,原非與后儒競立說,宜平心體會經文。”亦即從經典原文入手,探索經典原始之義理,恢復儒學原始之形態。又說:“經自漢經師所授,已差違失次,其所訓釋,復各持異解。余嘗欲搜考異文,以為訂經之助;又廣探漢儒箋注之存者,以為宗考古訓之助。”戴震重視漢人成果,但只將其作為自己研究經書的資料工具,從而開啟乾嘉樸學真正的“實事求是”的學風。“皖派”的宗旨是“求是”。揚州學派是繼吳、皖兩派后,同樣從事純漢學研究的地域性學派,由吳、皖分化演進而來,其學術宗旨和治學風格有所衍承。戴震精通小學、歷算、地理、名物,又講義理,倡導由小學而通經明道。他說:“經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詞也;所以成詞者,字也。”揚州學派的代表人物王念孫,少時師從戴震學習經義,接受文字、音韻、訓詁的訓練,樹立了治“許鄭之學”,考文字、辨音聲的志向,認為“訓詁聲音明而小學明,小學明而經學明”。其子王引之受父親影響,在《經義述聞》借用其父云:“說經期于經義而已,前人傳注不皆合于經意,而參之他經,證以成訓,雖別為說,亦無不可。必欲專守一家,無稍出入,則何邵公之墨守見伐于鄭康成者也。” 王引之反對“株守漢學而不求其是者”。 可見,“高郵二王”衍承了其師戴震的觀點。綜觀“二王”治學的實踐歷程,我們可以看到,“二王”治學宗旨無不“實事求是,研經求道,探討經典原義”。
“求真務實”的具體表現就是“反對鑿空,反對墨守”。從語言的實際出發,反對空談性理的“鑿空”,這是對歷史的清算;反對“墨守”,這是對現實的一場斗爭。“鑿空之弊有二:其一緣詞生訓也,其一守偽傳謬也。緣詞生訓者,所釋之義非其本義;守偽傳謬者,所據之經非其本經。”[23] (p.143) “二王”在實踐中公然提出有的經文非“本經”(文字錯誤),有的訓釋非“本義”(指經書原義)。清算古義研究積弊,掀起了思想解放的潮流。反對墨守主要指向是同時代的吳派。章太炎說:“吳派篤于尊信,綴次古義,鮮下己見;皖派分析條理,皆縝密嚴瑮,上述古義,而斷以己之律令。”“二王”不是“墨守漢學”而是“漢宋兼采”;不是“求古”而是“求是”的風格。對吳派“墨守”的批判,戴震開頭,段王上陣。王念孫說:“世人言漢學者,但見其異于今者則寶之,而于古人之傳授,文字之變遷,多不暇致辨。”[24] (p.89)
以小學溝通經學,破解經學許多難題。讀書萬卷,不作簡單的材料匯集,分析,歸納推理,進行真正的科學研究,得出新的獨到的見解,在于“二王”勇于創新的精神風格。宋以降,學者都強調“尊德性而道問學”,但都有所偏,或偏尊德性,或重道問學。“二王”則兩者兼之。德性方面,首先勤政,廉政。念孫作山東學政,“整飭士習”;永定河道的債務,引之代父還15年。其次,家風好,學風正。念孫六十,妻子病故,近三十年決然獨處,一心著述。王氏在自己的研究中,凡與他人暗合之處必將刪去,得于同學亦必說明。他在《史記雜志敘》中說:“與錢梁同者,一同刊削。”在《漢隸拾遺敘》云:“推求字畫,凡宋以后諸家所及者,略之,有其字而未及之及與誤指為他字者補之。”王氏的作法,令人敬佩。
三、“高郵二王”學術的主要表征
“表征”是指人或事物顯示出來的現象或表現出來的特征。我們可以從思想、精神、態度、方法等方面考察。尤其是方法中表征最多。思想、精神里邊有態度,也有方法,反過來,從態度、方法里也可見思想與精神。“二王”的學術表征很多,主要表現如下。
“實事求是,無征不信”是“二王”學術最主要的學術的表征。“實事求是”是乾嘉學者共同的學術標準。王氏父子眼中凡是“求是”必以“實”,必作價值上的“是非”判斷和實事之“是”的評判,無征不信。翻開王念孫的《廣雅疏證》,我們常常會看到他在糾正眾多的誤說。王念孫批評偽孔傳《尚書》的注釋,糾正《詩經》毛傳、鄭箋、孔疏的誤說,駁解《楚辭》《隸釋》的誤釋,駁證《史記》《漢書》的誤釋,連《說文》也不是不一味盲從。于所不知,不強作解人,也不隨意猜度,暫付闕如。王氏不僅刻薄古人,對時賢之說,若屬謬說,不留情面,如前輩顧炎武,老師戴震,時賢惠棟、錢大昕、段玉裁、程瑤田、劉臺拱、李惇、畢沅、藏用中、陳望樓、孫星衍、盧文弨等。梁啟超說:“如高郵父子者,實毛、鄭、賈、馬、服、杜之諍臣,非其將順之臣也。夫豈惟不將順古人,雖其父師,亦不茍同。”[2](p.91)對經典文獻而言,恢復本義為“求是”。一字的本義最精確無蔽,最能精確地反映實事或實相;古人用字亦常借用,后人欲明其意,常求真實用字,故“二王”常不惜大量篇幅,求本義,明假借,推訓明古,以探本溯源。《經義述聞》為求其“實是”,王引之必“一事必剖解精密,一義必反復推求,一例必輾轉旁通”。對于名物制度,天算輿地乃至草木蟲魚等等亦必正之。王念孫作《廣雅疏證》時,即“將花草竹木,鳥獸蟲魚,皆購列于所居,視其初生,以校對昔人所言形態。”[25] (p.176)《廣雅疏證》第十卷即《釋草》以下諸篇為王引之所撰,涉及草木蟲魚,他“若非參酌前人,得之目驗,則不易辨明”。此乃“實事求是”而已。
“廣博精深,綜貫會通” 是“高郵二王”最為顯著的第二個表征。“廣博”形容知識面寬。王氏父子博覽群書,貫通經史,融匯百家,各種類書,無所不窺。“精深”形容學問細致、嚴密。王氏做學問,用心及其微密。在他們的著作中,常會看到“凡言”“遍考”之類的話。沒有廣博的知識,縝密的思維,怎敢輕言。現代學者張舜徽說:“吳學最專,徽學最精,揚州之學最通。無吳、皖之專精,則清學不能盛,無揚州之通學,則清學不能大。”[1] (p.178)所謂“會通”,即不執一端,融會貫通。其中包含三層意思:一是博理群書,以求考據與義理的貫通;二是突破傳注的藩籬,以求學術領域的匯通;三是破除門戶之見,以求漢宋的融通。“二王”作為揚州學派的代表,在文字、音韻、校勘、辨偽、輯佚等方面,取得總結性的成就,如果“二王”學識不通達,不貫通,不可能將乾嘉漢學進一步推向高峰。王念孫根據以聲求義的原則為《廣雅》疏證,訂正了千余處錯誤;在校勘的基礎上,“舉漢以前倉雅古訓,皆搜括而通證之”。其《讀書雜志》82卷,校《淮南子內篇》《戰國策》《史記》《管子》《晏子春秋》《荀子》《逸周書》《漢書》《墨子》《漢隸拾遺》等古籍,“一字之證,博及萬卷”。 王引之“自九經三傳及周秦兩漢之書,返助語之文,遍為搜討。”[15](p.97) 這樣的成績,沒有廣博的知識、“會通”的能力是不行的。汪中“論次當代通儒僅八人”,而王念孫、王引之在其中。
“好學深思,創新兼容”是“高郵二王”最為顯著的第三個表征。“好學”包括讀書和親身實驗。“深思”就是能推理、概括,能用縝密的邏輯思維。“創新”,即前無古人,自創新例。即要有新的方法,新的見解,發凡起例,啟迪后人。高郵王氏父子一生束發研經,虛無度日,殫精竭慮,飽讀經書。二人“好學深思,探求規律,發明義例”。正是在這種思想指導下,能突破字形窒礙,運用“音近義同”的理論探求語源,示人大路,為語言文字研究揭開新的一頁。他們“擘肌分理,剖豪析藝”,探索出新的思路和方法。王念孫擅長歸納推理,他在《廣雅疏證》中指出:“夫雙聲字,本因聲以見義,不求諸聲而求諸字,固宜其說之多鑿也。”[26] (p.268)又說:“大抵雙聲疊韻字,其義存乎聲,求諸其聲則得,求諸其文則惑矣。”[26] (p.190)這是對規律的總結。段氏在《周禮漢讀考》發明三例:讀如、讀為、當為。“自先生此言出,學者凡讀漢儒經、子、《漢書》之注,如夢得覺,如醉得醒。”[27] (p.432)《經傳釋詞》在訓詁方法上,對句法、倒句、互文、對文(相對為文)、對言、散言、連文、連言進行用例歸納;用“凡、凡言、若、若……之類、仿此(放此)”等術語進行總結;通過“讀若、讀入、如字、之言、或作、又作亦作、古同聲、古同聲而通用、古字通、聲相近、聲近義通、聲近義同等術語說明音義互求。這些通例的總結,使其成為古漢語虛詞研究之圭臬。王氏之創新還表現在對前賢的注疏不專守一家。若諸說并列,擇善而從;若皆不合經意,則另作新解,博引他書以正之。新解在二王著作中俯拾皆是。如《經傳釋詞》卷二“謂”字條下四個義項,皆新解。其中第三個義項:“謂,猶與也。《史記·鄭世家》:‘鄭文公恐,不敢謂叔詹言。”《詩經·衛風·芄蘭》:“雖則佩觹,能不我知。”“能”當讀為“而”,二者古音近,義相通。這些注解讓人驚訝,耳目一新。《戰國策·觸詟說趙太后》究竟是“觸詟”還是“觸龍”,自古爭之。王氏考證為“觸龍”,為當代考古發掘所證明。 “二王”能夠超越前人,超越同時代,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他們不僅“好學”(能占有材料),而且會“深思”(能概括推理),還能找出規律,有新的發現。
渾言之,作為揚州學派的代表人物王念孫、王引之在音韻、訓詁、校勘方面獨樹一幟的學術內容,成就足掩前哲,深受同行學友、門人等擁戴,其才力影響到后學孫怡讓、俞樾,進而影響到章太炎、黃侃等人,澤備后世,竦桀時代。其卓越的學術思想、學術風格、學術特點值得研究和借鑒。
[參 考 文 獻]
[1]張舜徽.清代揚州學記[M].揚州:廣陵書社,2014.
[2]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3][清]焦循. 雕菰集·卷二一·李孝臣先生傳[M].道光十三年.
[4][清]汪中著,田漢云點校, 新編汪中集·第五輯·致王念孫書[M].揚州:廣陵書社,2005.
[5][清]阮元.國粹報·二九期·答友人書[J].國粹學報館,光緒三十三年.
[6]楊樹達.詞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7]王國維.王國維先生全集·周代金石文韻讀序[M]. 臺灣:大通書局影行,1976.
[8]陸宗達.語言學論文集·王石臞先生韻譜合韻譜遺稿跋[M].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6.
[9]王國維.觀堂集林·高郵王懷祖先生訓詁音韻書稿敘錄[M].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
[10]王力.中國語言學史[M].北京:中華書局,1996.
[11]黃侃.黃侃論學雜著[M].北京:中華書局,1964.
[12]殷孟倫.王念孫父子《廣雅疏證》在漢語研究時尚的地位[J].東岳論叢,1980(2).
[13][清]方東樹.漢學商兌·卷中之下[M].望三益齋,同治十年(1871).
[14][清]王引之.經義述聞·序[M].南京: 鳳凰出版社,1982.
[15][清]王引之.經傳釋詞[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16]單殿元.王念孫王引之著作析論[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
[17]蔡思尚.中國近現代學術思想史論[M].廣州: 廣東人民出版社,1986.
[18]王國維.國學論叢·王觀堂先生學術·一卷三號[M].北京: 商務印書館,1927.
[19][清]劉壽曾撰.傳雅堂文集·卷一·漚宦夜集記[M].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1937.
[20][清]李元度. 四庫備要·史部·國朝先正事略·卷十六“名臣”[M].北京:中華書局,1998.
[21][宋]戴侗撰.六書故·六書通釋[M].西蜀李鼎元師竹齋,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
[22][清]方以智撰.通雅·音義雜論[M].北京: 國家圖書館,2009.
[23][清]戴震.戴東原集·古經解鉤沉序[M].上海:上海點石齋, 清光緒十四年(1889).
[24][清]王念孫.王石臞先生譯文·卷二·拜經日記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5.
[25][清]劉盼遂輯.段王學五種:高郵王氏父子年譜[M].天津:天津古籍書店,1982.
[26][清]王念孫.廣雅疏證·卷六[M].萬有文庫本,光緒二十六年.
[27][清]阮元撰,鄧經元點校.揅經室集·周禮漢讀考序[M]. 中華書局,2006.
(作者系四川民族學院副教授)
[責任編輯 張曉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