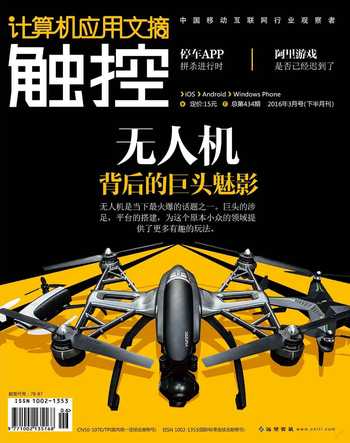移動醫療,未必全是正能量
大肚
掛號到底有多難?
在今年年初曝光的一個短視頻中,中國網民第一次全面了解了目前的醫療“新”難題:掛號。這不僅是體現在掛號難上,經“號販子”幾番抬價,原價300元人民幣的掛號費能漲到4 500元人民幣。當然,這只是在網絡上曝料的一例典型,至于互聯網之外到底有多少類似甚至是遠甚于此的情況,我們不得而知。
造成這種難題的原因很多,和監管不利、醫療資源相對集中以及民眾意識的偏頗等都有關系。據一份網絡調查的統計,參與調查的人中有90.91%的人會選擇先掛號再去科室,其中42.5%的人需排隊30分鐘以上。值得一提的是,參與調查的人中有75.91%的人認為“大城市、大醫院和掛名專家的醫生”是掛號首選。
從《2015年度掛號數據分析報告》中看,“全國醫院掛號排行榜”排名前十,北京就占了八成。以北京廣安門醫院為例,平均一天有11 000個門診,但醫務人員卻只有400人,門診量遠遠超過了醫院的最大負荷。然而北京全市醫院專家號全年不到180萬個,這就意味著99%的患者不能如愿掛上專家號。優質醫療資源過度集中,直接導致各大醫院的擁擠不堪。

不難看出,相對于民眾的觀念而言,醫療資源是遠遠不夠的。于是醫生“手動加號”便成了暫時緩解的辦法:在醫生的正常休息時間,通過手動加號來增加診療次數。但從實際情況來看,用“杯水車薪”四個字來形容這種辦法毫不為過,而且事實上,這也導致了醫患矛盾逐年激發的另一個誘因:“號販子”。
“號販子”與移動醫療
“號販子”的能耐到底有多大?在前段時間,中國青年網披露了一份記者的暗訪實錄。記者分別在北京、上海和廣州三地進行了調查,但無一例外都在“專家號已掛滿”和“網上預約無號”的情況下,從“號販子”手中高價買到了專家號。
實際上,在這三個城市中,“賣號倒號”已呈規模化,有系統的經營模式:參與加號的醫生與護士負責“出貨”,“號販子”負責尋找“客源”,其中收入是“出貨方”占大頭,剩下的是“號販子”的“勞務費”。
那么移動醫療呢?如今的相關APP實現掛號有兩種方式,一種是接入當地統一的掛號平臺,比如《微醫》在北京地區提供的部分網絡掛號服務,接入了北京地區的統一平臺114預約;另外一種是接入醫生加號的服務,比如《春雨醫生》和《一呼醫生》等提供的網絡預約掛號,就是來自醫生的手動加號。如前段時間央視就曾報道,有“號販子”利用《一呼醫生》搶到專家號后,再高價倒賣給患者。
移動醫療:黃牛養成記
在醫生不能手動加號后,苦的不僅是“號販子”,眾多擁有掛號業務的APP也會被波及。在最開始,移動醫療新創企業推出掛號業務時普遍有兩個方面的考量,一是可以放大稀缺的醫生資源,醫生可以用碎片化時間提供靈活的在線咨詢。二是通過APP把醫生和病人預約時間連接起來,極大減少患者在醫院排隊等候和停留的時間。
從初衷上看,移動醫療公司應該是“號販子”們的天敵。從“號販子”的各種手法中可以看出,最基本的一招就是利用信息不對稱,低價進高價出。而移動醫療采取的方式則是明碼標價,用戶能快速查詢并獲取。所以從表面上看,移動醫療相關APP的普及,會不斷擠壓“號販子”的生存空間,甚至最終讓“號販子”消失。
但實際上呢?
事實上,通過第三方醫療APP掛號加號,早已不是什么新鮮事。像好大夫、掛號網等互聯網醫療公司,在很早以前就開通了專家預約加號服務,也是明碼標價。但是,“號販子”這一個存在了10余年的隱形團體,也早已對這種方式熟門熟路,不僅有專人負責搶號,還有人負責聯系有手動加號資格的醫生與護士一起賺“外快”。
有業內人士指出,移動醫療公司開拓加號業務,實際上和現有的“號販子”做的事情極其類似。因為它既沒有改變就醫服務品質,也沒有優化醫療資源分配,最終只是和“號販子”一樣在利用醫生的“空閑休息”時間。唯一的不同,就是他們給“號販子”提供了一個更能獲取號源的平臺。
醫院“號販子”之所以能夠橫行10幾年,其根源就是優質醫療資源的供不應求,滿足不了龐大且日益集中的患者群體。所以從某個方面來說,“號販子”這職業是無法完全消失的—只要醫療資源不平衡帶來的問題依舊在,那么他們就永遠有生存的空間。而一些移動醫療企業的做法(掛號業務),則是相當于加劇了資源的傾斜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