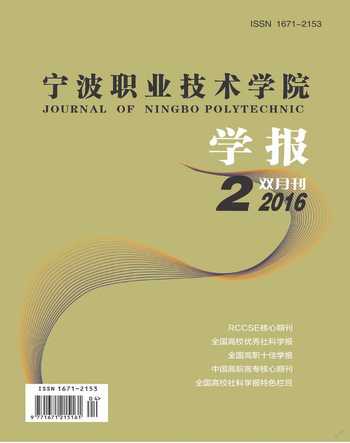全祖望的人生與治學新探
陸臻杰

摘 要: 全祖望是浙東地區著名的歷史學家,思想家。在短暫的人生道路上,他人生軌跡圍繞其祖籍寧波為中心南北顛簸,并且在治學上也以寧波作為其一大母題,揮灑文字,潑墨著書,為后世留下了彌足珍貴的甬上文化遺產。對全祖望的人生輾轉經歷與其治學母題做一探析,能夠深入理解謝山與寧波的關系。
關鍵詞: 全祖望; 寧波; 人生軌跡; 治學母題
中圖分類號: K207 文獻標志碼: A 文章編號: 1671-2153(2016)02-0077-05
一、引言
全祖望(1705—1755),字紹衣,號謝山,人稱謝山先生,浙江鄞縣(今寧波市)人。謝山治學嚴謹,為人正直,歷來為世稱頌。人們對于他的品格以及治學之道十分景仰及推崇,后人為其著書立傳頗多。在這些年譜或傳記中,尤以其友人之子董秉純所修的《全謝山年譜》最為精簡,是研究全謝山一生的第一手材料。此后,蔣天樞先生亦為先賢作傳,將先生一生概括為四個階段(1)。王永健教授的年代分期也大致與蔣先生所修年譜相似,對于全謝山四個階段進行客觀而公正的論述,展現了謝山坎坷而又豐富的一生,為我們研究謝山奠定了基礎。鑒于以上的研究,本文另辟蹊徑,擬將全謝山一生作為一個總體進行考察,通過重構其輾轉流離的人生軌跡,進行前后對比研究,以說明謝山坎坷顛沛的命運之路一直有其明確的指向和內在的牽引動力,同時知人論書,以剝離出謝山治學的母題,這就是他人生軌跡的空間指向——寧波。
二、以寧波為指向的人生軌跡
寧波是全謝山的人生羅盤的中心指向及其內在牽引動力。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謝山生于“寧波城內月湖西岸的白壇里,是明萬歷年間,進士及第,官至宮詹的全天敘的故宅。”[1]59十四歲以前,謝山就一直生活在這樣一個世代耕讀的書香門第之家,跟隨自己的父親吟園讀書識字,其父對子要求及其嚴格,培養了謝山今后兢兢業業,勤奮治學的良好習慣。自十四歲后的兩年中,謝山又受業于里中董正國先生的三馀草堂。“草堂帶湖濆,地僻繞梧柳。修竹蔭其東,清渠映其后,中安右圖書,琴棋列左右。”[1]64對于這樣修學環境,謝山一直念念不忘:“三馀草堂清離離,插架萬卷足自怡。”[2]2209完全被包孕于環境優美、人文濃郁的草堂內,專心研習功課,故而少年謝山的足跡幾乎游走于鄞縣的課堂與書齋之間, 醉心于諸子學問。
十六歲后謝山的人生指針開始發生偏轉,指向了鄞縣以外的“功名世界”,也拉開了他顛沛流離的人生。如圖所示(2),全謝山的一生中有兩次遠離家鄉的“遠游”,一北一南。 前一次是在杭州鄉試失敗后,為了再次中舉而進京趕考;還有一次是為了“生計”而顛沛于廣東肇慶。可是這兩次較大的人生軌跡震蕩并未使之絲毫偏離于寧波,卻更加彰顯了寧波作為其人生的中心指向。去往北京趕考發生于雍正八年,這時謝山二十六歲。此次北上,謝山不僅帶著母親而且“攜書二萬卷,兼車載之”,路途艱辛坎坷可想而知,不過雖然一路疲憊,也阻擋不住他欲望遠離鄞縣去往京城趕考的步伐,“行次山東,資斧告盡,以衣付質而行。”[3]36 青年全謝山對于考取功名寄予了較大的期望,故而他也力勸他的朋友能夠在仕途上有所作為。厲鶚本無意于應試。謝山則特別至書樊榭,力勸其應試“今樊榭為有司所物色,非已有所求而得之也。而欲伏而不見以為高,非中庸也。”趙氏兄弟是謝山在杭州遇到的好友,他也撰《與趙谷林兄弟書》,極力鼓舞他們應試:“今倘以賢兄弟當其選,堪為是科生色。”[2]351雍正十一年(1733年),謝山應北闈試于順天府,不料又不幸落榜。連帶杭州鄉試不中后,兩次落第,謝山準備打包袱回家。正在人生指向標再次引向寧波之時,謝山人生當中恩師李紱的出現,暫時使這一想法潛伏。李紱是當時的主考官,看到謝山的行卷后,大為贊嘆:“此深寧東發后一人也。”深寧是南宋時期著名思想家王應麟,而東發則是大儒黃震,兩人都是鄞縣人,將謝山與兩位大儒先賢并列,可見當時李紱對于謝山才氣的青睞。因此之故,李紱“固留”謝山,“使之應詞科”。[3]44乾隆元年,謝山三十三歲,在李紱賞識之下,那年他終于高中三甲三十六名進士,任職翰林院庶吉士,后又被舉薦博學鴻詞科。可是,當時主權派張廷玉以及徐本和李紱之間有相當的過節,何況謝山本人又相當“疏放”,故而必然對謝山甚為忌恨。在張廷玉和徐本的排擠下,謝山應試及第卻落得個“左遷”的下場。他徑直可以在散館后,作為外補去州縣做官,或者更加適合于在方苞的邀請下進入“三禮局”撰書立說,要知道京城所藏珍本善本就可以讓謝山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然而,謝山一封《奉方望溪先生辭書》[2]1753,對于京城學術氛圍大加撻伐,又不愿以自身之才屈就于其下。離開京城是權謀利益拒斥的客觀事實,也是謝山不愿以自身學術修為俯身求全的主觀愿望。至此,李紱的“固留”之后的“左遷”倒讓謝山更加堅定了辭京返鄉的決心,凸顯了家鄉作為其人生軌跡的中心指向。比及第一次“薄游京落”(3),謝山第二次“遠游”于廣東肇慶更為短暫,何況這次游離于鄞縣之外是因為廣東巡撫蘇昌的盛情邀請以及為“安身”而奔走。不過,對于人生坎坷之路,他還堅信:“雖然窮達命也,枯菀時也,而吾曹之所以自立者,非命之所能縛。”[2]1839乾隆十七年(1752年),他與受聘于粵秀書院的好友杭世駿一起趕路。到了肇慶以后,謝山還是積極融入到教學中去,與學生訪問名勝古跡,還探尋了明清易代之際南明桂王政權的駐蹕之地,感嘆道:“當年草草搆荒朝,五慮猶然斗口囂。一夜桂花零落盡,沙蟲猿鶴總魂銷。”[2]2296“九月,故疾復動。然少閑必與諸生講說學統之流派,考訂地望故跡,薄游光孝寺,寶月壇,登閱江樓、七星巖,皆有詩。又為諸生改定課藝百篇,刻之。又取博陵尹公所刻《呂語集粹序》而梓之院中,以廣其傳。”[3]155不過,本是多病纏身的謝山來到肇慶后,頑疾久而不愈,卻越來越嚴重。相比二十六歲時的血氣方剛,此時的謝山已經經歷了易變的世事及身體的摧殘,并未像在京之際是秉著“有得而又有聞”的追求的。只是,自謝山由京城返鄉后,其父母相繼去世;乾隆五年(1739年),舅父蔣拭之又駕鶴西去,第二年忘年交九萬沙也仙逝了。此后,忘年交鄭性、惠士奇、老友趙谷林等在四年間都相繼去世。應該說在鄞縣與謝山交好的朋友以及父母都已作古,而且在廣東還有至交杭世駿的時時來探望,何況旅途奔波對于病體絕然無益,那么為什么謝山還念念于鄞縣呢?筆者來看,謝山本就沒有打算在廣東長期居留的愿景。如果有意遠走他鄉,則必會帶上妻子兒女同行,且謝山自己“百疾相纏摎”,[3]2066無意于一生都移居肇慶。而“端溪書院制撫極相推重,且與先生配曹孺人有族誼,具啟事將特薦”[3]58又觸動了謝山以生病為托詞盡早離開廣東回歸鄉里。由此可知,不同于帝京“左遷”而回鄉,晚年謝山早已決定了其回歸之所。兩次“遠游”并未讓謝山的人生指向有所偏離。
除了這兩次人生中路途最遠的奔波,謝山足跡也遍布于紹興和揚州、杭州。去紹興是為謝山受紹興太守杜補堂的邀請,出任蕺山書院山長。不過在任山長之時,不滿于方宜田在校訂劉宗周遺書時“妄刪其中數人”(4), 辭職歸家。除此之外的這幾次的偏振則形成了謝山以揚州為軌跡半徑向寧波聚合的社交圈。第一次去揚州是在謝山往京城趕考的路上,那里巧遇了厲鶚,又由厲鶚結交了馬曰琯和馬曰璐兄弟,從此就和揚州結下了不解之緣。在京城“左遷”后,又再來到揚州拜會馬氏兄弟,并且居住于維揚一段時間。而杭州則是全謝山常去之地。自十六歲那年去杭州應試后,謝山就接連去過杭州四次,在這期間,他結識了摯友杭世駿、趙氏兄弟、厲鶚、陳兆侖、姚世鈺、王豫等他未來在學術上相互切磋的好友。故而,罷官后,乾隆七年至十一年的五年時間里,謝山參加了寧波“真率社”、揚州 “韓江雅集”和杭州“消寒之會”,往來于三地之間不亦樂乎。三地之間的奔走當然以寧波為其中心而周轉,不僅因為家在寧波,而且謝山在寧波已經怡然自得。謝山一首題名為《家居十載,故人誚讓蝟集,獨彭侍郎芝庭曰:吾觀同館諸公蕉萃已極,安得如謝山之舂容自便。不禁有感于其言》詩就體現了他樂山樂水的情狀。詩曰:“鮚埼亭下對蒼蒹,讀易忙時且下簾。敢道玉堂天上客,不如漁父澤中黔。八甎筆札誰雄長,一研菑畬我薄厭。只為向來無遠志,守雌守黑更何嫌。”[2]2152如果這是剛離帝京返鄉的詩作,也許可以被認為是其滿腹怨懟而寫,可是家居十年后,友人也覺得謝山從容自便,則可以想見謝山無“遠志”是內心深處有感而發的。這種內心的牽引一直伴隨著他足跡遠及嶺南,卻在沒多久之后又回到家鄉度過他最后幾年人生。
歷數謝山一生,他在寧波度過了大部分時間,而且在每次顛簸流離之后都指引向寧波這塊熱土,這是因為寧波是他人生足跡牽引的動力。少年時期,謝山在家鄉受到其父悉心教誨以及富有啟發的諄諄教導,以至于他八歲時就能夠“干治經外,援以《通鑒》、《通考》諸書”[2]897,十四歲以后又受教于董正國先生處,奠定了他勤奮治學的基礎。而在被張廷玉和徐本排擠出京城后,便拂袖而歸,從此不再致仕。當有為太守詢問他“不出之意,何其決也?”謝山則以詩答之曰:“野人家住鄞江上,但見山清而水空。一行作吏少佳趣,十年讀書多古歡。也識敵貧如敵寇,其奈愛睡不愛官。況復頭顱早頒白,那堪逐隊爭金幱。”[2]2219謝山對于自己家鄉抱持的這種態度始終保持如一,并非因為仕途坎坷而聊以慰藉之說。“諸謝遺蹤遍浙東,釣磯琴屋不可數。大雷靜水尤清奇,云是玄暉讀書處。晴嵐夾道瀉瀑流,故應釀出驚句。想見搔藥問天時,瑤草仙葩助思趣。諸謝詩格各入神,玄暉俊逸尤獨具。唐風亦自玄暉開,青蓮低首拜白紵。”[2]2390“浙東列城雖褊小,風俗由來擬鄒魯。”[2]2109“勾馀一片土,疇昔最清嘉。接葉詩書澤,連甕公相家。到今無恙者,猶有青山川。”[2]2210不僅是家鄉的山水令謝山倍感親和,而且這種人文的氣息讓他沉浸其中,也是他身為甬上之人最為驕傲的地方。謝山自豪的感嘆“南宋儒林五派,俱萃于此,嘆為盛哉!”[2]2393“明季遺民,莫如甬上”[4]549“自東江建國,繼以翁洲,又繼以林門,吾鄉志士如云。”[4]257謝山作為一名歷史學家以及經學家,在治學中,以嚴謹而不摻溢美之詞為世人所稱頌。因此在評價自己家鄉時,也是極其客觀公正的。可以想見,句余之地在他心目中是何其重要,而不可撼動。
三、治學母題——寧波
謝山五十一年的人生軌跡,無論是游離于鄞縣之外,還是淡泊于家宅田園,都以寧波為其人生的坐標,受寧波這塊土地歷史文化的牽引,故而其學問貫穿著句余之地的治學母題,這不僅體現在他的著述有關于寧波的占據了一大部分,而且其書的內在精神也是與寧波的人文氣質相互呼應的。
(一)在謝山的全部著述中,有關于甬上的著作比例蔚為大觀。
正如王永健教授所認為謝山與梨洲和萬氏兄弟一脈相承,亦以一代歷史文獻為己任。他重視文獻,特別是鄉幫文獻的搜集、整理和研究,這方面的著述數量最多,也最為突出。謝山對此,也表現的相當自信:“非予表而出之,其誰更表而出之!”[2]301據學者統計,謝山著有《鮚埼亭內編》三十八卷、《外編》五十卷,《續甬上耆舊詩》七十卷、《國朝甬上耆舊詩》四十卷、《句余土音》二卷、《經史問答》十卷、《宋元學案》一百卷、《讀易別錄》三卷、《漢書地理志稽疑》六卷、《七校<水經注>》以及《三箋困學紀聞》等著作,這其中涉及寧波地理人物志的為絕大多數。如《續甬上耆舊詩》就是為寧波的志士仁人所編的典型之作,以明清交替之際的遺民李鄴嗣(杲堂)《甬上耆舊詩集》藍本而編著的。為了更好的保護好寧波鄉里的文化遺產,李氏幾代人不可不謂窮心竭力,何況李家與全家又是世交。因此,李鄴嗣撰寫《甬上耆舊傳》,全書就有《增補宋元甬上耆舊詩》,而謝山則在兩人的基礎之上寫成《續甬上耆舊詩》,將明代萬歷后至清乾隆時期的寧波鄉賢,著書立傳,將他們的佳作流傳于世。《勾馀土音》二卷則是謝山和里中胡君山、董鈍軒等人成立“真率社”后寫成。勾余是寧波的故稱,因此也是鄉邦文獻。還有諸多謝山遺失的著書中,也有相當之多關于寧波人物。例如《錢忠介公年譜》是鄞縣籍明末官員錢肅樂的生平介紹;《張蒼水年譜》則是鄞縣抗清斗士張煌言的生平志;還有如為為山先生編輯詩集二卷。山先生是鄞縣人周容的號,是明末的諸生,入清以后則放浪湖山。他“以詩名甬上,……予為去其十之五,而存有關名節者數十首,次為二卷,足以想見先生之生平焉。”[2]230就連《宋元學案》之編纂也是謝山老友之子鄭臨之(大節)叮囑其接續慈溪黃宗羲《宋元學案》而寫就的。謝山有詩曰:“黃竹門墻尺五天,瓣香此日尚依然。千秋兀自紹薪火,三逕勞君盼渡船。酌酒消寒欣永日,挑燈講學憶當年,宋元儒案多宗旨,肯令遺書嘆失傳。”[2]2117
(二)校訂《水經注》及書寫地理書籍以助四明水利
在謝山的諸多著作中,《七校<水經注>》不得不提,此書是其用力最勤的,曾七校其稿。初看其校勘此書于寧波并無多大的關系,但是正如南明史專家謝國楨老先生所說的,謝山此舉是為了四明的水利事業。在謝山著述中曾指出:“吾鄉民命,盡系于江湖諸坡塘之功”[2]1080。因為家鄉的水利事業自歷代以來幾近于荒廢,而且又沒有人進行考證,到了謝山生活的清中葉,諸多堰壩已經不為人所知。因此,謝山要對《水經注》進行校訂,并且付之于實踐,為四明水利建設提供自己的參考意見,這也符合他“經世致用”的治學理想。不僅如此,他還通過翻閱書籍,對家鄉的地理進行考據,同時足跡幾及四明山周邊的所有溪流、河道,對古代的河道走向、水利設施詳加考證,寫出了《重浚古小港議》、《重浚鄞三喉水道議》、《東四明地脈議》、《重修蛟唇二池議》等具有高度現實意義的議論文,對于寧波水文規律、資源的分布狀況進行了系統性的梳理,也將自己的看法付之于書上:“吾鄉水利,阻山控海,淫潦則山水為患,潮汐則海水為患,而地勢有崇庳,故必資碶閘之屬,以司啟閉”。在進行認真的考察后,謝山對于水利設施建設提出了新的意見“雙湖之深無底,其水既從西南二門而入,不能更從西南二門而出,久在湖中,則水性怫而不暢,故出滯宣幽,皆于喉是賴”。喉是古代水利設施的一種,謝山認為喉對于寧波城內的水利系統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對于城區水的吐故納新尤為重要。謝山的地理著述對于寧波的水利建設有著較高的使用價值,也為學者研究古代四明水利提供了一手材料。
(三)謝山的人生與甬上精神相契合
浙東文化從黃宗羲開始就本著“經世致用”的哲學理念,這也貫穿于謝山的人生哲學之中。以發揚“三禮精義”為要旨,激勵忠孝節義為本務,謝山反對前人“為六經而六經”的治學思想,他認為對“六經”也該聯系現實的生活中去理解和把握,“夫以古人著《禮》之意而言,不惟其文,惟其實”[2]1855,這就是說鉆研經書是為了更好的服務于現實。因此,正如呂楚建先生所言謝山認為治學“必須結合當初的歷史實際,聯系現實的政治生活,這樣才真正把握了古人著經的思想,而運用于現實。[5]”
甬上文化包孕著顯而易見的故國遺民之意識,這在謝山的著述中靡不見現。《鮚埼亭集》內外編,絕大多數部分都是表彰明末清初人物忠孝節義事跡的。對此,他自己曾說:“夫所以加恩于異代死節之臣者,以教忠耳。是駕布必不負國,而后不負其父,必不負其父,而后不負圣朝”。故而在理解這種遺民心態之時,他比誰都于心戚戚。方苞和謝山皆對萬斯同懷有極大敬意,何況方苞又是著名的大學者,不過在理解萬氏的精神世界時,謝山表現出了更加強烈的契合度。詩曰:“四明上溯滁陽胄,風虎云龍三百年。一出祗緣為庀史,終身安敢望朝天。誰將客婦行吟苦,漫作枯魚望澤憐。試讀秣陵遺事句,杜鵑心跡尚昭然。”[2]2214
四、結語
縱觀全祖望的一生,他以寧波為始,又在寧波終老,同時在生平的百轉千回的經歷中,以寧波作為其人生的中心指向,揭示了他與寧波這塊土地之間難以割舍的緊密聯系。因為念念于茲,于是奮筆疾書,將關乎甬上民生大計以及文化傳承的一切,包羅萬象于筆端,也將甬上的文化精髓傾注于紙上,為后世留下了一筆豐富的史學及文學遺產,也使我們從謝山的眼中看到了古代寧波鐘靈毓秀、人才輩出以及波瀾壯闊的歷史畫卷。
注釋:
(1)根據王永健教授著述《全祖望評傳》中對于全祖望一生的分期,形成四個階段:二十五歲之前,是他讀書甬上,懷抱經世大志時期;從二十六歲到三十三歲,是他“薄游京洛”,飽嘗人生艱辛時期;三十四歲到四十四歲,是他“家居十載”,潛心學術研究時期;四十五歲到五十一歲,是他“衣食奔走”,二任書院山長時期。
(2)此圖是根據南京大學王永健教授著作《全祖望評傳》中生平考一章來繪制的,縱向代表方位距離(寧波剛好為橫軸線),橫向代表時間推移,此圖基本反映了全祖望主要的幾次人生軌跡轉變,亦有細節略去不計。
(3)此處薄洛京洛引用自王永健先生的《全祖望評傳》的歷史分期,并希望通過此引用與本文形成對照關系。
(4)此處董秉純認為謝山離開嶯山書院是由于好友杜補堂的失禮,但是蔣天樞先生認為杜補堂在后來與謝山有書信交往,并且又是舊識,不會有太大矛盾,而是因為方宜田在纂修劉宗周的遺書中,應顧慮于清朝審查制度而將明清易代之際的”殉難義士”刪去的行為惹怒了謝山,使之憤然離職。王永健先生在參看蔣氏的謝山年譜時,也同意其觀點。筆者在慎重比較后,采取了蔣先生的觀點。
參考文獻:
[1] 王永健. 全祖望評傳[M]. 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6.
[2] 朱鑄禹. 全祖望匯校集注[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3] 蔣天樞. 全謝山先生年譜(卷二)[M]. 上海:商務印書館,1930.
[4] 全祖望,沈善洪. 續甬上耆舊詩集[M]. 杭州:杭州出版社,2003.
[5] 呂建楚. 全祖望學術特點淺論[J]. 寧波師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987(3):97-101.
(責任編輯:程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