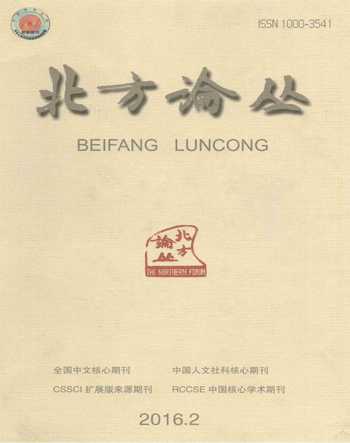馬爾庫塞自由價值觀的結構功能評析
馬淑娟 楊永志
[摘要]馬爾庫塞自由價值觀以追求人的潛在自由為核心,具有反對生產率標準唯一性的價值特點和以審美理性構建人的主體性的價值功能,目的在于建立非壓抑性秩序的價值理想。但是,由于馬爾庫塞在研究過程中背離了歷史唯物主義,折返到西方傳統理性之路,因此,他將自由實現寄托于審美理性的構建,致使自由成為一種脫離社會生產的幻象之物。
[關鍵詞]馬爾庫塞;潛在自由;審美理性
[中圖分類號]B50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3541(2016)02-0145-06
Abstract: With the pursuit of human potential freedom as its core goal, Marcuse's free value concepts have both the value characteristic of measurement with anti-productivity and the value function of human subjectivity construction with aesthetic reason, whose purpose is to establish the ideal value with no-repressive order. However, Marcuses free value concepts deviate from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return to the traditional western rational fence methodologically, with freedom built on the aesthetic reason construction, therefore, freedom can be nothing but an illusion without social practice.
Key words:Marcuse; potential free; aesthetic reason
馬爾庫塞自由價值觀產生的背景是西方工業技術理性對人的嚴重異化。馬爾庫塞指出,由于西方理性文化與現代資本主義生產秩序相結合,轉變為一種使統治趨向合理化的工具理性或技術理性即操作原則,已經喪失了對現實的批判功能。這種操作原則對生產設施的合理規定和使用,借口保護社會整體利益和個體自由,建立起對個體的極權主義統治。
具體來說,技術理性對個體的極權主義統治有四個方面:一是對勞動的異化,個體勞動的目的不再是為了滿足自己的需要和發揮自己的作用,而是履行某種功能,也就是說人在異化中工作。“人不能在勞動中實現自己,他的生命成了勞動工具”[1](p.74)。二是通過對勞動時間的控制,異化勞動占據了個人大部分生活時間,使人大部分時間處于痛苦之中。三是國家通過操縱大眾傳媒制造出一個娛樂社會,使個人的閑暇時間處于無思想狀態,使個人失去了理性思考的能力,無法運用理智對抗社會。四是操作原則對個人愛欲進行操縱,具體是通過文化傳統所形成的社會權威如道德等影響良心和無意識,形成超我,對本我欲望進行壓抑,使人放棄對未來本能滿足的要求。
技術理性的操作原則使個體喪失了反抗能力,表現為兩點:一是個體更加社會化,過去文化價值觀的傳承是通過個體之間的傳遞來完成的,而現在則是通過大眾傳媒直接面對個體進行傳播,極其強大的教育和娛樂機器令所有個體處于一種麻木不仁的狀態中,使個體喪失了對現實世界的理性反思能力;二是資本主義通過官僚機構和管理制度對個體進行統治,使個體在整個社會制度面前越發無能為力。
反抗能力的喪失表明人的潛在自由和能力遭到了壓抑,“裝備線的整套技巧、政府機關的日常事務以及買賣儀式,都已與人的潛能完全無關。”[1](p.72)通過制度和傳媒對人的控制,個體意識被同化,自我大大萎縮,個性被取消了,所謂個性不過是一種類的特殊表達(如賣淫婦、主婦、硬漢、女強人等),一切不過是生產銷售的符號。人越來越缺乏自主性,“人類生存不過是一種材料、物品和原料而已,全然沒有其自身的運動原則。”[1](p.73)
一、馬爾庫塞自由價值觀的結構分析
基于上述資本主義生產特點,馬爾庫塞提出了以愛欲解放為途徑、以實現人的潛在自由為核心的自由價值觀,包含四個層面:
(一)價值觀核心:追求人的潛在自由
針對工業文明社會中操作原則所造成的極權主義統治,馬爾庫塞延續了黑格爾哲學中“潛在的”、自由、理性等概念,以追求人的潛在自由為價值核心。
1.人的潛在自由以個體性存在為前提。在黑格爾的基礎上,馬爾庫塞指出自由在于個體性的保存,“他是自由的,因為在同其他人的存在中,他僅僅保持了自身。他認為他的存在好像是自己無可爭議的私有財產。自由就是所有‘外在的自足和獨立,就是所有客觀性已為主體所占有的狀態競爭社會的恐懼和不安似乎激發了自由的理念,喪失自我的個體恐懼和他的不安似乎保護了他自己”[2](p.111)。進一步,自由不僅強調個體性的保存、一種自我意識的自由與獨立,而且,個體還要與其他個體發生關系,由“我”的自由變成“我們”的自由。這個過程,就是個體之間進行“生死斗爭”,即黑格爾所言的主奴關系形成過程,個體自我意識之間的相互作用逐步形成整個人類的自我意識,即個體在斗爭過程中認識到自己的潛能,從而實現自由。
2.人的潛在自由是指理性所具有的一種認識和改造現實的理性構建力量。人的潛在自由是借助理性手段實現的,“貫穿于《精神現象學》的乃是把認識論領域溶入世界歷史,并通過自我意識的實踐,從主體的發現過渡到主宰現實的任務。”[2](p105)潛在自由,是人在利用理性實現自我意識的過程中,自我認識和改造現實世界的能力逐步擴展,表現為人的潛能的實現。這種利用理性實現人的潛能的過程,是人不斷利用理性追求真理、形成精神生命的過程。發現和塑造自我的過程中,人不斷意識到自我潛能、克服自身束縛,獲得自由。因此,“自由以使自由成為可能的條件為先決條件,即以意識和理性主宰世界為先決條件。”[2](p.96)也正因如此,馬爾庫塞反對實證主義,因為實證主義放棄了人的潛能。“實證主義是常識的哲學,它訴諸世界中的事實,而且,正如黑格爾所揭示的,在這個世界中,事實并不能代表現實所能代表的和應該代表的”[2](p.107)。并且實證主義是保守的,“它使思想滿足于事實,拒絕任何對事實的超越和對現存條件關系的偏離。”[2](p.38)
3人的潛在自由指向未來,要求打破現存事物或秩序的限定性,不斷探索面向未來的可能性。由于“潛在是在它的概念中被規定的。”“實在與潛在的差別構成了辯證過程的起點。”[2](p.70)任何事物總是處于一種不能完全表明其潛在狀態中的存在,因此,有限事物要通過否定運動過程逐步走向概念,也就是不斷經歷否定之否定實現自身的潛能。所以,人的潛能自由總是指向未來的,主張超越現有秩序,達到對真理的認識,對自我不斷重新認知和塑造,而不是既定于人類已有的經驗和習慣。
4.人追求潛在自由的動力在于對自身愛欲的追求。馬爾庫塞根據弗洛伊德關于人的心理結構理論,認為本我遵循快樂原則,追求愛欲的滿足。雖然在工業文明操作原則統治下,人的身心成為異化勞動的工具,“但只有當人的身心拋棄了人類有機體原先具有并追求力比多的主——客體自由時,才會成為這樣的工具。”[2](p.29)正是因為個體心理結構始終存在本我對于愛欲追求的動力,所以,人類社會總是處于文明秩序的壓抑力量與愛欲的破壞力量之間的不穩定狀態。正因如此,對于愛欲的需要就構成了個體對抗工業文明操作原則的統治,實現自我潛在自由的根本動力。
(二)價值觀特點:反對將生產率作為人類社會發展的唯一衡量標準
馬爾庫塞從弗洛伊德的文明觀出發,認為缺乏是人類社會的基本事實。為了滿足基本的生存需要,人必須從事痛苦的勞動,并且由于這種勞動的持久性,使人的快樂受阻,進而痛苦成為人類社會的普遍現象。由于人有追求快樂和滿足需求的本能,但為了生存,使這一本能被迫屈從于現實原則,接受壓抑性管制,形成了社會歷史對人的“基本壓抑”。但是,文明對人本能的壓抑不是一直都能維持在一個穩定狀態,恰恰相反,人類的本能遵循的快樂原則,始終要求人的需要得到滿足,構成了人的力比多能量。文明對人類本能不斷進行壓抑,導致個體的生命本能不斷被削弱,個體力比多能量不斷聚集,必然導致個體終究要求釋放這種能量,進而形成一種死亡本能,即對現實原則進行破壞的愿望。這種力比多能量不斷積累,形成了一種反抗文明、破壞社會的潛在能量。因此,整個人類社會的進步表現為一種“進步——崩壞——進步”的循環式發展。
在基本壓抑概念基礎上,馬爾庫塞提出額外壓抑和操作原則兩個術語。額外壓抑是指“為使人類在文明中永遠生存下去而對本能所做的必要‘變更。”[3](p.21)不同于基本壓抑,額外壓抑并不是維持人類基本生存的必要約束,而是為維護特定歷史機構和統治階級的特定利益對個體實施的附加控制。而操作原則就是現實原則的現行歷史形式。基于弗洛伊德文明是現實原則對個體壓抑結果的觀點,馬爾庫塞進一步指出,盡管操作原則通過將個體組織起來,并通過對權力的較為合理的安排和使用壓抑個體,進而使人類文明獲得進步。但是,權力的合理使用與操作原則存在區別,因為操作原則的目的是實現統治階級的特殊利益,而權力的合理使用則限于為整體進步所必需的機能和工作,這是一種勞動的合理分工。操作原則主要目的在于實現特殊的統治利益,文明進步只是一種副產品。所以,馬爾庫塞認為,那些將提高生產效率作為人類社會進步唯一標準的做法不過是為了維護工業社會對個體的極權主義統治;生產率價值標準是現代操作原則的文化反映,現代社會中的額外壓抑集中體現在生產率價值標準中,以往的觀念認為人類的解放在于生產率的提高,這種觀點不過是建立永久性壓抑性社會的合理性證明,于是“提高勞動生產率成了資本主義和斯大林主義共有的斯達漢諾夫主義的神圣不可侵犯的理想。”[3](p.112)
此外,馬爾庫塞認為,非壓抑性生產秩序的實現受到現代文化的阻撓,即受到生產率價值標準的思想束縛。西方社會進入后工業時代后,商品極大豐富,客觀上已經存在減少額外壓抑的現實條件。只要對操作原則進行合理使用,可以克服人類社會物質產品缺乏的問題。那么“在成熟工業文明的‘理想條件下,勞動全部實現了自動化,勞動時間減少到最低限度,勞動技能可以相互交換”,就存在結束異化的可能性。由于工作日的長度本身就是現實原則對快樂原則施加的主要壓抑性因素之一,所以,伴隨“縮短工時日,使得純粹的勞動時間量不再阻止人類的發展”[3](p.110),個體自由的實現不再遙遠。由于異化勞動越激烈,意味著勞動自動化發展越發達,也意味著勞動以外的時間和領域越充分,自由消遣的時間也就越多,“正是勞動以外的領域規定著自由和實現。”[3](p.113)因此,工業文明的發展為取消額外壓抑、超越操作原則和生產率價值標準提供現實可能性。
(三)價值觀功能:以審美理性塑造人的主體性
在理性問題上,馬爾庫塞主張構建審美理性,重新塑造人的主體性,以反對工具理性對人的壓抑和統治,這一思路延續了西方哲學的理性文化傳統。康德指出,解決一般和個別的矛盾,即義務命令和對幸福追求之間的矛盾,需要個體在其他答案中尋求真理。黑格爾沿著這條思路,在藝術和宗教中尋找真理,最終在哲學辨證中發現真理的認識過程。在馬爾庫塞這里,則將康德的理性結構與弗洛伊德的人的本能理論相結合,在審美中發現人的潛在自由。
康德的理性結構是由實踐理性和理論理性構成的,實踐理性構成了人的自由,受到道德律的支配;而理論理性構成了自然,為因果律所控制。判斷機能通過痛苦和快樂的感覺機能將自然領域和自由領域相聯系,理論理性提供認識的先天原則,實踐理性提供欲望的先天原則。快樂作為審美的判斷直接聯系藝術領域,成為自由影響自然的必然中介,即成為以實踐理性引導理論理性的中介。這意味著審美直覺地將道德與感性機能聯系起來,將理性與審美感覺相結合,證明了自由的實在性。因此,審美成為感覺和理性鏈接的中介,能夠調和感性和理性的分裂、自由和必然的分裂,進而協調被現實原則所分裂的人類生存的兩個方面,即享受與勞動的分離,手段與目的的分離。這種分離的現實背景就是人被操作原則束縛在生產整體的某個部件上,成為一個零件。根據弗洛伊德的文明觀,馬爾庫塞指出,文明是由感性沖動和形式沖動的矛盾運動所而獲得發展。現代文明中,兩者的關系始終處于對抗狀態:感性本質上是被動的、接受性的,而理性是主動的、支配性的和壓倒性的,感性只能通過破壞文明的方式得以表現。相應地,人的心理結構存在著以工具理性壓抑感性的不和諧,人在情感上由于工具理性的壓抑變得枯竭荒蕪,妨礙了人的潛在自由的實現。而審美理性使人的理性結構得到重新塑造,由藝術理性代替工具理性,重新聯系理性和感性,重新塑造人的主體性,激發人的潛能,最終將人從非人的狀態中解放出來。以藝術理性改變人,使人超越欲望和工具理性的統治,由一種受苦役和痛苦的狀態進入審美性的消遣狀態。此時,人不再是操作原則統治下執行命令的工具,而是作為創造主體,利用想象機能進行創造活動。人利用想象機能,“探尋并投射所有存在的潛能”[3](p.138),實現自身的潛在自由。
可見,潛在自由的實現在于將人的工作由一種異化勞動轉化為審美消遣,即人的工作不再是以外物為目的,不再是為了自我保存,而是為了消遣。將異化勞動轉化為消遣性工作的實現途徑在于審美原則的普遍化。
(四)價值觀理想:建立非壓抑性秩序
馬爾庫塞以藝術理性為基礎,提出建立一種普遍化的審美秩序,即人的欲望和需要無須通過異化勞動得到滿足,人能夠自由地消遣自己和自然的機能與潛能。由審美文化演繹的文明原則——消遣原則來支配整體人類生存。作為整體意志,審美秩序以個體性為前提和基礎,“秩序成為自由的必然條件也以個體的自由滿足為基礎,并為這種滿足所維持。”[3](p.140)審美秩序“將使每個人具有真正不同的需要、真正不同的滿足方式,即具有自己的取舍自由。”[3](p.168)
然而,由于人類自由包括兩部分內容:一是人通過理性掌握和征服自然所確立的自我實現自由;二是人作為個體對自我生活選擇和塑造的自由;操作原則和審美原則分別對應自我實現自由和自我選擇自由。所以,審美秩序并不是要完全取消操作原則,而是與操作原則相結合。作為一種成熟文明的功能,操作原則具有協調安排各種社會事物的作用,“以知識和必然性為基礎,保護和保存著生命為目標。”[3](p.165)將審美秩序與操作原則相結合,目的是以審美功能建立的感性審美秩序使操作原則的工具理性秩序變得人性化,使愛欲對理性重新規定,恢復人的個體自由。并且,審美秩序與操作原則的結合使審美秩序的延續和發展建立在社會現有機能基礎上,具有一種現實可能性,以免流于宗教式的幻想之中。此外,通過兩者的結合,操作原則不再是使人從事異化勞動的工具,不僅是實現人類自由的手段,更是人的自由的組成部分。
確立審美秩序需要發揮哲學對現實的批判功能,將哲學的批判功能與人對愛欲的追求相結合,使人恢復追求潛在自由的理性力量,“思想的一個崇高任務就是反對屈從時間,恢復記憶的權利,把它作為解放的手段。”[3](p.171)哲學對現實操作原則的批判體現在對現存秩序的否定,即反對將操作原則永恒化,“在堅持那些使自由降為持久的烏托邦的法律、秩序、順從和機構的時候,時間的流逝是社會最好的盟友。時間的流逝有助于人們忘卻過去存在的東西和可能存在的東西,使人們不去顧及美好的過去和美好的未來。”[3](p.171)文明使人們長時間屈從于操作原則如法律、制度等一系列的社會機制的束縛,形成了對社會生產性壓抑這一不合理現實的默認和容忍,而不再探索面向未來實現自由的可能性。反對壓抑性秩序和時間的聯合就成為人實現潛在自由的條件,人們建立審美理性以超越對抗性的人類實在即工業文明中的操作原則,最終實現追求人的潛在自由。
在審美秩序普遍化的前提下,通過想象的審美功能釋放人本能力量、重建文明,即以審美理性抵抗操作原則的工具理性統治,工作就有由一種異化勞動轉變為消遣的可能性。壓抑性文明發展模式就有可能轉變為非壓抑性文明發展模式,作為工具理性的操作原則對本能進行壓抑而獲得發展,就可能變為通過想象釋放力比多能量,文明的發展由壓抑本能變為對本能進行創造性的接受。
二、關于馬爾庫塞自由價值觀的評析
馬爾庫塞的自由價值觀分析了人之所以不自由,歸根結底是由于資本主義壓抑性生產造成的,并關于資本主義生產對人的異化程度和手段做了詳細論述,由此提出自由的核心在于人的潛在自由的實現。從某種程度上,這發展和豐富了馬克思關于人的異化理論和自由思想,尤其是揭露了當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對人進行的文化滲透和控制;其關于自由的價值和意義對于社會發展的文化反思有利于我們對自由價值觀內涵和功能的重新理解。
(一)對馬爾庫塞自由價值觀的內容評析
1.馬爾庫塞自由價值觀內容具有鮮明的時代性。馬爾庫塞對于自由的理解是在當今工業文明背景下提出的,針對的是工業社會技術理性對人極權主義統治所產生的人被工具化的問題。馬爾庫塞從黑格爾、康德哲學中關于自由的理解出發,結合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學中人的心理結構理論,提出在當今社會操作原則的統治下應當對工具理性本身進行文化批判,建立一種以審美理性為基礎的審美秩序,將工作由異化勞動變為審美消遣,進而實現人的潛在自由。雖然操作原則統治下也存在對人的自由的規定,但主要側重于法律規定的權利,是一種建立在工具理性基礎上的形式自由,是一把雙刃劍。換言之,這種以制度、法律等社會機制對人的統治雖然客觀上推動了人類文明的發展,但是,也造成實際當中人的主體性的壓抑。具體表現為人由于異化勞動而被工具化,從人的勞動再到人的消費休閑都被技術理性所操縱,尤其是在消費主義的影響下,人喪失了理性反思社會的能力,成為生產鏈條上的零件和被消費文化所定義的符號,失去了人的個性。因此,馬爾庫塞所提的人的潛在自由不僅是黑格爾、康德哲學中引申出的概念,沿著馬克思的人的異化理論和社會生產視角,體現了鮮明的時代生產特點。
2.馬爾庫塞自由價值觀注重個體的超越性特征。馬爾庫塞自由核心價值觀中的個體性體現了一種主體間性關系,是指個體與其他個體意識之間的相互作用,他認為,個體間自我意識的相互作用促進了人類思想的進步,推動社會發展。所以,馬爾庫塞所言之個性實際上源于黑格爾所講的個體性,包含兩點內容:(1)獨立性個體是指個體作為一種自在存在,“僅指一般地賦予當前已有的東西以個體的形式,內容方面仍然不出現在已有的普遍現實的范圍。”[4](p.201)(2)超越性個體作為一種自為存在,具有特殊的現實和特殊的內容,“使個體作為特殊的現實和獨特的內容跟普遍的現實對立起來。”[4](p.201)強調人展開自由的行動,不斷將自身所具有的潛能變現。通過超越性個體與獨立性個體之間展開自我意識的相互作用,不斷改變普遍的理論認識,進而推動社會進步。馬爾庫塞著重強調第二層含義,即個體與普遍現實即文化、習俗、道德等相對立的特殊性,從而某些特殊個體能夠超越社會既有規定、促進社會進步。馬爾庫塞強調超越性個體對于社會發展與進步具有重要作用,進而反對大眾傳媒所產生的虛假個性。
馬爾庫塞的愛欲論表明人的潛能或個性是蘊含在人的多維度需要或全面性中。而面對工業時代將人單面化的現實,馬爾庫塞關注人的利益訴求和價值愿望,追求人幸福的實現。馬爾庫塞所言的幸福不是單純的物欲滿足,也不是遙遠虛幻的宗教許諾,而是激發人追逐夢想、挖掘潛能、實現自我的超越性過程,即人實現自身潛在自由的過程。
(二) 對馬爾庫塞自由價值觀的功能評價
1.馬爾庫塞著重從社會生產角度思考人的主體性內容。人的主體性是人在理性認識和實踐過程中不斷改造主觀世界、逐步深化認識形成的自我意識。現代社會普遍以理性塑造人的主體性,這來自于西方哲學的認識。西方哲學普遍認為只有理性精神才能塑造人的主體性,因為在人追求真理的理性認識過程中逐步形成了自我意識的四個特性,即具有尊重規律的客觀性、改造自我認識的反思性、進行創新性認識與實踐的超越性、擺脫自然世界的獨立性。然而,馬爾庫塞認為,近代工業文明與傳統理性相結合,使傳統理性演變為一種工具理性,表現為勞動的異化使人成為資本主義生產的工具和大眾傳媒所制造的娛樂社會的容器,使人喪失了主體性,自我意識大大萎縮。“個體被大眾交往同化,只是也受到了支配和限制。個體并不真正理解所發生的事情”[3](p.73),喪失了自我認識的反思能力和超越現實的創造能力。為重新恢復人的主體性,馬爾庫塞在繼承西方理性傳統的基礎上,根據康德的理性結構,結合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論,將人的愛欲與理性相結合,提出既體現物質需求、又體現精神需要的審美理性,以審美理性重新塑造人的主體性,主張審美式的工作消遣,反對異化勞動和大眾傳媒對人心理空間的侵占。馬爾庫塞審美理性對人的主體性做出了新的定義,人不是實現生產目的的理性工具,也不是大眾媒體的被動接受者,而是追求潛在自由的人。因此,馬爾庫塞關注自我的個性發展和人的精神需求,更強調人作為主體對社會現實和自我認識所具有的反思性。
2.馬爾庫塞強調從文化角度探尋現人主體性的實現途徑。馬爾庫塞的自由價值觀提出了實現人主體性的社會條件。“(1)苦役(勞動)變為消遣,壓抑性生產變為表演。在這個變化之前,首先必須征服作為文明的決定因素的缺乏。”[3](p.141)針對這點,馬爾庫塞指出現代工業社會操作原則的發展將不斷提升社會生產效率,縮短勞動時間,提供更多的自由時間,也使社會管理更加合理,逐步消除物質缺乏的狀態,為工作變為消遣提供了本能基礎。“(2)感性(感性沖動)的自我升華和理性(形式沖動)的貶值,調和了這兩種基本的、對抗的沖動。”[3](p.142)馬爾庫塞提出了旨在改造傳統目的理性的審美理性,希望克服目的理性的片面性,對人進行更加全面的文化解讀,更新對人主體性的理解,進而改變對人自身的基本看法。“(3)征服有礙于持久滿足的時間。”[3](p.142)關于此,馬爾庫塞提出了理性重建思想,主張發揮文化對現實社會的批判作用,不斷提出新的理論認識使人們能夠超越文化傳統和社會現實,實現人們在歷史實踐中的創造性活動。只有將人的主體性理解與對社會現實問題的理性反思相結合,才能為人和社會的未來發展提出富有建設性的理論設想。盡管馬爾庫塞在他的著作中,只是在一種宏觀層面提到實現人潛在自由的社會可能性,并沒有解決具體落實的問題,并因此招致許多國內學者的批判,但是,他的思想卻為人類文明進一步發展提供了一個思考的方向。值得注意的是,其后來阿瑪蒂亞森繼續發展了這一思路,提出以自由看待社會發展的觀點,將發展看作是擴展人們享有的真實自由的一個過程,改變人們關于經濟發展的觀點,不再以GDP作為衡量經濟發展的指標體系,開始主張以人的自由程度作為經濟發展的衡量指標。
(三)馬爾庫塞自由價值觀的文化評論
馬爾庫塞自由價值觀思想包含著抽象理性邏輯和歷史唯物主義邏輯之間的矛盾。馬爾庫塞關于人的自由的思索一開始沿著馬克思的生產邏輯出發,指出資本主義生產秩序演變而來的操作原則對人的自由的壓抑,進一步提出西方理性文化與資本主義生產秩序相結合演變為壓抑人的工具理性。但是,在思考如何實現人的自由問題,馬爾庫塞卻未繼續沿著歷史唯物主義路徑,不是從分析生產方式角度進行求解,而是折返到西方傳統理性主義之路,希望借助理性重建的文化途徑改變人的存在狀況。馬爾庫塞將審美理性看作是超越時間和空間的終極解放力量,這無疑是一種在不改變資本主義現存生產秩序下的文化烏托邦理論,其自由價值觀也由此與歷史唯物主義分道揚鑣,陷入審美理性所編織的虛幻自由之中。從研究方法看,馬爾庫塞自由價值觀體現了將歷史唯物主義內含的社會結構多維度關系還原到文化領域中理性的單一維度過程。
因此,從整體上看,馬爾庫塞的自由價值觀延續了西方文化的理性傳統,突出表現為用理性建構的文化手段來解決自由實現的問題。如馬爾庫塞將人的主體性看作潛在自由的實現,將人的欲望重新解讀為愛欲,以愛欲形成審美理性,以此構成社會進步的動力,實際上是結合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論對黑格爾個體性思想的發展。黑格爾認為,人類不斷超越自我、實現社會發展的力量來源于人的欲望,馬爾庫塞自由價值觀正是在繼承了黑格爾理性思維的基礎上,對欲望本身做出重新規定。此外,馬爾庫塞對于人的潛在自由的強調,來源于黑格爾對自我的理解。黑格爾認為,作為自我的精神具有對待自我的兩種態度,一種是現實的態度,“有時候精神采取接受現實的態度,使自己適應于現有的風俗習慣倫理道德以及以精神自身為對象的那些思維方式等等”,還有一種是反對現實的態度,“有時候精神持反對現實的態度,進行獨立思考,根據自己的興趣情感來挑選其中特別為它的東西,使客觀事物適應于它自己。”[4](pp.200-201)黑格爾認為,理性的超越性才是個體性的本質,只有通過法權、法律和道德的普遍規定,才能為一切人實現個性提供前提條件。正是由于馬爾庫塞在研究過程中逐漸背離了歷史唯物主義,更多側重于對西方理性傳統的繼承,才會從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現實批判轉入審美理性的幻想之中。
[參 考 文 獻]
[1][美]赫伯特·馬爾庫塞.愛欲與文明[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
[2][美]赫伯特·馬爾庫塞.理性與革命——黑格爾和社會理論的興起[M].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7.
[3][美]赫伯特·馬爾庫塞.愛欲與文明[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
[4][德]黑格爾.精神現象學:上卷[M].北京:商務印書館,1987.
(馬淑娟:徐州工程學院講師,法學博士;楊永志:南開大學教授)
[責任編輯 張桂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