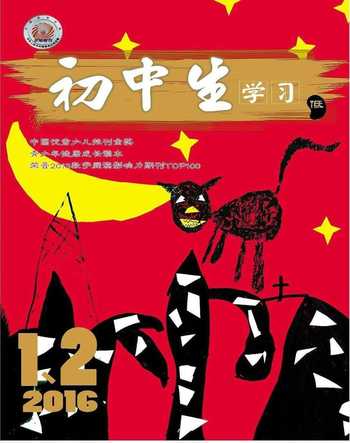心靈感應存在嗎?
劉曉峰
那些心靈感應的故事
一對生活在美國俄亥俄州的雙胞胎,一出生就被不同的家庭收養,40 多年后二人重逢時發現他們的生活驚人地相似。兄弟倆的名字都叫“詹姆士”,都在機械和木工工藝方面具有天賦。二人都有過兩次婚姻,他們的前妻都叫琳達,而現任妻子的名字又都是貝蒂。他們各有兩個兒子,分別名叫詹姆士·艾倫和詹姆士·艾蘭。
很多人看到這些驚人的相似都感到太神奇了,這難道是人們通常所說的“心靈感應”嗎?不過還有比這更神奇的故事。
里克和羅恩是美國的一對雙胞胎。1995年1月,里克從休斯敦國際機場起飛,前往非洲安哥拉的一家石油公司審核賬目。在安哥拉起初的幾天很平靜,但5月31日凌晨4點鐘,里克被腹部劇烈的疼痛驚醒。他立即去了醫院,醫生為里克做了全身檢查,但沒有發現什么問題。直到4個小時之后,里克身上的疼痛才逐漸消失。
但壞消息卻在當天夜里降臨,里克的雙胞胎哥哥羅恩,前一天夜里在美國家里被殺。驗尸報告表明羅恩的死亡時間是美國中部時間晚上10點30分,正是里克在安哥拉夜里因腹部疼痛驚醒的時間。里克相信他感應到了哥哥被殺時的劇烈疼痛。
雙胞胎之間到底有沒有“心靈感應”?美國《雙胞胎世界》的編輯勃蘭特說,他聽說過許多與里克的經歷相似的故事,并且相信雙胞胎之間存在一種超自然的溝通方式。
不僅雙胞胎之間,夫妻之間也有心靈感應。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美國一位名叫珍妮的女子收到了美國軍方簽發的丈夫的死亡通知書。此后,珍妮多次夢到丈夫在一個迷霧籠罩中的莊園里呼喚自己。于是,她開始了漫長的尋找之路。輾轉數年后,終于在法國的一個廢棄莊園里找到了和她夢中一樣堆滿尸骨的地窖。其中一具遺骸左手的無名指上有一枚刻著J&M的戒指,這戒指正是她丈夫莫林的。
心靈感應的理論依據
心靈感應是否真實存在?主流科學家都對此不屑一顧,認為心靈感應都是些不靠譜的傳說,無法進行科學驗證。但是,英國劍橋大學的生物學家魯伯特·謝爾德雷克20多年來一直在進行科學實驗,以證明人類的心靈感應和預感等現象可以從生物學角度得到解釋。
當我們想念某個朋友的時候,他正好就打來電話;當我們感覺有人在看我們的時候,就會回過頭去,那人果然在那里。謝爾德雷克認為,這是正常的動物行為,是動物經過了數百萬年的演變,為適應生存的需要而形成的。是什么促使謝爾德雷克做出這樣新穎的結論呢?謝爾德雷克認為,人類的心靈是受外部環境影響的,但同時也在周圍環境中留下了自己的痕跡。與電磁場的存在一樣,心靈也有自己的場域,或曰“形態共鳴場”。人體與心靈的信息就隨著形態場四處流動,理論上就跟電磁場一樣,可以傳播到無限遠,其細微的痕跡有可能被任何人捕捉。
但是,一般情況下,只有自己最親的人才有可能與你在形態場里發生心靈上的共鳴。這其中的道理是其如同電磁場一樣無處不在,但若需要接收特定的電磁信息,必須有對應的工具。我們必須用電視機接收電視臺發出的電磁波,用手機接收別人撥打的電話。因此,對于人體的“形態共鳴場”,最有可能捕捉到這種心靈痕跡的是自己的親人。心靈感應現象基本只在親朋好友之間發生。
正統的生物學理論認為原子構成分子、分子構成細胞、細胞構成器官,生命就像機器一樣,由零件組裝而成。而所有的生命現象都被認為原則上可用物理和化學的原理進行說明。例如生命的遺傳都是通過基因來完成的,因此現在生物學界最重大的使命就是破譯基因密碼。
但是,已經有越來越多的生物學家意識到,除基因遺傳程序之外,還有另一個因素在有機體中起作用,這就是生命的“形態共鳴場”。
早在20世紀20年代,為了說明生物體發育成長的過程,就有生物學家引入了“形態共鳴場”的概念。有一種扁體蠕蟲,當它被切成兩半時,每一半都會發育成一個完整的有機體。一些科學家對這個現象的解釋是,這種再生是受一個特殊的生物場支配的,正像一根磁鐵被截成兩半時會形成兩根新的磁鐵,每一根磁鐵都有自己的完整的磁性一樣,當扁體蠕蟲被一分為二時,它的形態共鳴場就分裂為兩個完全相同的場。
到了20世紀50年代,蘇聯科學家伊紐欣認為,對人類而言,“形態共鳴場”附屬于人腦,當這個場從人腦不斷散發開去,與另一個人的大腦產生共振效應時,就有可能產生心靈感應現象。
用實驗證明這微弱的效應
這種“形態共鳴場”是怎么發生作用的呢?謝爾德雷克聲稱,我們日常的行為方式就受形態共鳴場的支配。科學家的實驗證實,如果一只老鼠學習到一種新的行為方式,那么后來的老鼠就能以更快的速度學習到這種行為方式。學習完成這種任務的老鼠越多,則后來的老鼠就越容易學習這種本領。因此,若第一批有上千只老鼠在實驗室里被訓練學習進行一種新的操作,那么第二批老鼠就會以更快的速度學到這種本領。
為什么后來的老鼠學習新事物的速度要比前面的老鼠快呢?這就是“形態共鳴場”在發揮作用,在一個實驗室里,當越來越多的老鼠掌握了一種行為方式時,實驗室里就形成了比較強烈的“形態共鳴場”,讓后來的老鼠產生心靈感應,使它們學習這種新行為方式來得更容易些。
我們人類身上也有這種“形態共鳴場”效應。幾年前,英國一家電視臺對“形態共鳴”效應進行了實驗。電視臺準備了兩幅畫,這兩幅畫不仔細看并沒有什么特別的意義,只不過有很多顏色夾雜其中罷了。但其實畫中有畫,其中一幅是一個戴帽子的女性,另一幅是一個蓄著胡子的男性。
接著,電視臺找來第一批志愿者,讓他們辨認畫中隱藏的圖像,然后對第一批志愿者揭曉答案。再接下來,電視臺找來第二批志愿者辨認畫中隱藏的圖像,結果是第二批志愿者辨認出來的比例,竟然比第一批志愿者高了三倍。
這個結果正說明,第一批志愿者已經知道了答案,這給了那些素昧平生的第二批志愿者某種暗示。這種暗示在實驗室里產生“形態共鳴場”,從而使第二批志愿者答案的準確率得到了大幅度提高。
心靈感應處處見
毋庸置疑,對于普通人來說,生物的這種“形態共鳴”效應是極其微弱的,就像電磁場處處充滿我們的空間,但如果沒有專門的儀器,我們根本不可能意識到它的存在一樣。但心靈感應在我們理性的遮蔽下顯得神秘和不可思議,而且得不到主流科學家的承認。
但事實上,心靈感應現象在動物界卻普遍存在、屢見不鮮。
如果你仔細觀察鳥類的飛行,你會不會覺得很奇怪:它們為什么在飛行時好像一個整體,而不是各自亂飛?這類奇特的動物現象還有很多:鮭魚等魚類每年往返于河流與海洋之間,候鳥每年遷徙數千公里,它們是如何知道飛行或游動路線的呢?
人們用自組織理論來解釋飛鳥的整體行為,又用磁場理論來解釋飛鳥的遷徙行為,又用基因程序設計來解釋魚類洄游行為,但這類解釋卻沒有抓住動物行為的本質,事實上它們的這種群體行為更像是彼此之間的心靈感應。
動物間發生心靈感應,是“形態共鳴場”在發揮作用。當成群的魚或鳥聚集在一起時,這個“形態共鳴場”產生了共振現象,動物之間的心靈感應就發生了。
其實,在人類文明還沒有發展起來的原始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的心靈感應很常見。20 世紀30年代,悉尼大學人類學家埃爾金教授在對澳大利亞原住民長期調查后發現,原住民之間心靈感應經常發生,比如有一個原住民在距離家鄉相當遠的地方工作,突然有一天他對同事說自己的父親過世了,而他的妻子又生了一個孩子,他急急火火趕回家去,一看果然是這樣。在埃爾金教授的調查中,這樣的事例比比皆是。
心靈感應對遺傳的作用
人類的心靈感應是無法被扼殺的,它只是被壓制在人類的潛意識之中。我們來思考這樣一個問題:為什么許多人生來怕黑、怕蛇,卻對花有著留戀?這是因為遠古時代人們對自然的反應通過一代代遺傳存留在人類的種族記憶中,成為人類普遍擁有的集體潛意識。
問題是,這種有關集體潛意識的記憶是如何在我們出生時就在我們大腦中打下烙印的呢?又是留存在我們大腦的哪一部分呢?
生物學中一個未解之謎便是記憶本身。我們如何記住昨天的事情,又如何辨認周圍的人,等等,所有這些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記憶的確頗為神秘。通常人們認為,記憶在大腦中肯定是有一些物質基礎的,就像計算機中的存儲芯片一樣。但直到現在,并沒有人真正發現大腦中哪個部分是記憶所在,包括那些利用老鼠和猴子作為研究對象的所謂研究人類記憶的科學家,也一無所獲。
謝爾德雷克由此指出,當我們努力尋找大腦中的記憶物質時,其實是走錯了方向,我們的大腦根本不是記憶的存儲之地,它更像是個跟電視機一樣的調頻接收系統,通過“形態場”共鳴的方式找到我們各自的記憶。
正是這樣的調頻接收系統,使我們在意識的最深處接收到了一代又一代人傳承下來的記憶,這就是集體潛意識的由來。這種集體潛意識在動物身上也存在,例如蜜蜂的舞蹈語言、鳥類的筑巢及歌唱等本能,也都是它們的祖先世世代代遺傳下來的。
我們通常說遺傳是由基因決定的,但有形的基因怎么能決定這些無形的東西呢?基因只是指導了蛋白質的合成,決定了蛋白質中氨基酸的種類、數目、排列順序等等,它沒辦法遺傳人類或者動物的群體本能。因此,從遺傳角度來說,基因的作用也許被高估了,而正是因為心靈感應遺傳了更多的信息給后代,才由此塑造了不同的動物風貌。
當然,在如今這個理性占據統治地位的機械式科學時代,“心靈感應”被視為荒誕不經的幻想,從不會進入主流科學家的視野。因此當謝爾德雷克在20多年前推出自己的理論時,很多科學家把他的理論視為胡言亂語。
的確,謝爾德雷克教授的論點不僅奇特,還遠遠超出了人們通常所能理解的科學范疇。然而,我們知道,在量子物理學中,粒子之間有一種幽靈般的“超距感應”,兩個具有關聯的粒子,無論它們相互間的距離多么遙遠,其中一個狀態發生變化,另一個也會即刻發生相應的狀態變化。既然小小的粒子都有幽靈般的感應,那么動物之間、人類之間存在心靈感應有什么奇怪呢?
編輯/佟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