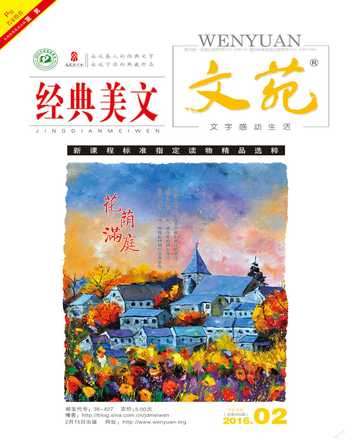摸云
鄭彥英
在我的童年時代,只要不下雨,爺爺都要帶著我,到我家后院看天,沒云的時候,看藍天的深淺干濕,有云的時候,看云彩的厚薄輕重,還有姿勢走向。爺爺每每由此斷定明日甚至以后幾日的天氣,等到我19歲離開家鄉到南方當兵時,爺爺積累了一生的關于天和云的知識基本上已經被我掌握。
我參軍進的是空軍部隊,部隊里就有氣象站,每天報告天氣,逢飛行日,幾乎一小時報一次氣象。我們的干部大都是氣象專家,我記得我們團長豎起一根大拇指,瞇著一只眼,眺著大拇指看向云彩,就能知道云的高低,然后即時決定飛什么科目。
我很敬佩我們團長,但是我沒有機會和時間學真正的氣象,只好一邊遺憾著一邊工作。
記得是1979年春天,我們部隊到前線值班,為了能夠在全天候氣象下作戰,我們團長在一個烏云低垂的上午,決定由8架飛機編隊飛穿云。那時候飛機的導航和雷達都很落后,8架飛機編成的編隊,非常密集,每架飛機之間的距離不到100米,稍有閃失,將機毀人亡。在這種情況下飛穿云,主要是靠飛行員的意念、膽識和技術。
氣象站的戰友告訴我,那天是低空層云,云高600多米,云層厚2300多米,云層內水氣密度高,幾乎伸手不見五指。團長也是這8名飛行員之一,看著他們提著頭盔,排著隊走向飛機時,我的心懸到了嗓子眼。當看到8架飛機直插入云的時候,我的眼一眨不眨地盯著云彩。大概36分鐘后,我看見了呼嘯飛臨機場上空的8架飛機,我至今還記得他們掠空而過的自豪隊形,至今還記得那響亮的噴氣聲音。
后來我調到軍區工作,有一次陪同首長去基層,乘坐的是螺旋槳運輸飛機,當飛機穿云時,我目不轉睛地看著窗外的云彩,才知道云彩如棉花團,子彈一般從窗外飛涌而過,我不禁又想起我們的團長,還有另外7名飛行員,我認為他們就是英雄,雖然這些英雄和我們朝夕相處,如凡人一樣有喜怒哀樂。
飛機飛到云彩上面的時候,我看到了一團團云彩棉花包一樣鋪排在天上,鋪排在飛機下面,浪漫而又壯觀。我很激動,禁不住說:“首長,我們到了云彩上面。”
首長笑笑,那笑容很寬厚,卻沒有說話。我立時想到首長本是飛行員,對于從天上往下看云彩,早已是家常便飯,便紅了一張臉,不敢再吭聲。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期,我在上海《萌芽》雜志獲了獎,雜志社組織我們獲獎作者去九華山和黃山采風。到九華山那天下著雨,車到半山腰時停下了,我往窗外一看,白霧蒙蒙,天地混沌。司機說不敢開了,也不讓我們下車,害怕有大膽的司機開車過來撞住我們。我突然想,我們已經在半山腰了,這些霧是不是我們平日看到的云彩呢?一問司機,司機笑了,說這還用問。于是我推開車窗,伸手去摸云彩。
摸云的感覺很有禪意,看著有滿把的云,一攥,卻一絲沒有,再張開手,云彩還在你手上,甚至還游走,你說它柔軟吧,你無法推開它,反而給你布下無法逃脫的迷局。你想打它一頓解氣,即便是成千上萬的人對著它拳腳相加,也傷不到它的一根毫毛。
就是這般詭異的云彩,我們的飛行員在1979年的春天,密集編隊,穿越直上,瀟灑凱旋。
去年夏天我約了幾個戰友,回訪我的老部隊。部隊的裝備大大高于當年,飛機很威風。當年的飛機小而低,我一抬腿,能坐到控速桿上。現在的飛機大了高了,要搬梯子才能上去。我和一個飛行員說起當年飛穿云的情況,他笑笑說,如今飛機和導航都先進了,密集編隊,穿云越海,小菜一碟。
我問:“如果現在讓你飛當年穿云一樣的任務,你行嗎?”飛行員笑了,指指自己:“生龍!”,指指飛機:“活虎。”
寫到這里,我不禁想到那個年輕飛行員的英姿。
“生龍活虎!”這才是當下最酷的詞!
摘自《解放日報》2015年12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