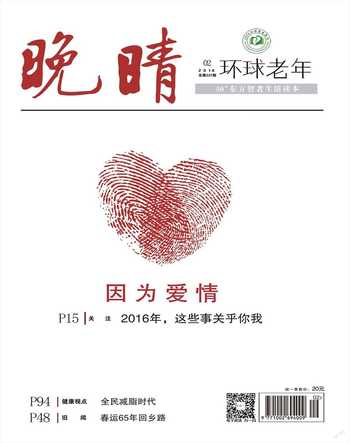從前奏到“潮流”

春運就像一首交響樂,60年中激越悲壯各不同。
五六十年代是春運的“青萍”年代,也可以定義為春運的前奏曲。
這個年代受經(jīng)濟發(fā)展和政治轉(zhuǎn)向的推動力,使得春運在局部地區(qū)有了緊張。主要交通工具也是以鐵路為主,配合短途的棚車和自行車。“這個時期春運客流變化主要受到政策的影響,在解決運輸能力和運輸矛盾時,政策起到了很大作用。”浙江大學(xué)經(jīng)濟學(xué)院副教授景乃權(quán)分析說。
1959年1月11日,《人民日報》發(fā)表社論《對春節(jié)回家旅客的幾點希望》。其中第一點中有“凡是路程比較短、步行一天可以到達的,最好不搭乘公共交通工具,有自行車的盡可能騎自行車,不要去搭坐火車、汽車和輪船”。
但隨著市場經(jīng)濟的逐漸轉(zhuǎn)向,客流的流向也發(fā)生了根本的變化,這樣臨時的方案也逐步退出舞臺。中國春運的客流變化,再次從經(jīng)濟性與政策性共同主導(dǎo)作用轉(zhuǎn)向以經(jīng)濟為主。
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召開,中國歷史開始了新的一頁。現(xiàn)代意義上的“春運”一詞第一次出現(xiàn)在《人民日報》上,春運也開始了新的篇章。
1978年改革開放后第一個春節(jié),由于農(nóng)村經(jīng)濟政策落實,節(jié)前節(jié)后城鄉(xiāng)集市貿(mào)易更為活躍,加上大專院校擴招,學(xué)生回家,知青回城,農(nóng)田水利建設(shè)民工返鄉(xiāng),港澳同胞探親訪友,職工探親密集,構(gòu)成了這一年的客流主力。1979年春節(jié)就達到了1億多人次,增加了200多對臨時客車,但還是“一票難求”。
1983年,春運由各省、市、自治區(qū)協(xié)助鐵路變?yōu)殍F路、道路、水路、航空分工協(xié)作,全社會支持,成為了春運運輸能力層面的分水嶺。
也就是從這一年開始,春運不再是鐵路包攬?zhí)煜拢歉鞣N交通運輸方式都加入了春運的大軍。此前的客流主要是探親訪友、旅行游覽,而隨著開發(fā)大西北戰(zhàn)略的實施和農(nóng)民進城務(wù)工的放開,客流量激增,1984年春運總?cè)舜芜_到6億,1985年春運總?cè)藬?shù)超過7億,鐵路將近1.5億人次。
這也標志著春運從最初的勇進轉(zhuǎn)為奮爭的年代。中國的春運也發(fā)生了“質(zhì)變”,無論哪一列火車,總是一樣地擁擠。
隨之而來的“買票難”便成為這一時期最鮮亮的名詞,在各大城市,買票的“人龍”成為城市的奇特景觀。同時圍繞著車票、服務(wù)和運輸能力的爭端也由此開始。
“當(dāng)年在成都,車站管理者要求買票的人必須一個人緊挨著一個人,后一個人必須抱著前一個人的腰,也不管前后是男是女、是老是少,這樣做不至于有人夾塞兒,也可盡量避免出現(xiàn)混亂。如此一來,幾十條“人龍”從售票處的窗口開始向外延伸,長達數(shù)百米甚至上千米。如果有哪個地方“人龍”鼓出來一個“包”,就被強拉出來。”成都籍張孝祥回想起當(dāng)時買票的情景略帶興奮地說。
“買票難”同時也滋生了中國特有的春運經(jīng)濟——票販子和“黃牛黨”,圍繞著車票的矛盾在原有的基礎(chǔ)上又增加了一項(至今這種矛盾依然存在)。普遍的觀點認為他們加劇了春運的供求矛盾。1986年春運,鐵路開始打擊票販子。
但也有觀點認為“黃牛黨”現(xiàn)象,是相關(guān)制度漏洞的結(jié)果,是將火車票的實際價值以貨幣的形式重新量化,符合市場規(guī)律。春運市場的矛盾實質(zhì)是春運火車票資源的不足,而不是黃牛黨的出現(xiàn)。
1987年春運還迎來了歷史上第一個民工潮春運,鐵路旅客已近1.3億人次,民工潮從廣州火車站爆發(fā),并于1988年席卷全國,最終發(fā)展為春運的另一個代名詞。
1988年《人民日報》刊發(fā)了“全國每天有70萬人站著乘火車”的報道,報道稱大部分列車都超員80%以上,個別列車高達100%。
延續(xù)到90年代,經(jīng)濟體制發(fā)生重大變化以后,以經(jīng)濟發(fā)展傳導(dǎo)的春運現(xiàn)象又有了新的變化。以“民工流”為主力的旅客全民化,成為90年代春運的鮮明特征。
“民工流”成為春運的絕對主力,加之恢復(fù)高考以后逐年增加的學(xué)生流、做生意的商人流,匯聚成了新時代的春運主力軍,浩浩蕩蕩橫掃全國所有鐵路沿線。此時的特點,已經(jīng)不再僅僅是西部地區(qū)擁擠,擁擠已經(jīng)是全國現(xiàn)象。只要有鐵路的地方,就一定有“擁擠”。航空以及公路運輸加進來以后,對鐵路的壓力也不見有多少好轉(zhuǎn)。
進入新世紀,2000年春運時又有了“黃金周”的旅客流匯入,客流不斷增多。惟一不變的是“春運難”以及圍繞此發(fā)生的糾葛不斷。
2001年鐵路春運40天發(fā)送旅客1.26億人次,直通客流首次突破4000萬人次。這一年對春運買票難、黃牛泛濫、服務(wù)質(zhì)量差的報道大爆發(fā)。1月18日,河北三和時代律師事務(wù)所律師喬占祥向鐵道部申請行政復(fù)議,質(zhì)疑鐵道部2001年春運期間部分旅客列車實行票價上浮的行政行為。這場官司以喬占祥敗訴告終。官司結(jié)了,但爭議還沒有結(jié)。直至2007年中國鐵道部新聞發(fā)言人王勇平對外宣布:“從今年起,鐵路春運火車票價格不再實行上浮制度”,圍繞著票價的爭端才告一段落。
2008年3月31日,時速350公里的首列國產(chǎn)化CRH3高速動車組在“唐車”下線,并進入測試運行。高鐵的加入,提升了鐵路的運輸能力,中國的春運也進入了一個高速發(fā)展的階段。
2010年廣鐵集團公司和成都鐵路局共37個車站試行火車票實名制。盡管票價較高,但武廣高鐵已經(jīng)成功地完成了分流任務(wù),春運期間始發(fā)列車上座率高達98%,累計發(fā)送旅客110.8萬人次,日均發(fā)送4.3萬人次。
2011年春運,在北京,客流高峰日的始發(fā)列車坐票和臥鋪票開售不到半小時便全部售罄;在廣東,由于通往廣西的鐵路運力不足,造成買票難,10多萬農(nóng)民工(大多數(shù)為廣西籍農(nóng)民工)騎上摩托返鄉(xiāng)過年;而國內(nèi)首個拼車互助聯(lián)盟上線半月內(nèi)已超過10萬人報名??
為了回家,火車、汽車、摩托車,人們動用了所有能使用的交通工具,相關(guān)部門做出了艱巨的努力,提升鐵路公路運力,然而運力的“窟窿”因為城市化進程的縱深、人員的加劇流動而難以消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