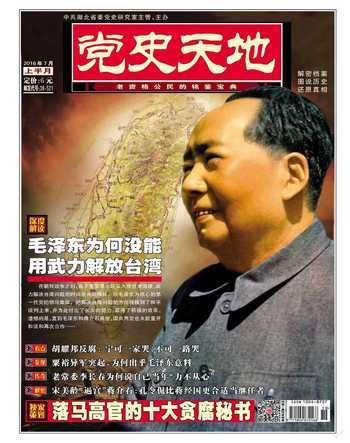1984- 1994:中國取消票證臺前幕后
深圳率先取消票證
1984年11月,時任深圳市長的梁湘主持召開會議,會議議題只有一個:是否徹底取消糧票,敞開糧食供應。
會上有人發言說,全國農村進行改革后,糧食已經出現了快速增長,糧食供應已經沒那么緊張。深圳又有政策先行先試的特區“特權”,何不大著膽子試一試呢?
但梁湘心里也很明白,這不是“試”的問題,而是必須一次成功,所以要把一切問題考慮周到。
如果取消糧食定量供應,首當其沖的問題,就是引來搶購。所以會上決定,通知各國營糧食部門多儲備糧食,提高糧食售價。若發現周邊地區來深圳搶購,再想其它法子應對。
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問題,糧食價格提高了,買糧貴了,職工意見自然會很大。所以,工資也得相應提高。有關部門當場算了筆細賬:1984年的時候,1斤三號大米牌價是0.146元,調高到0.29元,升幅達99%,接每個職工供養系數1.56人計,每個職工每月增加支出4.95元。再加上其它副食品提價,每個職工每個月增加支出13元。會議隨即確定:由于糧食、副食品等提價,按月增加補助給每個職工,在發工資的時候一并發放。由于提高了糧食價格,消除了購銷倒掛,因此財政不會因補貼職工而大量增加開支。
1984年11月4日,《深圳特區報》頭條刊登了這樣一條消息:“經上級批準,深圳市政府決定,從11月1日起,深圳經濟特區(不含寶安縣)取消糧、油、豬肉票證,實行議價、敞開供應。據有關部門通知,居民和機團糧簿上10月底以前的存糧,按原來牌價供應到12月20日止,其中20%的糧食指標可按原牌價換購食油。”
在深圳作家梁兆松的記憶里,雖然山雨欲來風滿樓,但糧票真正被取消之后,市面上反倒很平靜,沒有任何騷動,價格也沒有飛漲起來。梁兆松最初的擔憂很快就變成了驚喜:自己終于可以敞開肚皮吃頓飽飯了,再也不用擔心糧票和定量的問題。
幾年之后,梁兆松更有了新的發現,米缸變得越來越大,自己的飯量竟然變得越來越小,有時一個月連10斤米也吃不完,以前可是30斤大米也不夠!梁兆松心里明白,那是因為肉、蛋、魚、菜、水果之類的東西越來越多了,大米便吃得少了。
至此,深圳特區成功取消票證一事寫進了共和國發展和改革開放的歷程,它比全國范圍內最終取消票證早了近10年,而深圳也成了廣東乃至全國物價改革的試驗場。
票證在全國范圍內謝幕
票證謝幕在深圳演繹的“標本”多少有些特殊,與特區的特殊需要和特殊政策密不可分。
放眼全中國,取消票證的進程則要慢出許多,但時代潮流發展的大趨勢卻是任何力量也阻擋不了的。
在深圳啟動了價格改革之后,廣東開始了在全省范圍內加快改革的步伐。深圳放開糧價取消糧油票,等于放開了統購統銷的政策口子。以此為契機,廣東開始逐步縮小統購統銷的范圍。1985年,廣東將糧油由購銷倒掛改為購銷同價,部分糧油價格放開,實行自由購銷。
1988年,廣東首先放開了食油的價格,并取消了居民供應的定量。曾擔任廣東省糧食局局長的董富勝回憶說,當時省里曾想將糧價也同時放開,但中央認為糧食價格全面放開,對其它省份影響太大,遂沒有同意。
因為廣東歷來是一個缺糧的省份,糧源一直是重點關注的問題。省長和秘書長還曾帶隊帶著外匯或是化肥、白糖等“硬通貨”,到外省糧食產區去采購糧食。
然而開弓沒有回頭箭,4年之后,這一步還是邁出去了。1992年4月1日,廣東在全國率先放開糧食的購銷和價格,取消糧簿,告別了延續近40年的糧食統購統銷的傳統體制,使糧食的購銷走上了市場調節的軌道。糧價放開的當年,廣東財政用于補貼糧食的資金就從以往的約13億元下降到了約6億元。在董富勝看來,糧價放開意味著一個一直被視為經濟領域最大的禁區被沖破了。
“1992年糧價全面放開后,有人說廣東帶了一個壞頭,還有人說是廣東抬高了全國的米價。”董富勝說,他們當時提心吊膽,生怕政策會有反復。這種擔心一直持續到那年10月黨的“十四大”召開才最終消除。正是在那次大會上,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得以正式確立。
之后的一年多時間里,全國各地商品價格放開加速,票證開始逐一謝幕退場。
1993年4月,上海市城市居民購貨本和糧、油、肉、蛋票正式停止發放使用。
1993年5月10日,北京放開糧油價格,取消憑票、憑證、定量供應辦法,糧票停止流通。時任北京市糧食局市場處處長的張寶松回憶,北京除了取消糧票之外,還放寬了辦理糧食關系手續的有關規定,即以戶口為準保留糧食關系,市內遷入遷出不用再遷糧食關系,遷入外省市如果外省市需要糧食關系的,由區縣糧食局辦理糧食關系遷移手續。
到了1993年底,全國95%以上的市縣都完成了放開糧價的改革。
回憶起當年的票證取消,時任國家商業部部長的胡平不由感慨萬千:“1988年,我開始擔任商業部部長之初,李鵬總理曾經對我說:‘胡平,餓死人你是要負責的。但僅僅過了幾年,糧價放開,糧票取消,這和當時糧食穩定增長、糧源豐富,同時國家也建立了儲備制度等關系密切。這是改革開放的成果。”
票證謝幕后的余波
票證的故事并沒有就此打住,結尾的一段波折似乎也不得不提。由于市場尚未完全成熟,就在糧價全面放開不久的1993年底,一場糧食漲價風潮席卷全國。
漲價風潮與當年取消票證的路徑一模一樣,先從沿海區域開始,再擴展到內地,先從南方開始,再擴展到北方,最終波及全國。1993年是取消糧票放開糧價的開局之年,而這年年底,全國許多地區的居民都開始搶購糧食。
搶購風潮迅速驚動中央。1993年12月25日,全國平抑糧油價格工作會議召開。時任國務院副總理朱镕基指出,糧油價格是市場基礎價格,必須迅速抑制目前漲價勢頭,使之恢復到合理水平,防止可能發生的連鎖反應。他要求全國各地必須統一行動,協調一致,立即采取有力措施,堅決把過高的價格降下來,確保市場穩定。
到了1994年春夏之交,糧油價格仍在繼續上漲。為了平抑價格,國家拋售儲備糧25億公斤,儲備油3200萬公斤。陜西省、山東省、安徽省、北京市等地區也陸續拋售地方儲備糧油,但糧油價格仍然居高不下。
在這種情況下,糧票又被請出了山。
1994年年底,全國已有100多個縣市恢復使用糧票。到1995年,恢復使用糧票、糧本、糧卡的地方更多。
1995年6月,位于北京宣武區白紙坊的北京印鈔廠印糧票的機器又開始轉動了。雖然距離最后一次印糧票已經時隔兩年,但工人的業務仍然嫻熟無比。一切流程都是按照當年的程序。沒多久,標號為“1995年7月北京糧油供應券”的糧票全部印刷完畢。
這是按照當時北京市民的數量整體印刷的,可以說是人人有份。與當年略微不同的是,這套糧票是一整張,就像“套餐”一樣配著米、面、油,其中面粉票15枚,每枚500克;大米票3枚,每枚500克;油票2枚,每枚250克。
時隔一年,印刷廠又印制了一批糧票,也是1996年6月號的糧票。這次仍叫“北京糧油供應券”。只是比較一年前又有略微變化:面粉票為7枚,其中2500克2枚,500克5枚;大米票1枚,1500克。
不過,這兩次新印制的糧票最終都沒有與北京市民見面。
雖然市政府辦公會上批準了重印糧票,但真正決定是否啟用卻是慎之又慎的。
“當時市里是給糧食庫存確定了臨界點的,即存量必須保證數月的銷量。”時任北京市糧食局市場處處長的張寶松說,糧食部門很緊張地每天監控市場的情況。當時的市領導多次帶隊到產糧省份采購糧食,北京的糧食庫存始終沒有降過臨界點。
市場漸漸穩定下來,北京最終沒有重新啟用糧票。
至于其它地區恢復的糧票,有的繼續使用了好幾年,也有的在短短幾個月后就被廢除。總之,隨著市場上糧食價格的最終平穩,糧票就再也看不見了。
當中國經濟從貧弱短缺走向繁榮富足,從賣方市場走向買方市場,各種各樣的票證也自然而然地退出了歷史舞臺。
(摘自《光輝歲月:我們的新中國記憶》,作家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