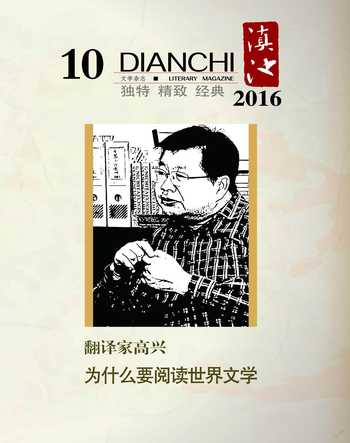一夜繽紛
成都凸凹
尤弘給我講的故事,覺著蠻有意思,暗暗繽紛了好一陣,又覺著不妥。因為這種繽紛是內里的,捂上的,并未敞開來,這就讓人想暗暗也暗暗不住了。今夜沒事,就將這個故事講出來,你,以及想聽的,都可聽聽。以我對尤弘的知根知底,可以肯定而負責地說,這個故事,可信。
尤弘說他不做汽車了,我大吃一驚。上次來省城玩時,還說看好汽車呢,這才幾個月,就撒手撂了場子。我說,那,那,不做汽車,做啥?他說,做摩托。我說,只做摩托?他說,只做摩托。
一陣風一陣雨,東一榔頭西一棒,商人嘛,一個德性,不足為怪。尤弘是商人,可他不是這樣的商人吧?
尤弘小我三四歲,是我連襟。西南財大畢業,天資聰慧而脾性篤厚。畢業后,先是在縣城農行討俸祿,一討數年。后又響應農行號召主動辭職,回到老家 L市,開起摩托行。期間,娶了我那公務員身份的漂亮的小姨妹。他們有個溺愛得成天泡在網游中的兒子,這不,小姨妹剛才還向我發招,讓我給妻侄在省城找一像樣的初中讀呢。因為小姨妹姐姐,也就是我老婆在省城,尤弘和小姨妹就常往省城跑,我家都成了他倆的駐省城辦事處了。連襟的摩托行開得紅紅火火,幾年下來,成了 L市三區四縣摩托行業的龍頭老大,行跟著變臉,早變了公司。前年吧,又新增了一塊業務,玩起了汽車的營生,他說,光摩托不過癮,要做,就做大家伙。那不當回事兒的口氣中,藏有說不出的豪邁。
我問,咋個又不做汽車了?賠啊?
尤弘說,賠啥賠,賺啊。又說,可這錢賺得啊,讓人不安生,心坎兒七上八下,毛焦火辣的。
接下來,就是尤弘給我講的,我決定講給你的那個蠻有意思的故事。
上午,我給太平縣邱老板打電話,說車到了,需不需要公司給您送去。邱老板財大氣粗地一笑,不用了,我反正要去市里辦事。尤總,這樣吧,下午提車,我親自來提。
太平縣離 L市也就一個多小時車程,加上市里辦事的時間,邱老板早該到了。再說,邱老板接電話時,沒準就在 L市呢。打電話問,邱老板說馬上。整個下午,一等不來,二等不來,都到門市打烊的點了,邱老板才馬上現了形;形是人形,高一米七,均寬四十九公分,重一百八十斤。
人形近了,背后又現出一人形。聯想到邱老板的陣勢,我把邱老板背后現出的這一人形歸為私營企業家女秘一類。
比邱老板的形先到的,是一連串真誠道歉的聲,哎呀,尤總,不好意思,讓您久候了。您曉得的,咱們這號人,鬼事多,剛提腳一個事,剛提腳又一個事,弄得老子提個車都提不清靜。尤總,要不,這就驗車?
我是真誠地餓了,但見客戶真誠如斯,急忙應道,好哇,驗車。喏,發票,合格證,鑰匙。一邊說一邊將手上的東西遞出去。
邱老板接了東西,并不像大多數客戶,鉆進車子打火,一踩油門,試駕一圈,再踩油門,走人。邱老板退后幾步,像踩蛋的公雞圍著車子繞圈子,他在看漆水,更是在做全局性目檢。又前進幾步,前蹄撐地,屁股撅起,伸個鵝脖子在車下晃,看底盤是否漏油。
這架式,老鬼。
媽的,不就一破帕薩特嗎,何至如此細心。心說,看來,沒一二小時,歇不了氣。口說,邱老板,這都過飯點了,要不,我請您殺館子……邱老板截了我的話頭,催我吧,尤總,該不是這車……我急忙申辯,不急,您慢慢驗,慢慢驗,我就是怕您肚兒遭了罪。邱老板說,要不,你們去吃,我再瞧瞧?我說,邱老板,您要不介意,我喊幾個盒飯吧。
邱老板一邊扒盒飯,一邊驗收,我和員工小殼鉆、歡喜頭兒一邊咽盒飯,一邊陪邱老板驗收。
是零公里吧?邱老板站在車外,身子拱進車內,插了鑰匙,并擰了半圈。零公里,是邱老板訂車時提出的要求。他知道公司必須去五百公里以外的省城接車,怕接車員瘋跑,傷了磨合,就提了這要求。對客戶提的零公里要求,公司有的是辦法滿足;斷開液晶里程表電路,拔掉機械傳動式里程表軟軸,怎么著都行,因此立即就應諾了。我說,表上顯著呢,二十來公里,算零公里吧。
我說,為了這零公里,我一拉摩托的大卡,一半車位,都給了你。
我說的是實話,同時打了個冷噤,心想,這活兒幸好做得實,否則,遇到這姓邱的,不栽才怪。
果然,他點了火,三分鐘后,又熄了火。之后,打開引擎蓋,拉出機油尺,并用一張雪白的紙巾裹著輕輕擦拭、抽動。看了紙巾色澤,才扣合了引擎蓋。
驗了零公里,這才開始試車。我看見車子動物般低吼著,沖出去,一個拐彎,不見了。莫約半小時,車回來了,從另一個方向回來了。另一個方向是西邊,一段坡道。一輛車子,不知哪個愣頭青開的,逆著晚霞,呼地闖了來,離我一米處,釘在地上。開你媽個球,我和倆員工正待爆粗口,卻見邱老板開了車門。
此后,查驗備胎,以及包括千斤頂、兩用螺絲刀、小扳子、輪罩拆卸鉤、換胎定位螺栓等在內的隨車工具。將橘紅色三角指示牌抓在手上,掂了掂重量,又拿狗鼻子嗅了嗅。最后,比著合格證、三包服務卡和三聯發票,看了發動機號、車架號、出廠日期。
邱老板終于折騰完畢了,我也終于松了口氣。出于虛偽的禮貌,更出于優良的職業習慣,我說,邱老板,您看天,眼瞅著就黑了。要不,車擱這兒,住一宿,明天白天走?邱老板立即說,那怎么行,好不容易驗了車,明天走,再驗一遍,背工了。我哭笑不得。嘴巴一張,一不留神放個屁,竟讓人覺得不懷了好意,媽的。彌補是必須的,我說,這樣行不,您非走不可,我派個司機,小殼鉆,幫您開吧。小殼鉆的車開得挺棒的,以前開出租,全市都有名。點小殼鉆,不點歡喜頭兒,除了面上的車技原因,主要出于性別考慮。女的,又年輕伸抖,不方便,更不安穩。雖說有女秘在側,可誰知道危急時刻女秘會站在哪邊呢?現如今的女秘,什么情況都可能發生,哪有靠譜的!小殼鉆聽老板這樣評薦自己,望著客戶靦腆地笑。小殼鉆肯定不想多這一事,任何員工都不想,但公司的出車補助會讓他們想的。這點基本面上的自信,我是有的。邱老板也笑了,但不是對著小殼鉆,他一邊對著歡喜頭兒和女秘笑,一邊對我說,尤總,您該不是懷疑我的技術吧?又說,我的本本,都跟了我二十年了,在部隊,我當的是汽車兵。我說,難怪邱老板對汽車這么在行,比我這個吃汽車飯的都在行啊。
我說,如果所有客戶都像邱老板這樣在行,吃汽車飯的,恐怕只得吃稀飯哦。又說,但正是邱老板這樣的買主,磨礪并成就了我們公司的優秀與聲名,嘿嘿。
聽了我撓到癢處的連吹捧帶譏損的話,邱老板非但不惱,反大悅了,渾身上下透出的無怨無悔舍我其誰功德圓滿的氣息,嘩一聲罩過來,讓我們三人一下置身在他的氣場中。
小殼鉆是不想出車的,但真讓不出車,又不舒坦了。他瞄了身邊歡喜頭兒一眼,又對著飛跑的帕薩特屁股,狠狠吐了一大塊硬如石子兒的黃澄澄的濃痰。我也想吐的,但不能吐,至少不能當著員工的面吐。雖不畏邱老板的耐心與精心,但討厭。他一路驗下來,好像不是驗車,而是驗我心頭的鬼似的。我也是一個睚眥必報的主,小殼鉆的一口濃痰,就像幫我吐的,隨著濃痰響亮落地,我的喉管與肺葉活絡多了。
這時,西山上的最后一抹夕光已對 L市說了再見。
回到家中,天,完全黑了。不到五分鐘,我的眼睛已適應了客廳落地燈與電視熒屏拼盤出來的戶內光。
手機籠子里的鳥兒叫得尖端而柔媚。以為是打牌電話,并不急于接。一看,是陌生號碼,更不急于接。但電話得理不饒人不知疲倦舍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的長鳴,讓我感到了一絲不快,和一絲不祥。
電話是女秘打來的。女秘說,邱老板出車禍了。
注意了一下時間,八點三十五,邱老板離開公司門市已一小時又三分鐘。可以不理睬這個電話的,正像那些個神馬銀行規定的當面點淸離柜不認,但我做不出來。客戶再討厭也是客戶;只有妓女才不把客戶當客戶,回回都是一手清,成都府到華陽府——現(縣)過現(縣),剛賺了人家銀子,籠上褲兒就不認人;何況人家邱老板還讓女秘揪住了我。
到了現場才清白,邱老板出車禍,出在了別人身上,他自己屁事兒沒有。女秘有點事,車子急剎,打歪,人斜著前沖,導致軟軟的右乳房撞上了硬件。倆人出禍而無禍,得益于安全氣囊按照設計者要求,在該彈出的時刻彈出來了,并且彈到了適當的點位上。被車禍禍了的別人是一老頭,看打頭,鄉下人無疑。嗣后,碰到邱老板,他跟我神侃,說女秘給我打電話時,從開始到結束,都是騰了一只手,一邊搓揉右乳房一邊打電話。尤總,你沒聽見她的哼哼聲?邱老板話畢,好一陣壞笑。
放下女秘電話,飛快打了小殼鉆電話,讓他帶三支手電筒,接了歡喜頭兒,就來接我。下得樓來才知道,天已經黑得發白了——天把月亮都黑出來了。一道車光打過來,隨即變成近光,小殼鉆、歡喜頭兒到了。小殼鉆以正宗一百二十碼的速度在高速公路上跑,跑到車禍地點,用時四十一分鐘。小殼鉆一邊靠邊停車,一邊咕嚕,媽的,狗日的邱老板沒飆車嘛,咋個出情況了?又道,對,一定是了,這家伙一定是跟那小娘們調情,調出了情況。
一下車,就在右手邊即公路東側護欄處看見了邱老板和女秘,但兩人就像沒看見我一樣,一個招呼沒有。這只有一個解釋,他倆拿我當陌生人,或我自成隱身人了。
直到這時,站在車禍現場,我才恍惚過來,咦,我來這兒干啥?
鬧不明白,你邱老板出車禍,喊我這車商有球事哇?你說是車的質量問題,可以找我,再由我找廠家,可你都仔細驗過了,確認了,還來纏我賴我干啥?就算真有質量問題,也該是質檢部門找我才對。出車禍了,第一時間該找的,永遠是 120、交警、保險和修理。這樣一想,就覺得女秘的電話來得有些詭譎。但電話千真萬確是女秘打的,女秘的長相,我的眼睛認得,女秘的聲音,我的耳朵認得。
邱老板、女秘喊了我來,卻不招呼,更不安排事,對此,我的理解是,讓我看著辦。從事后的情況看,以及種種跡象表明,我的理解基本正確。
于是,開始看著辦。首先看交警,只要看見交警,一切都 OK了,交警會辦妥一切的。還好,在車燈、手電和月光的照耀下,加之那與眾不同鶴立雞群的裝束,一眼就看見了交警。一,二,三,對,兩男一女,仨交警。兩男的,一胖一瘦。我看見女交警、瘦交警拿著手電筒、記錄本和相機,拉著這個問,拉著那個問,一邊問,一邊記。剩下那個傻里巴嘰的莽大漢胖交警,則扛著一臺攝像機,東瞄西瞅,點射,或成扇面掃射。
奇怪的是,現場所有的人,都對交警視而不見,他們無不顯得十分繁忙的樣子,凡被交警扭著問話的,更是顯出了不耐煩的動作。其實不光他們,連交警的工作也是一半認真,一半不認真。交警拿不認真的那一半,認認真真地跟大家伙兒忙著同一件事:望天、蹦跳、啊啊啊瘋子般嘰媽日怪地叫。
我、小殼鉆、歡喜頭兒莫名其妙,這讓咱仨像了局外人,相對于集體的瘋狂,咱仨的不瘋狂,反似瘋狂了。
突然,所有人都盯著小殼鉆叫了起來,是那種既替人著急,又幸災樂禍的叫。他們一邊叫,一邊用手指點著小殼鉆的頭。順著他們的手指,我看見小殼鉆頭發上粘了一小片紙。小殼鉆終于明白了大家伙兒的意思,伸手在頭上摸找,抓住了小紙片。我湊近順手電光一瞧,看見小殼鉆手上拿著的,是一張燒了一只角的人民幣,再看,卻是一張萬元陰幣。顯然,這張萬元陰幣來自天上。
拿眼望天。看見空中稀稀拉拉零零星星懸浮著沒有燒盡的或殘缺或完好的黃紙、陰幣和一些冥具。它們隨風飄動著,朝著大致的西邊,一些飛走了,一些又從東坡樹葉上、草叢中飛了來。還有一些在空中翻跟斗,爾后再慢慢悠悠似墜非墜地墜下來。事實上,高速公路地面上,已有不少陰曹地府用物什了。原來,大家伙兒忙碌的,就是抬頭望它們,并蹦跳著躲開它們,免得冥物上身。
本來,這該是件莊重肅穆而虔心重大的事,不知怎么了,卻被面前這幫屌絲弄得像了娛樂乃至狂歡。這幫屌絲由司機、乘客、當地農民,以及車禍事主、公干人員等構成。歡喜頭兒在哪兒都像他的名字,甚至比名字還萌,早撇下我和小殼鉆,與屌絲們一起歡喜去了。
這才明白,邱老板、女秘不理我,原來根兒在這里,他倆也忙啊。
一陣更大的風刮來,大得連地面上的冥物也抖擻起來了。一時間,滿天的黃紙、陰錢以及紙做的衣褲、房宅、美女、手表、電視、手機、空調、書籍、臘肉、酒瓶、眼鏡、皮鞋、足球……繽繽紛紛,如天女散花一般。
大家伙兒一方面為避開冥物,躲閃騰挪,太極八卦,降龍十八掌,什么都用上了,一方面為進一步狂歡,又亦步亦趨追了冥物而去。幾乎沒想,我也加入到了全面的集體狂歡中。幾乎不覺得,望著天上的冥物,竟越了公路中央隔離帶,出了公路,順著山溝,跑到了一大片村宅農院附近。只顧眼球、心跳,何曾想到腳也會附從,隨了風的方向。
農院的場面令人震驚,我這輩子應該是不會再能遇到的了。
冥物飛向農院,完全像一場有預謀的進攻。而農戶對冥物的撲打,也與一場城堡保衛戰無異。只不過,前者有風在指揮,后者卻像各自為戰。準確地講,后者也是有指揮的,那個站在院壩打谷場中央哇哇亂叫的族長一類的人物,那些分門別戶的貌似權威的家長,都是。問題是,面對神出鬼沒出神入化的黑黢黢陰煞煞的風,他們的指揮,基本無效,甚至更似笑料。這樣,所有的人,都成了指揮官,既指揮別人,更指揮自己。我們這群狂熱的過客,隨風而至后,也加入到指揮官行列,站在田坎上,動嘴動手,像薩滿一樣又唱歌又跳舞的。歡喜頭兒更甚,也更野,直接折了一枝大柏椏,雙手掄著,沖到了院壩上。
風指揮冥物,同時也應該是被指揮了的。神、鬼、上帝?不得而知。冥物們一會兒集中兵力成一豎刀,猛剖一處,企圖破城而入,一會兒又散開來成一橫棍,千軍萬馬層巒疊嶂鋪排掃來;一會兒猶疑著,不進不退,一會兒長驅直入,一會兒退避三舍;再一會兒圍點打援移花接木暗度陳倉,再一會兒聲東擊西引蛇出洞黑虎掏心;把三十六計七十二招掏出來一陣排列組合使了個遍。
這可苦煞了農戶這邊。為了不讓冥物附自己的體,上房子的身,不論男女老少,都手持了器物。或帚把,或布具,或雨傘,或蒲扇,或蓑衣,或魚網,或簸箕,見了冥物近身就舒展猿臂瘋狂撲打,一心只管把冥物往別處攆,實在攆不走的,就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腳,直到掃地出門方才罷休。后來我聽說,一個多小時前,冥物鬼子一般摸進村突襲這里時,有人來不及拿器物,只剩跑。前邊舍命跑,后邊拚命追。其中一人最過分,跟斗撲爬狼狽了兩條溝半匹山,才躲過了一劫。老人婦人在地面,少年青壯在屋頂,關門閉窗,各家自掃門前雪,整個架式森嚴壁壘。巷戰、陣地戰、坑道戰、狙擊戰、麻雀戰,乃至空城計,乃至誘敵深入十面埋伏,什么都使盡了,總之,怎么好使怎么使。顯然,他們戰斗很久了,往常這會兒,已是睡死打鼾的點了。這還未夏天呢,加之還是晚間,他們一個二個都弄成了汗人。汗在身上,吃了鄉野土塵與燒紙灰,整個人完全灰里灰氣花里胡哨形如鬼蜮了。但勁兒還在。他們的勁兒仿佛筋絲特好的面筋,風與冥物有多長,面筋就有多長。
怪古日精的風,突然人間蒸發。
不走的冥物摟著泥土睡去,一點氣色沒有。月光打下來,讓一下子無事可干的月下人,一臉煞白。
無事可干的時候,每個離開高速公路的異鄉人終于想起自己此行目的,并喃喃自問。
回到高速公路,才發現邱老板、女秘、三個交警并沒有跟風離開現場。他們身邊還有兩個疑似保險公司的人。壓斷高速公路的沒有車主的汽車,像攤開的東北大餅,更像南方的牛屎堆,讓他們一籌莫展,折磨得夠戧。我上前與邱老板打招呼,他竟仰頭望天,傻兒巴嘰的樣子。歡喜頭兒見狀,耳語我道,這家伙該不是嚇癲了吧。我說,至于嗎,不過,也難說,越是看上去能干的龜孫,越是經不得事兒。
找到女秘說話。
女秘,天生尤物,何其玲瓏曉事,見我走來,不待我開口,就先自把朱唇啟了。
老板提了新車,心頭高興,出城,拐上了高速。老板開得并不快,他想開快來著,路好車好的,考慮到磨合問題,剛把油門轟大,又松了腳。就是這樣,老板也開到了一百碼。也怪我,沒我在車上,老板至多只會開八十碼。老板說,今兒高興,為了我,咱飆回車,多開二十碼。我沒理他,只管作甄嬛狀賣萌賣笑。高速路沒路燈,但車燈很好,月光很好。為了少聞些車箱里新車的甲醛味,老板開了頂窗,我還嫌不夠,又開了小半扇門窗。為了氣氛,老板插了一張歌碟放起來,我喜歡的,老板專門為我買的。為買這張歌碟,老板牽著我跑遍了 L市所有的音像店。這樣,心情就別提有多爽了。是的,一定很爽了,不爽又咋個你來我往,老板菊了我一口,我啄了老板一嘴呢。尤總,你可千萬別想岔了,車禍與親嘴,那是八竿子打不著的事。因為出車禍前,老板開得可規矩老實了。老板開著開著,山坳處,一個拐彎,我突然看見前邊路上有一團黑影,老板應該也看見了,我精喳喳叫了起來,但來不及了。車子殺過去,一下子把黑影撞飛了出去。先是向上飛,在空中打旋,再是側后飛。車子從黑影下邊穿過,開了好長一段,才一頭撞在右邊路欄上停下。
見我和女秘在一邊說話,歡喜頭兒、小殼鉆就一前一后梭了過來。聽到這里,歡喜頭兒塞了一瓶礦泉水給女秘,這意思很明顯,既是對前邊已講故事的嘉勉,又是對后邊未講故事的鼓勵。看得出,女秘不想喝的,她想一口氣講完呢,出于禮貌,還是喙了一口。我狠狠剜了歡喜頭兒一眼,歡喜頭兒調皮地奓了嘴洞,故意讓猩紅的舌頭吊出來,長長的,像鬼。因為礦泉水的打岔,女秘醞釀了好一會兒情緒,才接上了先前的氣口與話茬。
帕薩特撞上黑影時,先是嘭地一聲沉悶巨響,跟著就是噼里啪啦的鞭炮聲與煙霧,隨著鞭炮聲與煙霧出現的,是滿天飄起了無數火球般的小玩意兒。車子咣啷一聲撞上路邊鐵欄桿后,安全氣囊呼一聲彈出來,罩住了我和老板。
見老板不動彈,以為出了人命,我一下蹭出車子,繞車屁股轉過去,把他扯了出來。老板以為自己死了,被我扯出后,才知還能把氣出順,這還不止,他啥事沒有呢。也不是沒有,他是嚇壞了,你們看,到現在都沒緩過神來。我還算清白,見老板沒事,把他扶到鐵欄桿上靠著后,就急忙拿手伸進駕駛室,摁亮了應急燈。還想做別的事,但天空的奇觀容不得我分身。
滿天的小火球,不,滿天小星星,密密匝匝,紛紛揚揚,它們在夜空中歌舞,月光下繽紛!
定睛望去,小星星更像一些小火炬,被風舉著,跑向風的目的地。它們的周圍,還有一些晦暗的飄浮物,一碰觸到它們,也成了它們,傳染的勁道不亞禽流感。大家伙兒有時糾葛在一起,抱團成了更大的火炬,有時更大的火炬散開,又成了無數微塵般的遙遠星子。一輛一輛汽車的停下、經過,讓我的詩性與浪漫受到影響。幾乎沒有想,我打了 110。對 110,我沒有提治安,我說的是車禍,高速路上的車禍。打了之后才想起,該打 122的。之后,打了保險公司和尤總電話。是我陪老板買的保險,保險單在我這里,我知道號碼。
大約因為鞭炮聲太響了,很快,就有附近的農二哥、村姑等飛叉叉跑了來。他們先是被繁花似錦的天空奇觀震驚,繼而開始猴跳一般躲著從天而降的飛物。經過的車輛,被眼前的異象吸引,靠邊停了。后邊的見前邊停了,究竟也不問,跟著就停。這樣,所有北來的車都停了。后來,不想停也沒法了,因為前邊的車已擺滿了所有通道:主車道、快車道和應急車道。隔離帶另側,南往的車見了,也停了部分,對,就是特別熱愛生活的那部分。司機乘客從車中走下來,立刻被免資的刺激活動刺激,像投身大革命運動,紛紛投身其中。
一些農戶像突然反應過來什么,沿著小火炬飛去的方向撲去。他們要超過飛物,撲到飛物的前邊去。另一些農戶望著他們逃命似的奔跑樣,笑了,笑得山搖地動陰風煞煞莫名所以。笑過之后,繼續狂歡。不久,就有一撥農戶停了下來,沿著先前那些農戶奔跑的方向去了。天上的火炬漸漸少了,小了。但還是滿天飄著,只不過成了無火的火炬。
農戶一來,大家伙兒就知道了奇觀的真相。原來,隨鞭炮飛滿天空的,系冥界使用之物,黃紙、陰幣,等等。它們被鞭炮炸開,引燃,形成滿天星和空中小火炬。看看癱瘓在一邊的破了相的帕薩特和蔫不拉嘰六神無主的老板,農戶們即刻推斷出,是誰制造了這場奇觀。此刻需要知道的,是誰將冥物帶到了高速公路上,并與猛虎一樣的帕薩特產生了聯系。這個人,現在,在哪里?問老板,老板搖頭,問我,我搖頭。于是,農戶們以似若挾持的行為,招呼老板和我與他們一起找人。
我已經清醒地知道,我們要找的人,就是我和老板車禍前看見的黑影,也是那嘭一聲沉悶聲響。
按照我的比劃與描述,農戶們開始找。現場的其他人,依然狂歡著,后來停車加入的人,扭著前邊的人說情況,前邊的人,一些傲慢無比自顧不暇,一些像打了雞血針一樣興奮,一講就講得沒完沒了扭著對方不放把對方折磨得不行。
我們還沒找到黑影,縣交警就到了,跟著,保險公司也到了。找從高速公路上飛出去的黑影,是他們的專業。果然,一會兒功夫,找到了。
一看,差點嚇暈死過去。早知道黑影是這德性,恐怕真不敢擅作主張,打了這電話,又打那電話,招呼了一大群拿繩繩的爺。偷偷瞟了一眼老板,他的雙腿,竟成了篩糠的篩。我想,他這熊樣,只怕想當逃逸者也當不了。再說,那車能否動彈,能否助紂為虐,還兩說呢。這樣一想,心也安順了。
黑影呈人形。女交警上前伸倆并攏的手指探了黑影某個部位,說,沒氣了。拍照、攝像,白光如微型閃電,閃個不停。
瘦交警抓過胖交警手上的礦泉水,連同自己的一瓶,旋了蓋,倒豎在黑影上方。兩股清冽的從天而降的泉水流下來,流下來,黑影在流下來中有了人臉。
黑影是一農民老頭,六七十歲吧。他背著一海大的背兜,坐在公路東岸的山包上,活像一活人,累了,坐下來,倚著背兜歇氣。女交警說,老頭哇。又說,如果是青壯,或許還有戲。老頭從頭到腳灰撲撲的,局部地方黑似鍋底,比如礦泉水抵達前的腦球部分。背兜已炸得不成形了,一根背帶已斷,但另一根依然環在老頭肩上。背兜里還有一些炸散的冥物,在不停地起飛,越過高速公路,飛向西邊。山包附近零星有幾堆冥物,也在聞風而動。冥物們走在空中,隆隆重重,軒軒昂昂,嘰嘰喳喳,像小學生排隊齊步走。女交警指了天空,又指著背兜分析說,這老頭背的黃紙陰錢什么的,不知冒出背兜好高,至少比他人都高。
交警開始問身邊的農人,死者是誰。開始一個交警問,接著兩個,最后三個,再最后,老板、我和保險公司的全上,分頭出擊,逮了人就問,但沒有一個人認識面前枯坐的尸體是誰。
保險公司兩人一直在協助交警工作,他們用皮尺測了車禍地點到尸體坐落地的距離,三十四米。由于在山包無事可干,我們回到了這兒,高速公路上。在這兒,交警和保險公司又開始忙他們的工作,我和老板就傻呆著,看稀奇。
后來的情況,不用我嘮叨了,因為這當口,你們來了。
你們可以走了。你,對,就是你,得跟我們回去。
我回頭一看,是交警在不遠處對著我們喊話。整個高速公路上,除了車禍相關人,再無一閑雜人員。原來,在女秘給我們講情況時,交警已完成了疏通公路、疏散人群的任務,并與保險公司倆人達成合作協議:保險公司守尸,交警解決糾紛定案時適當向保險公司傾斜。此前,交警嘗試雇一二農民守尸,但出到近千元也沒人接招。如果出價一直高下去,估計會出效果,可那樣的話,就該交警自掏腰包了。交警當然沒有這樣傻蛋,即或傻如胖交警者,也沒有。
交警喊的你們,是我、小殼鉆、歡喜頭兒以及女秘。你,是邱老板。
顯然,輾死人的邱老板被控制了。
怕電話響起。怕交警、保險、質檢、事主給我打電話,好在,沒有。這事就算與我無關了。
這事就算過去了。出了這號事兒,誰還腦殼長包自個兒往渾水里趟?那天去現場,已是鬼迷心竅糊涂得見鬼的事,我是不會讓自己在同一條溝里翻第二次船了。可,小半年來,公司時不時冒出的怪事,卻讓我改變了主意。我還是想了解一下那個車禍后來的情況。撥太平縣邱老板電話,關機,后來得悉是換機。當撥通女秘電話的那一刻,才明白,我是一直想打這個電話的,只是不愿承認罷了。出于好奇,人道,還是什么,不知。也許兼而有之吧。
雖然女秘的敘述如作秀如臺詞,但敘述的內容還是讓我震驚,同時無言以對。
天一亮,就該做接下來的工作了。對交警和保險而言,接下來的工作主要有二,首先辨尸,確認尸源,而后定案追責理賠。邱老板、女秘也去了。邱老板是被迫心甘情愿去的,女秘是沖著邱老板自個兒去的。車禍地點離太平縣城很近,距離不是問題。大家伙兒手持老頭照片,走村串戶,一天下來,毫無結果,車禍現場方圓十里,沒人識得老頭。發揮基層組織作用,增加人手,范圍擴大至方圓二十里,又找了一天,依然沒有斬獲。同時,墻上紙上的,媒體網絡的,尋找尸體家人啟事,滿天飛。
家人不至,尸體沒人領,沒人埋。就算找把鋤頭來挖坑代埋,可哪一塊地準許你挖和埋?要是夏天,尸體早有味了。但再下去,該來的,就該來了。這燙手湯圓被保險公司捏著,想甩甩不了,喊天天不應,喊地地不靈,冤得不行。
老頭是誰呢?他背那么多冥物,是自用,還是他用?如果是自用,那他家里在陰曹地府扎堆的人,真夠多的,又或者這家人喜歡把一年的冥物一次置齊,反正有余資,又省得冥物漲價。如果是他用,則老頭家一定開有冥物店,做買賣用的,因為沒人懶到連冥物這號殊品也托人從縣城里代買的程度。老頭應該是在太平縣城購的冥物、鞭炮、香燭、火柴等,搭班車回的場鎮,此后背著冥物甩火腿回家,而家在高速公路另側,而老頭又不想繞遠路走天橋,這就遇了帕薩特。大家伙兒分析來分析去,一圈一圈轉,總也轉不出來。決定不再分析,繞開首先找人這一常規程序,直接進入理賠程序。殺豬殺屁眼,名有各的殺法。這一次,殺的就是屁眼,但殺對了。一刀捅進去,尸源出來了。
出于傾向弱者和從人道主義原則出發等理由,將對車禍死者家人賠付人民幣四萬元。消息甫一傳出,車禍現場附近三個村的村委會主任風風火火來了。
三位主任都說,認得死者,是咱村的,家人忌出面,委托本主任代為理賠。第一位主任說完,交警正待辦理,第二位主任來了,交警傻了,第三位主任一來,交警徹底傻了。交警的殺豬真理,為交警織了個套。但最后來的這位主任為交警解了套。他兩字一頓,直接對先他而來的兩位主任同志說,這錢,你們,也敢,詐吃?你們,也不,怕那,地府,上門,追討……話沒頓完,兩人早遁沒影兒了。
有人接了招兒,也就意味著,保險公司再也不用嗅尸臭味了。村主任三刨兩卸,就協調出了一塊墳地兒。這墳地兒就是老頭最后的坐落地。這樣也好,去陰間,不兜圈子,不走冤枉路。老頭死前折騰大了,死后就不再折騰了。
公司小半年來,冒出了這樣一些怪事。
歡喜頭兒駕車,見紅燈亮,停下。卻見擋風玻璃前,一車輪匹馬單槍滾滾向前,獨闖紅燈去了。歡喜頭兒樂了,兩排牙齒裸露得像月光肉。綠燈亮,松剎,一檔,起步,二檔,車繼續前進,但,不正常了。停車,下車,一看,自己車子的右前輪位置,只有車轂子,哪有車輪子?抬望眼,那車輪竟跑去撞上了一英俊交警的屁股。
公司一員工開車,一個超車加速,車子猛地前竄,員工竟將方向盤提拎了起來。又一員工開車,一個拐彎,車上竟甩了兩人出去,副駕座一位,后座一位。前后倆右車門莫名開了。
我是在一個晚上出的事。車開著,突然就打歪,怎么轉方向盤都無用。車子躍上護坡,向懸崖邊沖出。我嚇得七竅少了六竅,想,等著死吧。突然,黑影一閃,咚一聲肉響,車抖了抖,停了下來。事后得知,原來,有家農戶,丟了一頭大黑牛,不想卻在懸崖下找到了它一摔八瓣的尸身。記得小時候聽外婆講過,她的老輩子曾救過一個叫黑牛的小伙子的命。難道,替代車子下崖的大黑牛,是小伙子隔了幾代的托身,并應上了我的身?
最奇的,還不是我遇到的大黑牛,而是殯儀館的一輛運尸車。這事兒就是上個月發生的。運尸車從市四醫太平間拉了尸體,前往火葬場。路上,鬼使神差,一人不知咋的竟被卷入了車底,當場壓死。這樣,運尸車都不用叫,將就這輛車,新的尸體搭了便車,與車上尸體作伴,被送去了火葬場。據說這新的尸體未成為尸體前,有疑似自殺傾向,但不確切。小殼鉆是這輛運尸車的新任司機。高速路邱老板車禍不久,小殼鉆跳了槽。也不怪小殼鉆,甭管賣啥車開啥車,薪酬翻番,任誰也得動心。
蹊蹺了。不敢再耽擱。聽了女秘的介紹,我一個人去了花蕊山中一座隋末老寺。老寺之行,讓我知道了六個字:命犯四,與二和。想多求一字,無果。下山后,我把自己關在賓館想了一周,才想出了一些眉目。總體的意思是,凡沾四的人、物、事,都對我不利,凡二,皆好。真是不理不知道,一理嚇一跳。一周下來,竟理出了一籮筐四!邱老板車禍那天,是清明的頭天,四月四。我四十歲,邱老板四十四歲,壓死那老頭六十四歲……汽車是四個輪,公司汽車業務板塊四個股東。摩托車兩個輪,我老婆倆酒窩,我十二歲學會騎自行車,二十二歲那年學會駕駛兩輪摩托……想通這一切,我打了幾個電話,其中一個電話,打給了公司法律顧問。從賓館出來后,我一下子又回到了純粹的摩托老板身份。
如此說來,連襟尤弘甩了汽車生意不做,正常了。
尤弘講,來成都前一周,他還在 L市街頭偶遇了邱老板。邱老板不想提車禍的,但聊到女秘后,竟然一下來了聊性,且是那種很亢奮的聊性。看來,他在車禍現場被嚇著不假,但要說他在哪個方面都被嚇著,就假了。以開快車著稱的邱老板,如今以開慢車著稱。以前,一上高速,就因為超速扣分罰款,如今卻因為低速扣分罰款。至于夜間行車,早戒了。
不可否認,連襟的故事的確吸引了我。我想知道的是,他講的故事,有無胡吹亂侃扯謊成分,是高于生活,低于生活,平行生活,還是等于生活?之所以說到低于生活,是因為他把故事,都講到地的下邊去了。這都不叫低,還有啥子叫低的?你說是不。
責任編輯 包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