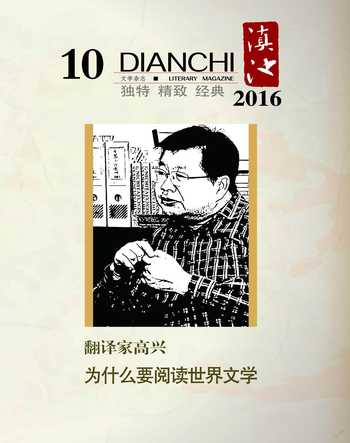無法抗拒
李達偉

1
那是后珍小時候的照片,拍攝于十多年以前。在一個魚塘里,后珍站在竹筏上,水流清澈,水中有古木綠竹藍天。那張照片向我呈現著自然世界本身的豐盈,光與影的組構,以及一些可以無限延伸的東西。這是在哪里?村寨后面,奘房前面。奘房是傣族對廟宇的稱呼。傣族的奘房往往在樹木繁密的地方。
一片近乎與照片中一樣的自然,呈現在了面前,那些古木綠竹甚至比照片中更蔥蘢繁盛茂密。有一種恍若昨日的感覺,多少讓人感覺有點不可思議。那個魚塘曾經被人承包了一年,那年魚塘里面的魚比往年肥比往年多。但有人投毒毒死了整整一塘子魚。老祖正在奘房前清掃著那個小溝。老祖邊打撈著落葉,邊跟我們說起這個事情。那時涼風瑟瑟,又有一些枯葉落入溝里。老祖幾乎每天都來奘房。老祖想象不出她見到的人中哪個有嫌疑,老祖早已沒有了對人的戒備心。投毒的人是在夜間進行的。夜間,奘房前面,老祖詫異不已。在老祖看來,人的內心里雖然隨時會生出邪念,但在奘房面前,這樣的邪念會被洗滌。秩序竟以那樣的方式開始垮塌,老祖不曾想過。
無法抗拒。我們明明知道一些東西是無法抗拒的,但我們依然在努力抗拒著。我們明明知道人心會在更為兇惡更為容易被迷惑的世界中沉淪,但我們依然在抗拒著。
是在某個清冽的早晨,那些魚在魚塘里翻白。一些目擊者說那家的男人一句話不說,只是不停地咬著下嘴唇,女人同樣沒說話,也沒有流多少淚水,沉默,只有沉默。男人和女人帶著兩個孩子,離開了那個村寨。后珍朝某個空落破舊的院子指著,就是那家。那是行將坍塌的院落,沒有人氣的充盈支撐,院落往往坍塌得更快。也許,某天他們會回到那個村寨。也許,他們早已鐵定心不再回來。直到我離開潞江壩,那家人還沒有回來。我們在塘子里看到了零星的魚,暫時沒有人再去承包那個塘子了,塘子閑著。我的思想又開始從這家人身上躍到了別處。我又想到了很多從我們眼前走失的人。我偶爾會想想那些走失的人的思想狀態以及生存狀態。當那戶人家走失之后,塘子還在,茂密的古木還在,但那個自然環境也可能會如人一般走失。有些人有些物的消失,充滿痛感。
在教書之余,我們一伙人經常會來到潞江壩的那些自然中,談生活的晦澀、纏繞、平淡與幸福。我們會在那樣的一片完整的自然中,偶爾談起還未回來的那家人以及別的從我們眼前走失的人,也偶爾會談起人性在那個場域中的隨時走失。
2
我和后珍來小寨看小舅和他女兒。小舅的女人跑了。別人口中,“女人”和“跑”這幾個詞,發音很重,強調,是意味深長的強調。據說小舅的女人是朝鋼筋叢林逃去的。在人們口中,小舅的女人很決絕,她說走就走,離開后音訊全無。我沒有見過小舅的女人。我們一眼就看到了小舅的憂傷,頭發很長,雜亂的胡須,神色悲傷,話語悲戚。在這些看得見的憂傷面前,我們只能遮遮掩掩地跟小舅交談,我們努力表現得自然些。我們不知道該如何安慰小舅。
小舅有事離開了一小會。那時我們還沒見到小舅的女兒。我們以為小舅的女兒出去跟同齡人玩了。后珍給我講了一個人成精的民間故事。后珍講完,我們接著聽老祖講別的故事。這時小舅的女兒突然出現了,她正抬著自己的衣服來到院子里的水龍頭邊,并自己打開了水龍頭……我們都看到了她,我們面面相覷。故事在那樣的場景中,多少顯得有點怪異。我們不再講述故事。那一刻我們猛然想起她才四歲。小舅回來,目光復雜地望著女兒說女兒太聽話了。這時,小舅跟我們說為了女兒想和前妻復合,即便付出什么樣的代價都行。
女人逃跑,在潞江壩已經不是讓人感到驚詫的事情了。除了小舅的女人,還有一些女人接連逃逸。小舅所在的那個村寨與其他很多村寨一樣,自然環境很好,有很多古榕樹,小舅家還有好幾十畝芒果樹。小舅的女人,至今下落不明。女兒似乎只是他們沖動的惡果,其實并不是惡果,出現在我們面前的是一個晶體般泛著光的小女孩。小舅的女兒已經上幼兒園,她并不孤獨,在潞江壩還有好些像她一樣的孩子。很多女孩還未到法定年齡便結婚,先結婚生子后領證,有些人幸福著,有些人并不幸福。在很多人看來,這很正常,在他們看來,自由戀愛,自由結婚,也可以自由離婚。這些人的內心深處似乎有那么一個遠方,隨時等著他們逃離。我們沒能真正關心小舅的女兒,我們在如何關心她上,早已束手無策。
我和小舅大口大口喝著酒,沉默著,屋外的榕樹上鳥聲清越,那時確實是有鳥聲,我們都不自覺地朝屋外望了一眼,然后繼續喝我們的酒。我們在不斷制造謊言。我們那安慰的話語里,夾雜了過多的謊言。有時我們會隱隱希望某些謊言是真的。小舅在我們那漏洞百出的謊言與表情面前不停地點頭。大地的廣袤輕易就能把人吞沒,那時芒果正熟,芒果的香味夾雜在泥土的氣息之中,在我們周圍縈繞。我恍惚了一會,那時我甚至沒聽清楚小舅說了些什么。因了女兒,小舅不能離開小寨出去打工。如果不是因為女兒,小舅應該是最想逃離小寨的。逃離于小舅至少意味著某種程度的逃離尷尬,在一些人眼中,小舅的形象多少有些尷尬。小舅經常去村寨背后的那些密林里。在那些密林里,小舅有著屬于自己的蜂巢,而且還很多。讓人變得充盈的密林,讓人變得充盈的蜜蜂以及采擷自然的萬千精華釀造的蜂蜜。小舅需要那些密林,以及那些蜂巢,以及女兒。小舅似乎明白了沉默的深義,他長時間沉默,似乎那是悲傷、無奈、憤怒等等相互媾和的結果。語言不再連貫,表達不再連貫,表情不再自然,一切變得吞吞吐吐。那是我。那是后珍。那是老祖。那是小舅。這時我們突然聽到了小舅的女兒叫了老祖一聲,銀鈴般清脆,如水流般清澈。
3
在潞江壩,撤點并校帶來的問題,在交通較為發達面前,沒有暴露出來。江東岸“白巖”那個村寨,由于太遠太不方便,而在撤與不撤間猶疑著。到“白巖”,要經過怒江,以前沒有船,現在有渡船。在潞江壩,靠渡船,或走過那些讓人膽寒的鐵索橋,就會見到一些和白巖一樣交通不便的村寨。最后一次去白巖,交通依然不便,由于雨水的沖刷,路況極其糟糕。幾次來白巖,白巖并沒有發生大的變化。世界在發展,有些局部卻被遺忘。這個村寨,需要一條好的公路,這個村寨和出生地一樣需要一條好的公路。在白巖,一直以來,許多家長,寧愿讓孩子走路,也不敢用摩托車帶他們。許多人在那條土公路上,小心翼翼地行駛,但每年依然有一些翻車致死致殘的事故發生。我就在其中一次騎著摩托去白巖時翻摩托了,幸好是摩托往上側翻,只是膝蓋擦破了一點,如果往下側翻的話,后果不堪設想。我們騎著摩托到渡口,把摩托寄在江邊,再讓白巖村的人來接我們。我們騎著摩托,一路膽戰心驚,而畢姓同學那伙人,要繼續像往常一樣一直從渡口那里往上走。我們先騎著摩托朝白巖村趕去,我們只想在那里呆上一天,晚上就要回到我們任教的學校。那天,將近到中午,我們才看到了畢福君他們回到了白巖,我們一眼就看到了他們的疲憊不堪。
白巖村的很多人依然還堅守在那個陡峭的山地上,只有一部分人,已經搬到山腳比較平坦的地方。山腳受河谷氣候的影響,能種植許多經濟植物,這其中就有稻谷。以前,在“白巖”居住的人群,與稻谷無緣。在這個寨子里生存的大部分人,依然固守“讀書改變命運”的傳統。畢福君這群人往往成績很好,性格內斂,懂事。在“白巖小學”,楊姓教師不無感傷地跟我說起,在“白巖小學”并不是每年都招生。適齡兒童,就只能拖著,拖兩年甚至三年。這樣的情形,依然沒有終止的意思。我們第一次去那里招生時,是提前來的,我們來那年,白巖小學沒有六年級。那時我們所要面對的是“擇校熱”的問題,為了招一些基礎不錯的學生,我們必須提前來。而在江這邊的許多村落,交通便利,經濟作物隨處可見,咖啡瓜果遍地,但輟學的人很多。
一直以來,叢干是輟學人數最多的寨子,輟學原因莫衷一是。叢干是離我們所任教的那所鄉間中學最遠的一個寨子。比白巖還要遠些,只是去叢干的路要好走一些。我們去家訪那天,雨淅淅瀝瀝地下著。那個寨子是傣族和傈僳族雜居區,里面的傈僳族信耶穌。在那之前,我還未去過那個村落。我只是在那些還未輟學,或者行將輟學,或者已經輟學的學生的只言片語里,了解到一些東西。但從他們口中了解到的,對于勸他們回來似乎沒有任何作用。我們去的那天不是周末。教堂緊鎖,從那扇鐵門的縫隙朝里看,空落,或者是空曠。我甚至找不到說服她們的理由,在她們面前,語言的宮殿瞬間傾塌。在那群輟學的學生身上,我看到了自己。在我讀小學時,我們那些距鄉鎮最遠的學生,經常被鄉鎮上的人欺負。那時,我看著寨子里的同齡人一個接一個輟學回家,我也有了輟學的想法。當我把那種想法跟父母說時,父母堅決不同意,但又不知道怎么辦。在眼前的這個寨子里,很多家長也因為那樣的事情而頭疼,有些父母便在嘆氣與咒罵中,讓自己的孩子輟學了。我早已經忘記了當年我們是怎么堅持下來的。我有點遺憾地搖了搖頭,我有點不知所措。在那群孩子眼里,既然沒有解決的辦法,他們就不能回到學校。那時,我頓時感覺到有一股無法清除的痛楚正在痛擊著我。我想給她們講述韜光養晦的生存哲學,但我不知道該如何說。我已經意識到一些道理在她們面前的虛脫與蒼白。但他們輟學的原因,似乎還不是這么簡單。走訪那個寨子以失敗結束。我們還去了幾次,我們只是希望學生輟學人數能少些而已。最終輟學的人中,只有一個回到了學校。
叢干輟學的那些學生,她們輟學然后朝城市走去。在我回到潞江壩的途中偶爾會見到其中的一些人,她們打扮得花枝招展,她們早已不是素面朝天,那略顯夸張的化妝包裹著的內部,有著對于一個世界屬于她們的看法。她們和我打著招呼,我問著她們什么時候回到打工處,她們朝我樂了一下,說快了,瞬間混入別的那些人群中。
4
我們需要那些在密林中聚集的殘骸。但我們不需要那種由于人類對于自然界的侵吞所制造的殘骸。我多次進入過高黎貢山。高黎貢山,保留了那種讓人驚訝的殘骸。古木繼續生長的氣息與古木殘骸的氣息交雜。我們很多人被自然的那種氣息所濡染。我們多次專門組織深入高黎貢山,其中有一次最終的目的地是“小地方”。于高黎貢山而言,那個密林中的小村落確實就是小地方。“小地方”,當看到了寨子口的標記時,后珍和我對視了一眼,我在那一刻想到了“小寨”,后珍跟我說她也想到了“小寨”。“小寨”,一些民間傳說,一些發生在小舅身上的不幸,以及可能會發生在任何一個人身上的不幸。只是許多民間傳說正在隱去,很多不幸卻凸顯著。在那么多次集體行走中,我們看到了輪廓棱角異常分明的各種各樣的群山植物,我們感受到了那種濃烈的叢林氣息原始氣息。在出生地,這樣原始的氣息早已變得稀薄。大地本應有的繁盛的生殖能力,情欲的旺盛,已經在很多角落里面悄然淡化。在眼前這片熱帶河谷之中,卻一直濃烈著。我們走出村寨,離大河遠些,我們在高黎貢山上望著大河。我們是多次出現在了高黎貢山,我們就遠遠望著那條大河,大河并不波濤洶涌,其實走近就會發現那條大河一直洶涌著。為了自然界的殘骸,我們要遠離那些村寨,我們要進入那片密林中。電視臺的朋友專門做了關于高黎貢山密林中動物與植物的紀錄片,動物與植物的樹木繁多,所有的動物所有的植物以及別的很多物都是以活著的姿態存在。活著,熱鬧,又異常靜謐。
前段時間,有一頭野豬混入了我家的豬里,它們一起在那個山谷的草場中汲取雨露,共用一個草場,這樣的情景不只是存在于歌聲和過去的記憶里,這讓我感到吃驚。我一直對出生地的一些東西失望,我根本就不曾想過這樣的事情會再次發生,而最終那頭野豬只是和家豬在了一段時間就消失了。據一些人猜測很可能是被偷獵者獵殺了,這樣一幅本是很唯美的畫面,就不再具有美感了,我甚至聽到了一聲槍響,斷裂的聲響,割裂的聲響。我希望那頭野豬是回到了山野。出生地,在雨季,山野破敗,泥石流過后,幾年甚至幾十年是根本無法復原一片草野的。野豬以那樣的方式再次出現,這里面似乎暗含了一些美好的東西。最后野豬的結局又似乎暗示了那片自然的其中一種結局。許多野豬隨著別的野獸從那個山野間消失,它們一定經過了不斷往遠方的遷徙過程,往遠方,有密林的遠方。
該如何才能更好保留一片山野的完整性?通過宗教,或者其他?出生地一直都沒有解決好這個問題,而在潞江壩,似乎早已解決得很好。我羨慕在潞江壩生活著的后珍、小舅、小舅的女兒和老祖。我侄兒子他們,還有畢姓同學那伙人一定像我一樣羨慕在潞江壩生活著的后珍、小舅、小舅的女兒和老祖。我們羨慕他們生活在那樣一片近乎完整的自然,即便這樣的生活環境依然無法抗拒生活中的諸多不幸。
5
那是怒江。那是我們在高黎貢山上望見的那條大河。那本是一條體面的大河,而這樣的體面正慢慢被盤剝。只有雨季,怒江才會給人是一條大河的感覺。我們在那個地域生活的很多人都無法繞開怒江。后珍和我還多次來到芒棒村的那些莊稼地里,遠遠望著一條江,我們遠遠望著一條江的流量變小,然后增加,然后再變小。似乎我們都心知肚明,只是沒有把它言明。或者,那時后珍和我的眼里更多是莊稼,而很少有怒江。
有個左姓朋友,我們曾經就那些大河的命運談論了很長時間,他頭頭是道地分析著那些大河面臨的困境,同時也不斷提到了自己身體所表達出來的不安。他在一些文字中把自己的肉身與那些大河進行過對比。他說自己的肉身早已不是完整的,自己早已不是以體面的方式生活著,他一度擔心自己會不會以一種極其不體面的方式消亡?他最終離世了,以他一度擔心的并不體面的方式離世。他的很多器官早已不完整,心臟有問題,痛風,視力極其不好,還有很多問題。也許,他早已意識到自己無法再與那樣的殘缺進行抗爭了,只是在努力抗拒著。我們還談到了那些大河的支流。怒江、瀾滄江、金沙江的很多支流,我們意識到了由那些支流所帶來的精神危機,畢竟與我們有關的很多條支流正有徹底干涸的可能。
我們談到了一條大河的體面。一條大江的體面首先應該是流量的恢宏磅礴,同時是兩岸上植被的密集,以及兩岸的村寨城市所體現出來的體面。我們都覺得瀾滄江、怒江、金沙江等幾條大江,所展示出來的澎湃是無可厚非的。我們很多人也一直在努力體面地活著,這也是無可厚非的。有時我們的處境與那些大江的結局是一樣的,我們都感受到了生命在時間面前的無奈。前些時日,聽到左姓友人離世的消息時,我竟狠狠地吐了一口氣,他解脫了。
很多人用不同的方式努力體面活著。那些村寨中的老人體面活著的方式,就是經常去奘房。在奘房里面,他們只有一種身份,虔誠的信眾。他們中的一些人在那個清澈的水溝里打撈著枯葉,有些老人在那個電視機前看傣戲,有些老人在奘房前面種植草木。在那個奘房里,傣戲以那樣的方式被保留。在我來到那個奘房之前的很多年,傣戲曾鮮活地存在于潞江壩,而現在傣戲已經成為一個很小眾的民間藝術。像傣戲,專門要有唱戲的戲臺,有些戲臺的華麗講究和民間的素樸形成強烈的對比。現在,曾經全民癡迷傣戲的情景現在幾乎就看不到了。只有在奘房里,很多老人才能真正輕松一下。而在平時,很多老人努力勞作,為了更好安度晚年。傣戲,一定是有它們存在的必要,只是它成了受眾面極其小的藝術,這樣它的真正作用沒能真正體現出來。當作用沒能真正體現出來,很多民間藝術已經不再鮮活,也加快了民間的一些秩序的垮塌。我們要回避很多問題,我們要極力回避民間藝術長河的斷流所帶來的精神秩序的崩塌。
很多生命匆匆消逝,當我還在為那個患皮膚癌的李姓老人擔心,擔心他該如何繼續面對日益潰爛、不斷結痂又潰爛的傷口所帶來的痛苦與無奈時,聽說他離世了。對他以及很多人而言,可能這樣會更好一些。
6
在進入潞江壩這個于我而言很嶄新的世界之后,才發現許多在出生地發生的事件在潞江壩同樣發生著。在出生地,有那么一群外出打工然后回來的男人。他們拖著疲憊的身心(應該是疲憊了,除此外,我還真找不出任何能說服自己的理由)回來了,這些回來的人,對農活早已生疏,他們需要再次學習適應,這其中就有我的表哥。表哥還是非農業戶口,他在某個夜晚給我打電話訴苦,說是非農業人口的身份在農村里面沒有給他帶來任何好處,而相反因為這樣的身份讓他在生活中比別人更加艱難,我聽到了他對姨爹的抱怨,他抱怨,長時間在抱怨,我不知道該通過什么樣的方式安慰他。在和他通電話的過程中,我感覺到電話那頭的他就是一頭困獸,正在為如何繼續更好地生活下去而發愁。那是一個茫無頭緒的群體,表哥只是其中一個,很多人像表哥一樣慘敗。
這個群體中有很多酒鬼,而其中一些酒鬼,喝醉酒之后,就會打媳婦。那個群體,經常會被一些人評說。我也會直言表哥不應該成為酒鬼,或者即便成為酒鬼也不應該一喝酒打表嫂。表哥經常打表嫂,有些時候下手還狠。表哥不分青紅皂白地打表嫂,里面有著對于逃離出生地最終潰敗后的沮喪。表嫂就那樣忍受著,很多女人就那么忍受著,而表哥他們那群人依然在一種就是醉生夢死(可能絲毫不夸張)的狀態中活著。他們在頻頻舉杯中談論自己的過去,那些在城市里面生活的經歷,但隨著灌入腹中的酒越來越多,他們開始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緒,他們開始詛咒生活的不公,以及離開村寨在城市中生活依然艱難帶來的頹喪。當那些陪著喝酒的人離去,當喧鬧的群體被分割成孤獨的個體之后,他們一看到媳婦,媳婦便不順眼了,然后媳婦便被咒罵,媳婦便被狠狠地揍了一頓。表哥曾多次揍過表嫂,有多次,沒有人敢去訓斥表哥,姨爹姨媽兩人常年被病痛折磨,姨媽還多次因為表哥打表嫂而嚇病。我們很多人在評述像表嫂一樣的人時,我們都在納悶為何她們還一直忍受著,她們就不能想方設法逃離?像表嫂一樣的人,在出生地生活了很長時間之后,她們也會講了一些當地的方言,但從她們口中發出的方言,還是感覺怪怪的。她們跟隨著那些慘敗的人們回到出生地的時候,她們往往也成為了慘敗的人。在那個于她們而言很陌生的世界中,她們很長時間與出生地之間存在著裂痕,需要慢慢地修復,而有些裂痕可能永遠也得不到修復。在潞江壩,同樣有著這樣的群體,他們同樣從城市里面重新回到潞江壩,成為酒鬼,詛咒生活,打罵老婆。也有那么一些人從城市回來后認真活著,在出生地找到了活得更好的方式。表哥在多次酒醉后,突然跟我們說自己是過分了一些,他說一定要嘗試著戒酒,他也在努力著。
7
那次泥石流,讓很多人震驚。其實,人們早已習慣了泥石流,在云南的很多地方,每到雨季經常會發生泥石流。只是那次泥石流掩埋了一些人。那次泥石流發生的具體地點,是瓦馬鄉鎮府旁邊的一個村寨。離潞江壩不遠,只需要翻越一座山,或者沿著怒江的某條支流就可抵達那個村寨。事件發生一個星期后,我第一次出現在了瓦馬。我去并不是為了那起事件,而是那時女友在那所鄉鎮中學教書。那是一個依舊落后的鄉鎮,那樣的鄉鎮我很熟悉,在云南的高山峽谷中有很多。在那里呆了短短兩天,我便落荒而逃。
其中有一個死者是那所鄉鎮中學的新生,本來事件發生前天就應該來報到了,但由于一些被泥石流卷走的原因沒能按時來。這是云南大地上的一種死亡方式。發生泥石流的那個地方,地質條件很差,松動的土石,一下雨就泥濘不堪的土路,那些山石上面經常會有一些水滲出,水在不停地侵蝕著那個本身就很脆弱的地質環境。在那個看似(或者本來就是)窮山惡水的地方,人們一直信賴著生活的那個自然環境,這多少讓外人感到驚詫。那些人為何一直生活在那個河谷中?在那次事件中幸免于難的一些老人可能知道理由,但那些老人已經疲憊,已經疲于講述。在那次泥石流發生之前的很長時間里,泥石流在那里從未發生過(這同樣多少會讓外人感到吃驚),只是一些日漸增多的泥漿會隨著那些溪流流到那個河谷中,然后繼續往下游流去,流進怒江,然后經過潞江壩。怒江的水,在那些多雨的季節,總是很渾濁,它的許多支流裹挾著太多泥沙涌入怒江。
這起事件除了吞噬了好些人,還吞沒了許多來不及逃脫的生命,而被吞沒的植物應該是最少的,當我來到那個河谷時,植物稀少,空氣稀薄。每每想起這起事件,我就會感受到某種清晰的痛感與不安。似乎從表象看,這起事件與我真的沒有任何關系,實際關系很深。在云南大地上,我看到了許多與那個村寨一樣的角落,我的出生地就是,那些生態脆弱的角落,生態正在惡化,經常發生雖然沒有掩埋過人,卻掩埋了諸多草木的泥石流。在這之后,我還多次回到過瓦馬,并經常經過那個發生過泥石流的河谷,依然還有一些零星的人家居住在那個河谷。我多次在瓦馬的暗夜中醒來,還有多次想逃離瓦馬這個偏遠的鄉鎮的想法,而最終我真的逃離了。2010年之后,我就再也沒有來瓦馬了,但偶爾我會通過別人口中了解到一些關于瓦馬的信息。據說,瓦馬有了一點點變化。我不知道,在那起事件中,在心靈上受到了嚴重傷害的那些人隨著時間的變化,以及鄉鎮的變化,是否得到了治愈?
真正遠離那些很惡劣的自然環境吧?但有時即便有可以遷徙定居之地,但又能都輕易就拋掉那些自己熟悉的自然,更何況現在還有多少可以遷徙定居之地。我們需要的是一片寂靜的自然,我們需要的是一片完整的密林。在那些暗夜里,我似乎看到了一片完整的密林,我是真實地看到了瓦馬夜空里面璀璨且繁密的星辰。星辰在暗夜醒來,一些自然萬物在暗夜中沉睡,一些自然萬物在暗夜中醒來,一些心靈在暗夜醒著。那起事件發生在暗夜,還是有好多事件發生在白日。如果無法避免,我還真希望一些事件是發生在白日,一些生命可能就會在白日的敞亮里逃脫。而在暗夜,許多生命在沉睡中無法逃逸,許多生活在沉睡中忘了逃逸。與那個被奪取生命的學生不一樣的是,有一些人按時來到了那所鄉鎮中學,家人卻在那起事件中被掩埋。
8
那是一起自殺事件。那個女人代表了一群人,并不是代表了一群自殺的人,而是代表了一群年紀很小便結婚的女人。但為了成長,為了變得成熟,不應該付出自殺的代價。有時,自殺即毀滅。當我聽說那起自殺事件時,那個女人早已被埋葬。在潞江壩,自殺的事件時而發生。自殺不僅在人類中發生,在潞江壩,自殺還蔓延到了自然界。我親眼見到了一些死亡的植物,一棵古老粗壯的古樹(被某些村寨奉為神靈)突然枯死了,那樣的枯死只有自殺才能解釋。還有一些植物在自殺,莫名其妙地枯死,先是從樹葉開始,樹葉開始卷曲然后干枯然后掉落然后腐化,樹葉死亡后,才發現樹根(有好幾百年)也枯死了,但那些植物絕對不是干旱而死,似乎只有自殺才能解釋得清。而很多小動物的自殺就不需要去猜測,只需要看看現場便知道那是活生生的自殺。自殺,是一個值得深思又不值得深思的問題。那些植物和動物的自殺是無法遏制的,就像是無法遏制某些人的自殺一樣。
死者如果按年齡來算的話,還是一個小姑娘,應該剛剛成年,但不按年齡來說的話,她已經是一個兩歲孩子的母親。我曾見過她的孩子,那時她已經不在人世。在面對一個孩子時,我內心深處那根最脆弱敏感的神經,表現出了前所未有的無措與沉重。像她一樣的女人在潞江壩還有好些,先結婚后領證,以一個小姑娘的心理承受力來承受生活的種種,包括了生活的幸福與艱難。而面對生活的艱難時,她們中的很多人往往很無措。
這個兩歲娃娃的母親,她面對的只是生活中的一點點不是很嚴重的爭吵,但她無法承受,爭吵變得嚴重,她想到了死,想到了以死來報復自己的丈夫。這并不是一個能負重的女人,她們那個群體中的很多人都是無法負重的,畢竟年齡太小了。她是喝百草枯自殺的,這種殺草的藥在潞江壩看來,只要喝了百草枯就沒有救活的可能(在潞江壩,常見的另外一種自殺方式是喝敵敵畏,一些喝了敵敵畏的還有被救活的,但喝百草枯的人沒有一個救活過),選擇百草枯的她帶有著某種決絕的意味。這種藥物的腐蝕性很強,據說她只是灌了一點點,他丈夫眼疾手快從她手中把百草枯奪了過來,但已經來不及了。那時的她就是某種草,本可以是一歲一枯榮的草,本是一棵具有很強的韌性的草,但在百草枯面前,韌性被弱化,草的姿態被弱化。她死時的慘狀,讓許多人感覺到害怕,在這里我只是在復述,我都覺得害怕,我只能把那種慘狀忽略。
隨著一個母親的離去,產生了一個孤兒。那個年紀很小的母親,在人們的口傳中更多是被放置于被批判的角色上的,批判她對于生命的輕視。這在很多人看來,太過可怕,太過不可思議,也應該不能輕易饒恕,她的自殺無疑是對于生命的輕易放棄。人們還批判那個女人對于一個孩子的放棄,這是一個不負責任的女人,她應該為了孩子好好活著。在人們看來,根本就不能把生命視若草芥。那個女人以被批判的角色出現在了人們的世界里,我卻不知道該讓她以怎樣的角色出現在我的講述中,我一開始也想到了批判,但似乎無法輕易來批判那起自殺事件,一個自殺事件里還潛藏了太多隱而未露或者某天會突然之間浮現出來的東西。
9
關于那個瘋女人的事情,我都是耳聞的。這是另外一個患有精神病的女人。我看到她時,她已經恢復正常。在那個有古木眾多的村寨里,我見到了那個女人。眼前的她,有點臃腫。我向一些人打聽關于那個女人的事情,那些被我詢問的人并沒有表現出任何異樣的神色與語氣,而是很耐心地給我講述關于一個女人的事情。那個女人,本是幸福的,結婚,生子。但娃娃長到兩歲時,丈夫出軌。女人的丈夫一直努力遮掩著出軌的事實,但畢竟有太多躲在暗處的眼睛,這些眼睛輕易就能讓事實掙脫遮蓋物,這些眼睛往往無法控制自己的表達欲,事實在日光下變得醒目。女人責問丈夫,丈夫直言不諱。丈夫可能是無法消除內心的不安,一個人外出打工。
女人并沒有跟著外出打工,而是把時間重點放在了照顧娃娃上面。那個娃娃聰穎可愛,所有講述者都沒有把這一條忽略掉。在講述時,幾乎所有人都面露憾色,他們的語氣基本是這樣:可惜了那么好的一個娃。娃娃在某天晚上發燒,而潞江壩離衛生院很遠,女人沒有任何辦法,用一些土辦法給娃娃降溫,但在那個晚上那些民間的辦法沒有起作用,娃娃的后果可想而知。那個娃娃,在那一次發燒之后便不會講話了,雙腳也麻痹無法行走。那個女人經常要把兒子背著,前后背了一年,直到兒子夭折。兒子夭折的那天,女人撕心裂肺地哭著,有許多人都聽到了凄慘的哭聲,同時也聽到了凄慘的笑聲。女人就這樣真的瘋了,瘋了的女人被送往精神病院。在精神病院的三年時間里,原本身材瘦弱的女人開始發胖(據說是吃藥的結果,也可能真是發胖了,也許一到精神病院里,疼痛便在女人的意識深處消失,女人已經感覺不到疼痛,女人已經因無法感覺到的疼痛而徹底冷靜了下來),出現在我面前的女人才那般臃腫。她是正常的,也該正常了,不然那么沉重的痛苦會徹底把人壓垮,幸好她還能從壓垮后重新振作起來。至少她是挺過來一些了,至少她在精神上有了一種抗拒過往生活的能力,不然她不會那么平靜地出現在我面前,精神病院可能無法真正治療她,她需要自己的治療。
三年后,是丈夫把她從精神病院接了回來,女人似乎沒有任何的激動,而是沒有任何表情地跟著丈夫回家。到這里我才提到了“沒有任何表情”這樣的話語,是的,我見過的她便是沒有任何表情的,是的,從精神病院出來后的她在別人的講述中,都是沒有任何表情的。表情本應是很豐富的,但三年時間里她似乎忘了表情的豐富。后來我多次見到她,但確實看不到她的表情,也可能她的表情就只有一種,僵硬的冷,抑或超脫的淡。這個我確實無法猜測,在這樣一個女人面前,我不能再進行任何猜測了,猜測無異于在褻瀆。一個女人,并不只是一個女人,就像上文中提到的那些女人,她們無法真正脫離潞江壩,在很多時候,無法作為一個獨立的人存在。
10
在潞江壩,模樣同樣會經常騙人。那個才三十多歲的女人,看著早已不是三十歲的模樣。我猜測著,四十歲,或者五十歲。三十多歲?這是經過證實的,我感到很吃驚。她那可以算是我的親戚,她的頭發已經花白,但才一歲多點的娃娃經常背在背上,偶爾會出現在我們面前,偶爾也會和我們閑談閑談。但更多時候,她已經被生活剝奪了閑談的權利,她的丈夫在現實中就是一個游手好閑的人,很少幫她干活,卻經常和一些人酗酒。在潞江壩,一些男人敗給了酒,說得準確些應該是過量的酒。
在潞江壩,讓我印象最深刻便是酒文化的濃厚。酒文化濃厚無可厚非,酒文化背后也包含了許多好的東西,但更多時候太過濃厚的酒文化也給一些人帶來了災難與不幸。她的丈夫在久而久之的酒精的浸泡下,真正成了生活中的閑人。在潞江壩,當心真正閑置下來,那無疑是一種毀滅性的災難。這樣那個男人便給一個家,或者至少是那個女人帶來了災難。生活的重壓便全部要讓她來承擔。出現在我們面前的她,會讓人有一種已經無法承受生活的重負的感覺,那樣的身體太過瘦弱了,那樣的皺紋太過深刻了。連背上的那個娃娃也太過瘦弱了,似乎那個娃娃也在過早地嘗到了生活的苦難之后,變得麻木了呆滯了,我們幾個人有意去逗那個小孩,但他沒有任何反應,只用一雙還算清澈的眼睛注視著我們。
這樣的女人,在那個富庶的潞江壩還有好些。在很長的時間里,我總覺得潞江壩無疑是富庶的,那生活在其中的人們無疑也是富庶的,并且還因富庶而幸福,而真實的情形并不是這樣。富庶的只是一個從外面看到的大世界,而它的內里還有一些讓人刻骨銘心的貧瘠。那個女人,家里家外繼續忙活著,繼續承受著生活的重壓。她并沒有像潞江壩的許多女人一樣外出打工,她的男人也并沒有像潞江壩的許多男人一樣外出打工。他們的堅守,并沒有堅守著民間的一些應該保留的東西。他們家的農田很多,但現在已經有許多成為了荒地。荒地具有了強烈的象征意義。我們說起了那些荒地,但她只是無奈地搖了搖頭,也只有嘆氣了,也只剩下無奈了。需要一個男人,一個能開墾荒地,或者讓良田不會變成荒地的男人。而她有一個男人,卻不是一個擁有這樣能力的男人。我的文字,可能無法真正抵達她的不幸。那個男人也無法真正消解她的苦難,只是給她制造了無盡的苦難。其實苦難是可以分擔的,如果那個男人哪怕幫她分擔一點點苦難,她也絕對不會是眼前的這個模樣。那樣的話,他們的堅守就有了某種意義。有時我會悲觀地覺得,時間對于一些人并不能改變什么,哪怕是呼吸的節奏、喘氣的聲息、胃里翻騰而出的酒氣。這都可能只是一些陳腐的東西,都是一些固定的東西。我就坐在那里,連正眼都不想看他一眼。在那一刻,我無法控制住內心對他的厭惡以及鄙視。我唯有一副怒其不爭哀其不幸的樣子,似乎才能真正表達我內心的想法。而他對我同樣表現出一樣的姿態,他同樣對我不聞不問。
11
那是一個出軌的女人,以及被車子撞死的她的丈夫。我的敘述中應該不能忽略一些人,像他們的兩個孩子,像他們的父母,我可能要牽扯到好幾個家庭,我需要多個角度多個線條來對這些人進行他們應有的敘述。而在進行真正敘述后,我才發現自己的敘述是無力的,我根本沒有能力把牽扯到的所有人都敘述清楚。我感覺到敘述那些人時,敘述所給我帶來的前所未有的壓迫感,我需要喘息,為了喘息,我必須要把其中一些人忽略掉。在潞江壩,像她一樣出軌的女人有好些,但因出軌導致丈夫被撞死這樣的事件似乎就只是那一件。也許,我需要盡快地進行我的敘述,不然許多人開始對我的敘述進行猜測,會猜測這里面可能會涉及到謀殺之類的,但我要說的是與類似的猜想是完全沒有關聯的,那絕對不是一起謀殺事件。在這里,我只是想借助一種緩慢的敘述節奏,我希望有時候緩慢的敘述節奏亦可以有力量。
女人出軌了,她與那個有家室的男人經常混在一起。那個男人剛好在那個女人所在的村寨里開了一家飯館,女人來飯館打工。生意做得不溫不火,似乎他們所要抗拒的便是飯館生意的不溫不火。隨著我們進入那個飯館次數的增加,我們發現了他們二人之間的關系。應該除了我們而外,還有一些人也發現了他們之間關系的不同尋常。在一些人的講述中,女人的丈夫是最后一個才發現的,同時也在一些人的講述中,女人的丈夫早就知道了。總之,女人的丈夫是知道了,但并沒有來飯館里鬧,據別人轉述女人的丈夫私底下和女人好好商量,但商量未果。女人的丈夫開始酗酒,那種生的力量被酒消磨殆盡。在其中某次酗酒之后,女人的丈夫騎著摩托車往家的方向趕去,家里面還有兩個娃娃和年老的父母(到這里我開始意識到這段敘述無法離開這些人的支撐),這些家人也在等待著他的回來,而女人已經好長時間沒有回來。出軌的女人,成為了那家人的羞恥。而出軌的女人似乎并不覺得那是羞恥。女人的丈夫在騎著摩托車回去的路上,被一輛大卡車碾死,現場血腥慘不忍睹,但那里只出現了他的娃娃以及家人,而并沒有出現女人。
一個完整的家,在那一刻瞬間變得支離破碎。到后來,我在某個城市碰到了那個女人和那個飯館的老板,女人勾著男人的手,很親密的樣子。似乎那起事件,對他們并沒有太多的影響。在這里,我只是簡單地提到了那個出軌的男人,而出軌的男人的妻子父母等等被我的敘述忽略,我需要他們成為我敘述的留白,是能讓人進行一定思考的留白。兩個家庭,一些人,兩個出軌的人。對于這兩個出軌的人,我無法輕易定義。
12
時空如斯,在一條大河邊上的民間任苦難與幸福安然地發展著沉淀著,似乎除了安然的生活態度,已經無法對抗那些生活中無處不在的苦難了。幸福與苦難如斯,特別是苦難。于眼前的某些人,當時空于他們一直如斯之后,風景已經無法幫助他們對抗生活的苦難,以及內心深處的迷茫。風景的作用被人為被意識弱化。在潞江壩,擁有那樣動人的風景,在一定程度上只是幫助了一些人。而那些未被風景感染的人,重點是無暇顧及風景。自然風景,被擱置著。曾經風景一度成為人們日常生活中不可缺的一部分。
自然的不缺失,這是我出現在潞江壩的大部分時間里,所能真切感受得到的。在潞江壩,那個自然場景的存在,把民間的一些東西遮蔽了,包括其中的苦難。如果我只是靜悄悄地來靜悄悄地走的話,我就會無法深入那片無法安靜的生活內部。我的眼前我的記憶中,將只會留下一個美得讓人感到驚訝的自然場景而已。而在潞江壩,我偏偏很不安分。有時我甚至就是以一個寫作者的身份,出現在潞江壩。我與潞江壩的一些人,說出了我內心里面的感受,我想把潞江壩的真實展現出來。一開始我所理解的真實,似乎只是呈現那些自然場景的美,以及在潞江壩里面生活的人們的生活的美如畫。而最終,那個世界里還有一些生命在掙扎著。一些生活場景真正在消失,這些行將消失的東西需要被記錄;一些生活中的苦難被人們忽略,這些被忽略的東西需要被記錄;一些美如斯的自然場景有消失的可能,這些被我擔心要消失的東西需要被記錄……
在潞江壩,苦難確實無處不在,地名的變遷確實改變不了一些屬于生命普遍的困境。苦難是有著大苦難與小苦難之類的區別,我的那些苦難永遠只是一些小苦難,甚至是一些根本就應該被忽略的苦難。在眼前潞江壩內部潛藏的那些苦難面前,我的苦難簡直算不了什么。而在潞江壩,很多人擁有一種看似更冷靜地對待那些苦難的方式。我在潞江壩生活的時間里,我真的希望有些人能有所抱怨。但似乎一些女人是不能抱怨的,她們在生活中有時處于弱勢地位的,她們要面對來自多方面的強權,像丈夫的強權(有些丈夫毫不講理,把生活中的一切不如意都歸罪到女人),像公公婆婆(有些女人真就碰到了這么一些不講理的公公婆婆,有些不講理到已經有點心理上的病態這樣的程度,當然也是有那么一些女人毫不講理,又恰恰與公公婆婆的講理不一樣,這里我只是提其中的一些女人,那些被毫不講理的強權壓制的女人。在這里我沒有絲毫的夸張)。
有時我還真希望那些女人會來一次大逃亡,有一些女人已經開始逃亡,逃亡的女人被潞江壩的評判尺度評判著,有些逃亡的女人被一棍子打死,在潞江壩最傳統的理念里逃亡就是不對的。逃亡與否?以及在什么情形下才逃亡?或者怎么對抗內心里面一直想逃亡的沖動?這些都是問題,都是一些我在這里無法輕易做出判斷的。逃亡會引起混亂,但有些逃亡會讓一些女人獲得解脫。而我在私底下所期望的一些逃亡并沒有發生。有那么一些女人,卻是真正逃亡了,不顧一切地逃亡,她們從潞江壩逃離,逃到遠方,只存活在潞江壩的口語語境之中。那些自殺的女人,那些出軌的女人,似乎都是某種意義上的逃亡。她們的逃亡,只留下了一些破碎的家庭,以及一些無辜的小孩。我在面對那些無辜的小孩時,我又開始懷疑那些逃亡的女人了。也許,逃亡并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我所期望逃亡的那些女人,她們還背負著一些東西,她們可能也意識到了逃亡根本無法解決一些問題,但逃亡之外,她們又想不出別的能解決那些問題的方法。
逃亡與不逃亡?
或者……
但有時,一些生命往往無法輕易逃逸,就像那些人無法在一場突如其來的泥石流面前無法逃逸一樣。
在潞江壩,悲劇依然在不停地發生著。我在不停地關注著那些悲劇。我想和那些人談談,至少談談他們的苦難以及幸福。但一些人早已離世,一些人早已拒絕與人交談。
13
許多生命正在潞江壩這塊大地上,或者在出生地,或者在別處,繼續為體面活著而努力著掙扎著抗拒著逃離著。我又何嘗不是那些努力逃離某些世界與角落的人中的一員。我們正用我們的方式逃離自己想逃離的世界。一些人已經逃離,一些人已經無法逃離,一些人已經不想逃離。
責任編輯 包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