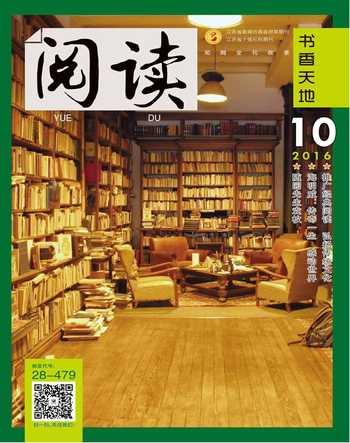薔薇般綻放 櫻花般飄舞
劉晨
讀書會,或者說公共閱讀有兩種狀態,一種安靜,如薔薇般綻放;另一種熱烈,如櫻花般飄舞。
英國人把讀書會叫做reading group。跟一些沙龍類似,reading group往往針對一個小問題,召集一些對這個問題感興趣的人,或有主講人或沒有,大家圍坐在圓桌旁,細細地討論。讀書會的重點不在于主講人講了什么,或者閱讀材料本身的內容,而在于最后的討論和博弈。
我的博士導師Phil Crang教授組織了一個名為October group的讀書會。每隔一周,中午12點45分,在倫敦市中心的一個畫廊里,一群二三十歲的學生和一群四五十歲的老師一邊喝酒吃飯,一邊聊著閱讀。最初,這個松散的活動僅僅是Phil為了讓學生們認真讀書而舉辦的。后來,隨著他的學生越來越多,學生又有了自己的學生,Octobergroup的成員換了一批又一批,但始終固定在20人左右,以便每個人都能參與到討論中來。針對物質文化的研究,October group面向倫敦的學者,探討時尚和“舒適”的生活模式。每次的話題都會提前在郵件群里發給所有可能來參加的人。
2012年的初冬,Phil讓我和我的同學Priya一起主持一場有關飲食的讀書會。在接下來的一周里,我們一起定主題、找文章,把文章發給每個讀書會的成員。我們打算探討國際商品網絡中食品生產、流通、消費和意義的變化。甚至,我們帶了一個在英國超市里售賣的,貼有“fair trade”(公平交易)標簽的木瓜。意料之中,討論在觥籌交錯中漸行漸遠。話題從最初的道德消費偏離到抵制消費,從最初的全球化談論到本土剝削,從最初的文化多元講到量化幸福感和全民普查的弊端。吵吵鬧鬧,喝酒,吃芝士。大笑、憤怒、爭吵、妥協。甚至牽扯出了國際地理學上對不同語言和權力不公平對待的批判。一個半小時之后,一切戛然而止。大家關上電腦,合上筆記本,穿上外套,各自出門。那天,畫廊正在布展,一棵枯樹上掛著一朵大紅色的花。
畢業之后,我離開了倫敦,到北英格蘭的謝菲爾德大學工作。因為研究興趣使然,被同事Megan叫去參加了一個討論食品問題的reading group。這個讀書會每個月舉行一次,在各個成員的家中輪流舉行。最初,這個組織由謝菲爾德大學研究食品政策的幾個學者發起,定期討論與吃喝相關的話題。慢慢地,通過口口相傳以及學者之間的聯絡,這個FoodReading Group慢慢開始有了自己的郵件群、固定的參與人群和輪值秘書。與其說是讀書會,還不如說是以討論食品問題為名的家庭聚會。
第一次去的時候,坐了半小時公共汽車來到主持人Peter的家中。一進門,Peter的女朋友撲面而來一句:“你要紅酒、白酒還是啤酒?”一時沒反應過來的我拿出了一疊打印的資料問:“我們今天不是來探討糧食安全的問題嗎?”而Peter的女朋友說:“親愛的,先喝一杯吧!”于是,在喝著酒,吃著零食,鬧騰地寒暄之后,所有人切換成靜音模式,開始輪流講述自己對糧食安全和地緣政治的見解。輪到我的時候,我說,自己曾經把“食品安全”和“糧食安全”弄混過,鬧了個笑話。但日常生活中,誰會去考慮糧食安全的問題呢?又有誰會去考慮糧食主權的問題呢?這么一說,整個reading group炸了鍋。有說日常的政治和國家治理原本就是一體的,也有說新自由主義就是要個人負起社會責任的。跟October group一樣,這個松散的Food Reading Group一討論起來就熱鬧非凡,紳士淑女們平時的溫和不知去了哪里。大家借著酒勁高談闊論,直到鄰居前來敲門,讓我們說話小聲點。討論結束后,一切歸為平靜。回家的路上Megan問我感想如何。我說:“你們太鬧了。”Megan卻說:“不這樣討論的話,如何批判性思考?”誠然,如果不這樣吵吵鬧鬧,何來討論?何來思想的碰撞?我們都是懷著深入探討社會問題的初衷而來,爭吵是不可避免的。
再后來,因緣際會之下,我來到南京展開一個對比英國、中國和烏干達的代際文化、消費和可持續性的研究項目。為了探尋不同的社會如何將不同年齡的人組織在一起,打造聯合國所說的“不分年齡,人人共享的社會”,我探訪了不同的個人、家庭和社會組織。有一天,一個朋友發來郵件,說有兩個青年讀書會不知我是否感興趣,一個在樺墅的鄉間(嚶鳴讀書會),另一個在紫金山上(群學書院)。跟英格蘭工業化和城市化濃烈的喧囂不同,南京的讀書會帶著那么一點鄉野和山林的靜美。
去嚶鳴讀書會的那天剛過小暑,輾轉坐了地鐵、公共汽車和出租車。好不容易找到讀書會所在的嚶棲書院,卻只見一片農田,聽見吱吱呀呀的蟬鳴。在我等待訪談的時候,拿出kindle,靜靜地讀完了一本買了很久的《肥肉》。書院里有老人、姑娘和瘦狗,一切安寧。其時,書院正在進行“半農半x”的活動,呼應那句“兩件事讀書耕田”。書院的創始人告訴我,讀書會實質是在推動全民閱讀。通過環境氛圍的營造,讓人們自覺或被動地形成良好的閱讀習慣,達到讀書會友、讀書為樂的目的。
嚶鳴讀書會的活動有三種類型:第一種是讀書演講會,即依靠知名作家來現場講演,吸引年輕人來參加活動,讓年輕人感受到這個城市中的讀書氛圍。第二種活動可以稱之為讀詩會和讀劇會,這些活動比較注重參與讀書的過程,鼓勵年輕人不但做一個聽眾,也能做一個表達者,用他們的身體和語言來表達自己。第三種是精讀會,就是深入閱讀,在閱讀后寫出一些成果與大家分享。讀書是為了以書為友,耕田是為了以自然為師。那天,暑氣正盛的下午,一群青年在聽完有關如何寫詩的課程后,扛起鋤頭拎起桶,走向田間地頭。讀書和耕田兩不誤。晚間風起,關于詩與未來的話題還在繼續。
剛入秋時,初見群學書院。同樣是為了推廣全民閱讀,同樣是遠離城市的喧囂。書院在每個周末的時候會有面向公眾的學術講演,探討社會問題,或者尋求心靈的安息。每年還會組織幾次游學的活動,讓人們換個環境好好閱讀。我去的那天暑氣已經消散,夏日的浮躁也漸漸褪去。雖是周末,地鐵上人卻不多。在地鐵上,我還是拿出了kindle,靜靜地把看到一半的《世事如煙》看了下去。
那日,山里正在進行“心理學視野中的自我與社會”深度研修班的初次講演。跟大多數的讀書會類似,有演講人,有聽眾,有書,有主持人。剛上山的時候,覺得這種安靜的、程式化的讀書會讓我有點水土不服——我似乎已經習慣了那種喧鬧的討論方式,也許是因為很久沒有走進課堂,心總是靜不下來。但聽到最后,卻發現遠離城市的山林或許更適合一起讀書,因為這里更加自由和廣闊,是思想需要的地方。安靜地坐下、聽講,帶著思想回家,閱讀、思考,也是另一種讀書之道。
所以讀書的意義不在于讀了什么書,讀了多少書,也不在于如何去讀書,而在思考、交流、批判和深入骨髓地踐行。
不管在畫廊里、家里、田間還是山上,閱讀都是一個程序化的實踐和社會化的過程。作為一個知識積累的過程,閱讀本身可能不具備什么社會性。而公共閱讀,卻能讓人們帶上自己的思考,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與更多的人探討一切。無論是以薔薇般綻放的從容,還是以櫻花般飄舞的熱情,公共閱讀總能推動社會的改變和發展。
(本文作者為謝菲爾德大學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