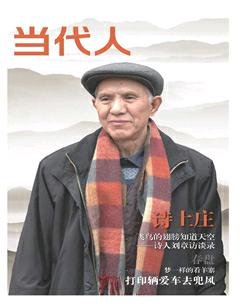布衣草履游春去
陳旭霞
“舞西風(fēng)兩葉寬袍袖,看日月搬昏晝。[滾繡球]千家飯足可周,百結(jié)衣不害羞。問甚么破設(shè)設(shè)歇著皮肉,傲人間伯子公侯。”戴長巾,穿寬衣大袖,呈飄逸自然之風(fēng),蹬芒鞋,拄竹杖,隨意所之,信步而行,讓慣常的踏青拾翠,觀景游春,多一份詩意,是一種聊以自慰的表面曠達(dá)的表現(xiàn)。
元代,棉花廣泛種植,人們的服飾在質(zhì)料上發(fā)生了較大變化,棉布成為主要衣料。但布衣、蒼頭、鶉衣、褐衣,還是平民百姓的主要服飾。元曲中平民服飾的描寫,為我們?nèi)嬲J(rèn)識元代社會提供了豐富資料。
白樸雜劇《董秀英花月東墻記》第五折:“誰想你入科場藝在先,金榜上名堪羨。脫卻了舊布衣,直走上金鑾殿。”無名氏雜劇《凍蘇秦衣錦還鄉(xiāng)》第一折王長者云:“久聞先生學(xué)成滿腹文章,只合早早立身顯姓,秉政臨民,卻還在此布衣之中,不圖進(jìn)取,當(dāng)是為何?”高文秀雜劇《須賈大夫誶范叔》第三折:“我如今卸下冠帶,仍舊打扮布衣,到客館中看須賈去,看他可還認(rèn)得我么?”費唐臣雜劇《蘇子瞻風(fēng)雪貶黃州》第三折:“住的是小窗茅屋疏籬,吃的是粗羹淡飯黃虀,穿的是破帽歪靴布衣,一身襤褸。”馬彥良套數(shù)[南呂·一枝花]《春雨》:“留待晴明好天氣,穿一領(lǐng)布衣,著一對草履,訪柳尋春萬事喜。”
這里,布衣雖有代指,但多為實寫。反映出廣大勞動者平日勞作與生活的艱辛、貧苦,也顯示出他們在衣著服飾上務(wù)實而又順乎自然的樂觀精神,而這種務(wù)實與順乎自然,讓他們每時每刻都散發(fā)著一種別樣的光彩:粗野、質(zhì)樸、自然。
蒼頭,原指戰(zhàn)國時主人戰(zhàn)旗下的軍隊,多以鄉(xiāng)黨的青年組成,因以青巾裹頭,故名。漢代,戰(zhàn)事減少,逐漸淪為奴隸,操持貴族邸宅的雜務(wù)。元代沿襲。張可久小令[雙調(diào)·慶東原]《次馬致遠(yuǎn)先輩韻九篇》:“蒼頭哨,驄馬驕,放轡頭也只到長安道。”高文秀雜劇《保成公徑赴澠池會》第四折楔子:“將我這駟馬高車前后擁,你看那虞候蒼頭左右沖,尋鬧吵顯威風(fēng)。”可見,在元代“蒼頭”仍指百姓和差役。
元曲中提到另一種平民服裝,就是窮苦人所穿的褐衣。褐衣是獸毛或粗麻制成的短衣。元曲中“褐衣”出現(xiàn)頻率很高,如馮子振小令[正宮·鸚鵡曲]《南城贈丹砂道伴》:“長松蒼鶴相依住,骨老健稱褐衣父。”褐衣借指貧賤者。喬吉小令[中呂·滿庭芳]《漁父詞》:“包古今不宜時短褐。”
“褐”的稱法,在先秦時期就有。據(jù)《詩經(jīng)·豳風(fēng)·七月》記載:“無衣無褐,何以卒歲。”《史記·平原君虞卿列傳》:“邯鄲之民,炊骨易子而食,可謂急矣,而君之后宮以百數(shù),婢妾被綺縠,馀粱肉,而民褐衣不完,糟糠不厭。”描寫當(dāng)時人民衣不遮體的貧困生活。古代詩歌典籍中的“毛褐”“短褐”“被褐”指的都是當(dāng)時農(nóng)夫、平民的衣服。這種衣服,質(zhì)地粗糙,重且不暖,與貴族穿的輕暖華麗的狐皮裘衣恰成鮮明對比。元曲中的褐衣記錄元代百姓的生活,傳遞著元代社會特有的時代信息和濃郁的文化氣息。
鶉衣也是元代窮人的常服。湯舜民小令[中呂·山坡羊]《書懷示友人》:“田園荒廢,箕裘陵替,桃源有路難尋覓。典鶉衣,舉螺杯,酕醄醉了囫圇睡,啼鳥一聲驚覺起。悲,也未知;喜,也未知。”“鶉衣”本是破破爛爛的衣服,還要典掉,可見其貧窮。
元曲中對文人服飾作了最真實的描繪,反映了元代文人極度貧困的生活境遇,如王實甫雜劇《呂蒙正風(fēng)雪破窯記》中,呂蒙正“一貧如洗,在此少陽城外破瓦窯中居止”,夫妻倆“尋不的一升兒米,覓不的半根柴,兀的不誤了齋。麻鞋破腳難抬,布衫破手難揣,牙關(guān)挫口難開,面皮冷淚難揩。”無名氏雜劇《凍蘇秦衣錦還鄉(xiāng)》第一折寫蘇秦穿的“領(lǐng)破藍(lán)衫剛有那一條囫圇領(lǐng)”,住的是“那通也波廳,通廳土坑冷,兀的不著我翻來覆去直到明,且休說冰斷我肚腸,爭些兒凍出我眼睛。”沈從文說:“元代階級壓迫極殘酷,統(tǒng)治者早期出于恐懼知識分子反抗,有意把讀書人貶得極低,特別是對于南方讀書人。”元曲通過對文人服飾的描寫,直觀深刻地揭示了這種現(xiàn)象。
元代隱士服飾的描寫,反映了元代隱士生活。隱士的生活一般都很清苦,有的甚至連布袍也沒有,平時只能“露頂短褐,布襪草履”。即使家境較好的,服裝用具也很簡單,“衣服惟尚綢絹、木棉,若毳衣、苧絲、綾羅,不過各一二件而已。白綢襖一著三十年”。元曲中隱士服飾多反映渴望退隱山林后的閑適、安逸、自由的生活。如胡祗遹小令[雙調(diào)·沉醉東風(fēng)]:“蓑笠綸竿釣今古,一任他斜風(fēng)細(xì)雨。”不忽木套數(shù)[仙呂·點絳唇]《辭朝》:“布袍寬褪拿云手,玉簫占斷談天口。”張可久小令[南呂·金字經(jīng)]《湖上書事》:“竹枕蘆花被,草衣荷葉巾,一棹煙波湖上春。”鄧玉賓套數(shù)[中呂·粉蝶兒]:“丫髻環(huán)條,急流中棄官修道,鹿皮囊草履麻袍。”鄧學(xué)可套數(shù)[正宮·端正好]《樂道》:“舞西風(fēng)兩葉寬袍袖,看日月搬昏晝。[滾繡球]千家飯足可周,百結(jié)衣不害羞。問甚么破設(shè)設(shè)歇著皮肉,傲人間伯子公侯。”
這些描寫,表現(xiàn)了元代隱士服飾的特點:一是質(zhì)性自然,無繪飾之功,反映了取法自然、返樸歸真的審美追求。從質(zhì)地上看:竹為冠、葛為巾、布為袍、草為履。從色彩上看:皂布袍、皂絳、烏履,黑與白,占據(jù)了主導(dǎo)地位。這些服飾的一個突出特點,就是它們無不具有濃郁的野逸、休閑氣息,是飄然、淡然、自在、遺俗、簡樸的裝束,代表著冠帶袍笏、拘束刻板的官府生活以外的另外一種人生。款式寬松,無拘束之跡,借助服飾這一外在載體和形式,映襯出對安貧樂道以及對散淡無憂的生活方式的向往。
正如美國學(xué)者弗龍格所說:“任何一種時髦都離不開時代的思想和愿望。”戴長巾,穿寬衣大袖,呈飄逸自然之風(fēng),蹬芒鞋,拄竹杖,隨意所之,信步而行,讓慣常的踏青拾翠,觀景游春,多一份詩意,是一種聊以自慰的表面曠達(dá)的表現(xiàn)。服飾展現(xiàn)了隱士們擺脫痛苦與怨憤,轉(zhuǎn)移失意心理,以達(dá)到心理平衡、滿足自尊,追求心靈自由的精神狀況,也反映了當(dāng)時社會的思想文化背景,更為重要的是對等級服飾制度的一種挑戰(zhà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