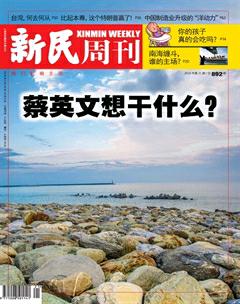生命該由支付能力決定嗎?
劉洪波
杭州媒體報道,一個女孩當活靶為其姐姐籌手術費。這名叫吉佳麗的女孩,出現在武林廣場,擺下一個游戲,自當人肉活靶,10元一次,聲稱籌集白血病骨髓移植的手術資金。經證實,吉佳麗的姐姐吉佳艷確實面臨移植缺少費用。吉佳麗設下“人肉靶子”兩小時無人問津,被帶到派出所后,她說,“我也很后悔,不應該用這種過激的方式”,并接受了民警的教育。
至于吉佳艷患病的情況,則在去年就曾引起關注,她父親車禍去世,她患病后為不拖累家里,留下書信離家出走,母親在昆明、成都等地街頭擺地狀尋女,還曾脫了上衣身背荊條,為自己不能為女兒治病“負荊請罪”,事經媒體報道,吉佳艷回到了母親身邊,現在她與弟弟配型成功,正等待手術。
按照網絡上流行的話說,媒體大概只能幫到這里了。吉佳麗沒能籌到錢,吉佳艷仍在等待她弟弟的骨髓來救命,手術仍不能進行。但事情已經不重要了,確有其事,不是騙人,大家就散了開去。
有些事情是無可奈何的,很多疾病在奪人生命,花再多的錢也無濟于事,于是治療就只是一種人道表示,或者說,是體現人類精神的一種象征性行為。有些疾病是可以治愈,甚至篤定可以治愈的,那么支付能力就成為生命的決定性因素,吉佳艷現在面臨的就是這樣一種支付能力的困局。生命平等,道理是這樣講的,但落實下來,人們的支付治療費用的能力,或者支配醫療資源的能力并不相同,結果就不一樣了。
類似的情況,現在可能還包括“達成諒解”的能力。我們已經在不少案件中看到,一個犯下罪行的人,因為獲得受害人的諒解,在定罪量刑上就可以從輕考慮。如果受害人已經死去,那么他的家人可以來進行決定是否諒解的活動。怎樣才能諒解呢,理論上,當然是要精誠所至,金石為開,但現實地說,用一定數額的錢來表示請求諒解的誠意,是必須的。
著名的陜西“撞人補刀”案件,受害人家屬不同意諒解,輿論上對此頗有微詞,覺得不合乎理性。按照“理性”,受害者已死,人死不能復生,如果諒解,家人可以得到一筆錢,兇手不判死刑,兩下都有好處;而不同意諒解,則兇手要伏法,受害者“人財兩空”。現在,人們就是這樣來體現“理性”的。實現諒解的能力,其實也就是支付能力。這不是直接的以財買刑,但確實使人看到罪犯因經濟能力而產生了差異。人們經常嘲笑“災難出英雄”的現象,指責“壞事變好事”的邏輯,犯罪后諒解則“雙贏”,還不至于是“災難出英雄”,但不也同樣是“壞事變好事”,人們卻又很樂觀其成。
在這種非常樂于看到“付費諒解”的理性后面,有著人們都承認和接受支付能力之作用的背景,甚至“錢應該在任何時候都起到作用”的意識。因此,如果有誰不同意“諒解”,使錢起不到作用,那就是對這種社會意識的冒犯,持有這種意識的人就會被視為“不理性”。
回頭來看前面那個妹妹街頭自當活靶為姐姐籌手術費的事情。在那個事情中,派出所也好,觀看者也好,很關心事情的真偽,要進行查證。但真偽有什么意思呢,如果是假的,人們會抨擊欺騙公眾感情;但如果是真的,也僅僅是讓人們有著一種自己沒有受騙的感覺罷了,并不是說如果情況屬實,手術費就有什么辦法。換言之,人們對一個人因手術費缺乏而無法治療,是不以為意的,潛意識中或者“理性”之中,認為這種情況是正常的。
以權力去分配資源,人人盡知其非;但“金錢面前一律平等”,就可以成為新的信念嗎?社會真的就該是這樣子嗎?就算“先進國家”都是這樣子,我們難道就一定要奔著這樣子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