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云起落武舉制
文/武兵
風云起落武舉制
文/武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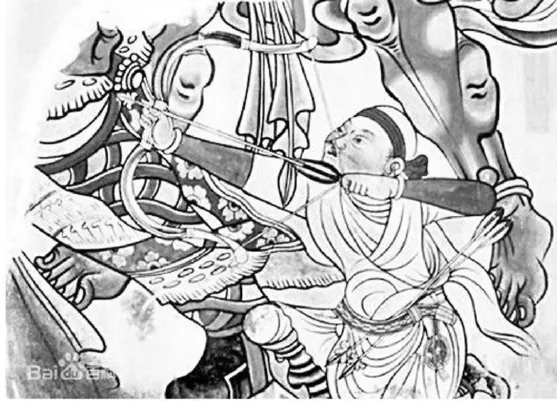
科舉是中國古代讀書人參加的人才選拔考試,是歷代封建王朝通過考試選拔官吏的一種制度。它由于采用分科取士的辦法,所以叫科舉。在中國歷史上,隋朝首先創(chuàng)立了選拔文官的科舉制度,到清光緒二十七年舉行最后一科進士考試為止,經歷了1300多年。武舉創(chuàng)立之前,科舉制度呈單軌運行狀態(tài),那些雖有武藝卻不善文的武士被拒之門外,這顯然不利于社會的穩(wěn)定和封建統(tǒng)治的加強。所以,增設武科,籠絡和安置武勇人才,完善和發(fā)展科舉制度,便成為社會的需要。
一、武舉制度的創(chuàng)立與艱難發(fā)展
武舉制度創(chuàng)始于唐代武則天執(zhí)政時期,至清朝時改稱武科。在科舉史上,武科延續(xù)的時間僅次于進士科,這與唐朝首創(chuàng)武舉之功是分不開的。科舉制度中武舉制度的正式出臺,改變了選文不選武的做法,給當時普通的武術人提供了一個進入官場的競爭機會。歷史上武舉考試一共進行過約500次。武舉主要選拔將才,與文舉比較,其重要性不及文舉,武舉出身的人地位也不及文舉的進士。
武舉制度能夠選拔優(yōu)秀的武術人才為皇權統(tǒng)治服務,這是武舉之所以能在歷史上延續(xù)1000多年的重要原因。雖然武舉制度為統(tǒng)治者培養(yǎng)了部分軍事人才,但出于對武人掌權的恐懼,后來的各代統(tǒng)治者根據自己的需要,對武舉制度時而重視時而忽略,因此幾經朝代變更,武舉制度步履維艱、時斷時續(xù)。
武則天長安二年(公元702年)發(fā)布“詔天下諸州宣教武藝”,并確定在兵部主持下每年為天下武士舉行一次考試,考試合格者授予武職。考試內容偏重于技勇,重點是馬上槍法,此外還要考靶射、騎射、步射、身高相貌、言論、舉重(翹關)、負重摔跤。唐代武舉制度還不夠完備,只能說是其創(chuàng)制時期,并且規(guī)定凡觸犯令者、工商之子、州縣衙門小吏不得參加考試。
唐德宗貞元十四年(公元798年),唐王朝停廢武舉,時間長達10年,這是武舉史上的首次被停廢,起因是諫議大夫田敦認為武舉人拿著弓箭出入皇城,可能會威脅到皇帝的安全,上表請求廢止武舉。直到唐憲宗元和三年(公元808年),在朝野上下的呼聲中,唐王朝恢復了武舉。但是到了五代時期(公元907-960年),由于軍閥混戰(zhàn),戰(zhàn)亂頻仍,武舉再次停廢。
到了北宋仁宗天圣七年(公元1029年),宋王朝重設武舉,恢復了自五代停廢的武舉考試。
二、武舉制度的完善與興盛
武舉的興盛時期是在明清兩代,特別是清代。
清朝統(tǒng)治者由于出身于游牧民族,善于騎射,因此對武舉的重視程度大大超過明代。
宋代開始,武舉被納入整個科舉體系之中,確定了三組考試的程序和外場考武藝、內場考策論兵書的考試辦法,規(guī)定武舉不能只有武力,還要考問軍事策略,比如孫吳(孫子、吳起)兵法等。武舉制度此間臻于規(guī)整。
到了明朝時武舉更改為“先之以謀略,次之以武藝”,把軍事謀略置于軍事技術之上,如果在答策的筆試中不及格便不能參加武試。初期的筆試考三題,試策兩題,另一題論考四書,后來四書的題目改為默寫武經。武試則最少要求騎射九矢中三、步射九矢中五。
至清朝時,改為先試馬、步射,馬射二回六矢中三為合,步射九矢中五為合。之后比力氣,包括拉硬弓、舞刀、舉石。弓分八、十、十二力,刀分八十、一百、百二斤,石分二百、二百五十、三百斤。合格者才考筆試。
宋以前并沒有“武狀元”之設。首名武狀元產生于宋神宗時,為福建人薛奕,后與西夏作戰(zhàn)時戰(zhàn)死。歷史上著名的武舉出身的武將有唐代的郭子儀(唐玄宗開元初年武舉異等),北宋徐徽言(文進士出身,后棄文習武,徽宗授武狀元),等等。
武科舉考試其實是等級考試,北宋二年(公元1078年)的《大小使臣試弓馬藝業(yè)出官法》中有規(guī)定:
第一等:步射一石弓,十發(fā)三中;馬上能射七斗弓,并掌握五種馬上格斗武藝;《孫吳兵法》十道題答出七道,“時務邊防策”五題“文理優(yōu)長”,法律題十道答出七道,就可以出任低級武官。
第二等:步射八斗弓,十發(fā)二中,馬上能射六斗弓,有三項馬上武藝,答出一半兵法題目和法律題目,可以見習低級武官。
第三等:步射六斗弓,十發(fā)一中,只有兩項馬上武藝,兵法、法律只能答三題的,記錄在案。
每三年考試一次,任命武官不過30人,后來逐步增額,以至于三人取一,每次都有百人入流,比文科舉得官還容易。
宋徽宗大觀四年(公元1110年),朝廷開始規(guī)定限額,每次考試只能取10人,其余的入武學。
南宋時期進一步改革武舉,南宋紹興五年(公元1135年)開始由皇帝親自“廷試”,合格的都賜予武進士,授予武官銜“保義郎”、“承節(jié)郎”等名目,但實授的職務往往并非軍官。
南宋乾道二年(公元1166年),武舉進士也比照文科,有第一、二、三名的排名。以后又規(guī)定參加廷試的都必須由各地方長官先行選拔,作為“武舉人”保送朝廷。這樣一來,武科舉體系與文科舉體系趨于基本相同。
南宋孝宗淳熙四年(公元1177年),明確了武科狀元之稱謂。朝廷規(guī)定,凡武狀元愿意從軍者,一律授予正將之職,第二、三名授予副將,第四、五名授予準備將。
明憲宗成化十四年(公元1478年),明朝武舉根據太監(jiān)王直的建議,以文科為例,設武科鄉(xiāng)、會試。
明弘治六年(公元1493年),定武舉六年一試,先策略,后弓馬,策不中者不準試弓馬。后又改為三年一試。考試內容主要是馬步、弓箭和策試。
明萬歷末年(公元1573年),曾有過一次實行改革的議論,有朝臣主張設“將材武科”,初場試武藝,內容包括馬步、箭及槍、刀、劍、戟、拳搏、擊刺等法,二場試營陣、地雷、火藥、戰(zhàn)車等項,三場各就其兵法、天文、地理所熟悉者言之。顯然易見,這是一個具有遠見卓識的提議,可惜并沒有引起朝廷重視,只是說說罷了,若提議被接受,將會產生極為深遠的歷史影響。
明崇禎四年(公元1631年),參加武會試的舉子中,能運百斤大刀者只有王來聘、徐彥琦兩人,然發(fā)榜后徐彥琦榜上無名,議論騰起。當時正“銳意重武”的崇禎皇帝認為有人作弊,將考官、監(jiān)試御史等一大批官員下獄、撤職,令倪元路、方逢年等主持復試。復試后選取百人,依照文榜例分三甲傳臚賜宴。崇禎親自調閱前三十名試卷,欽定一甲三人,王來聘居一甲第一名,也就是武狀元,授副總兵職。正式有武狀元之設,王來聘是第一人。之前明代武舉一直沒有殿試,也沒有設立一、二、三甲的區(qū)分和鼎甲名號。
明代武職多半由世蔭承襲,加上由行伍起家者,武舉只是個補充形式,所以明代武舉出人不多。值得一提的是明末名臣熊廷弼,他是一位難得的文武通材。《明史》本傳說他“身長七尺,有膽知兵,善左右射”。
清代武官雖然仍以行伍出身為“正途”,武舉出身次之,但武舉出身者數量不斷增大,在軍中占有相當比例。加上封建國家大力提倡武舉,制度日益嚴密,錄取相對公正,因此民間習武者對武舉考試趨之若鶩,民間習武之風興盛一時。
清代武舉制度中的考核,依文榜程序,大致分四個等級進行:
童試,在縣、府進行,考中者為武秀才。
鄉(xiāng)試,在省城進行,考中者為武舉人。
會試,在京城進行,考中者為武進士。
殿試,會試后已取得武進士資格者,再通過殿試(也稱廷試)分出等次,共分三等,稱為“三甲”。
一甲是前三名,頭名是武狀元,二名是武榜眼,三名是武探花。前三名世稱為“鼎甲”,獲“賜武堤及第”資格。
二甲十多名,獲“賜武進士出身”資格。
二甲以下的都屬三甲,獲“賜同武進士出身”資格。
殿試的規(guī)格很高,一般由皇帝親自主考。考試揭曉后,在太和殿唱名,西長安門外掛榜,并賜給武狀元盔甲,然后由巡捕營護送武狀元歸第炫耀恩榮。第二天,在兵部舉行盛大的“會試宴”,又賞給武狀元盔甲、腰刀等,賞給眾進士銀兩等。清代科甲等級差別甚大,同樣是武進士,一、二、三甲的等級和榮譽卻大不相同。自然狀元是出盡了風頭的,登第后的三天內可以披紅掛彩、上街夸官,真所謂春風得意,風光十足了。
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規(guī)定,武狀元授予御前一等侍衛(wèi),武榜眼、探花授予二等侍衛(wèi),再從二甲中選頭十名授予三等侍衛(wèi),其余全在兵部注冊授予守備等營職。雍正以后,各朝武進士的授官情況還有一些變化,不過所授品階基本上以康熙朝定制為準,沒有太大的變更。
清朝武舉各級考試通常每三年舉行一次,每科錄取人數也有定額。但常科以外還時常增設所謂“恩科”,常額以外也增加一點“恩額”。這類“恩科”、“恩額”都由皇帝直接掌握,無非籠絡人心,吸收更多的武勇人士為統(tǒng)治者效命。考試辦法差不多與明代一樣,分一、二、三場進行。
一、二場試考弓馬技勇,稱為“外場”;三場試考策論武經,稱“內場”。一場試內容為馬上箭法,馳馬三趟,發(fā)箭九枝,三箭中靶為合格,達不到三箭者不準參加二場。乾隆年間,一場又增加了馬射“地球”,俗稱“拾帽子”,專為考察伏射能力。二場考步射、技勇。步射九發(fā)三中為合格。所謂“技勇”實際上主要測膂力,一共三項。頭項拉硬弓,弓分十二力、十力、八力三號,另備有十二力以上的出號弓。應試者弓號自選,限拉三次,每次以拉滿為準。二項舞大刀,刀分一百二十斤、一百斤、八十斤三號,試刀者應先成左右闖刀過頂、前后胸舞花等動作。刀號自選,一次完成為準。第三項是拿石子,石子即專為考試而備的石塊,長方形,兩邊各有可以用手指頭摳住的地方,但并不深,也分為三號,頭號三百斤,二號二百五十斤,三號二百斤。考場還備有三百斤以上的出號石。應試者石號自選,要求將石提至胸腹之間,再借助腹力將石底部左右各翻露一次,叫做“獻印”,一次完成為合格。凡應試者,弓、刀、石三項必有兩項為頭號和二號成績,三號成績超過兩項者為不合格,取消三場考試資格。
三場是考文,當時叫“程文”,也稱“內場”,相當于文化課考試。內場考試對大多數武人來說比外場考試更難應付,所以考試辦法不得不屢有變動。最初是考策、論文章,“策”相當于問答題,“論”是按試題寫一篇議論文。順治時定為策二篇、論二篇,題目選自四書和兵書。康熙年間改為策一篇、論二篇,策題出自《孫子》、《吳子》、《司馬法》三部兵書,論題只從《論語》、《孟子》中出,考試難度有所降低。乾隆時,又改為策一題、論一題,題目都選自《武經七書》。到嘉慶年間,考慮到武人多不能文,所考策、論多不合格,而不少外場成績突出者又往往敗于內場,于是干脆廢除策、論,改為按要求默寫《武經七書》中一段,通常只一百字左右。這樣一味遷就,使內場考試的水平越來越低,最后差不多只是形式上的存在了。當時社會上歧視武人之風很盛,經此一改,武人更加被文士們看成粗野的武夫,武舉的社會地位與清代前期相比已大不如前了。
三、武舉制度的弊病和廢止
康熙皇帝已經注意到了科舉文武分途不利于造就兼?zhèn)淙瞬牡膯栴},他曾要求打破考試中的傳統(tǒng)界線,允許文武生員舉人交叉考試,武科舉人可以改考文科進士,文科舉人可以改考武科進士。
康熙認為:“如此則各得展其所學,文武兩途,皆得真才矣。”然而,整個清代,文武交叉考試者寥寥無幾,文武各成畛域而壁壘森嚴的現象越來越嚴重,文人不武,武人不文,文武兼長的人材也就越來越少。文武分途的考試制度培養(yǎng)了大批專門人材,卻很難造就出能文能武的博通人材,應該說這是科舉制度的弊端之一,也是清朝中后期政壇上出將入相人才日見匱乏的原因之一。
鴉片戰(zhàn)爭(公元1840年)以后,頻繁的御侮戰(zhàn)爭中逐漸顯露出武舉人材不能適應新的戰(zhàn)爭,除了長矛大刀與堅船利炮之間的差距外,更重要的還是基本素質和軍事思想上的差距。然而朝野上下株守陳規(guī),玩歲日,武舉考試一直被延續(xù)下去。
光緒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榮祿首先提出廢止武舉考試。他說:“自火器盛行,弓矢已失其利,習非所用,與八比試帖之弊略同。積弱之端,未始不由于此。”他主張各省創(chuàng)設武備學堂,以西洋軍事課程培養(yǎng)新式軍人。然而榮祿的倡議并沒有得到大多數朝臣的響應,武舉廢止一拖便是幾年。
光緒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照例舉行武舉會試——這是中國歷史上最后一次武會試。不久,要求改革的呼聲又一次響起來,“內外臣工請變更武科舊制,廢弓、矢、刀、石,試槍炮”。然而依舊未能實行改革。
此時的清政府內憂外患,武舉制度已經不能有效發(fā)揮其政治功能和社會功能,對外不能抵御外敵入侵,對內不能維持社會秩序,甚至成為社會的對立面。這時,地方督撫的權力開始膨脹,打破了清初的絕對皇帝權威,他們開始對舊有的武舉制度提出自己的看法,在武舉的存廢問題上與清朝中央勢力展開了三個階段的爭奪:其一,督撫上奏,謹慎處理;其二,危機重重,有效采納;其三,困境革新,廢除武舉。隨著湘軍、淮軍的編練和軍事學堂的開辦,武舉制度的功能被替代,最終在光緒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清政府宣布廢止武舉制度。至此,武舉制度徹底退出了歷史的舞臺。
無疑,武舉制是中國武術史上濃墨重彩的一筆,與文科制的并行設立,在當時重文輕武的社會背景下是體現武術人的價值的一個有力依托,對武術的發(fā)展產生了積極的、深遠的影響。但由于武舉制度自身的局限性,武舉制在一定程度上又制約了武術的發(fā)展,延緩了武術發(fā)展的步伐。特別是武舉制度在清朝的延續(xù)和廢止,為我國武術運動在民間全面開展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可以說,武舉制度的結束,是武術運動發(fā)展的一個重要節(jié)點。當下,各種臻于完善的武術制度,若不能與時俱進,順應時代,最后也只能是步武舉制度的后塵,被淘汰,被拋棄。
四、武舉制度的軼聞趣事
清代的武會試,自順治三年(丙戌)開科,到光緒二十四年(戊戌)截止,一共進行了112次。也就是說一共產生了112個武狀元,還各有112名榜眼和探花,總計武科前三名(鼎甲)是336名。
112名武狀元的姓名都有記載,但目前能確知其籍貫者只92人,其余20人還有待于考求。這92個武狀元,河北出的最多,共32名。以下山東13名,浙江8名,江蘇6名,河南、山西各5名,廣東4名,甘肅、福建各3名,江西2名,四川、陜西各1名。此外,漢軍旗6名,滿軍旗3名。
也許這個統(tǒng)計不是很完備,也不是很準確,不過大體可見各省武舉基礎的差別。所謂武舉基礎,可從兩個方面認識,一是尚武風氣,二是文教水平。
清代武舉為國家提供了大批人才,其中產生了不少杰出人物。
科舉考試的最高榮譽是“獨占三元”,即一個人得了三個第一名:鄉(xiāng)試第一解元,會試第一會元,殿試第一狀元。清朝二百多年中,文科得“三元”者僅2人,一個是乾隆時代江蘇常州的錢,另一個是嘉慶時代廣西臨桂的陳繼昌。武科得三元者只有1位,此人是清初浙江仁和的王玉。說來這個王玉不止是“獨占三元”,而是“獨占四元”。他本來是明朝崇禎十二年(1639)浙江武鄉(xiāng)試的解元,入清以后又參加新王朝的武舉,獲順治八年(1651)武鄉(xiāng)試解元,接著獲順治九年武會試會元,殿試又得狀元,是名副其實的“連捷三元”。王玉體貌偉岸,武力絕倫,甚得順治賞識,曾任天津鎮(zhèn)總兵等職。
江蘇泰州人劉榮慶,是乾隆四十九年甲辰科(公元1784年)武狀元。只隔了3年,他的弟弟劉國慶又獲乾隆五十二年丁未科(公元1787年)武狀元。兄弟兩人都是武狀元,這在清朝是唯一一例。
(編輯/張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