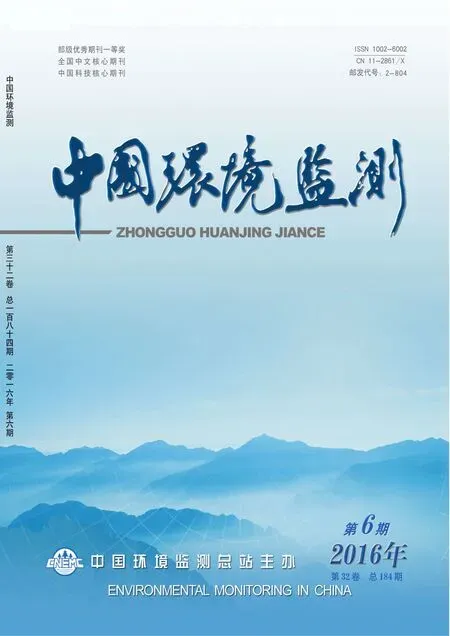區域污染治理能力與排污規模的協調性評價
李名升,陳遠航,張鳳英,武中波,谷 萍,騰建禮
1.中國環境監測總站,國家環境保護環境監測質量控制重點實驗室,北京 100012 2.吉林省環境監測中心站,吉林 長春 130011 3.中國環境保護產業協會,北京 100037
區域污染治理能力與排污規模的協調性評價
李名升1,陳遠航1,張鳳英1,武中波2,谷 萍1,騰建禮3
1.中國環境監測總站,國家環境保護環境監測質量控制重點實驗室,北京 100012 2.吉林省環境監測中心站,吉林 長春 130011 3.中國環境保護產業協會,北京 100037
為分析區域排污規模與污染治理的協調性,構建了排污規模與污染治理協調度模型,并以2006、2013年的數據對模型進行實證分析。結果表明,制約排污規模和污染治理協調性的主要矛盾是污染治理能力的落后,全國70%以上地區污染治理能力均滯后于污染物產生規模;國內治理能力在研究期間不斷提高,區域差異在不斷縮小,治理能力過度滯后的省份由14個減少到2個;除江蘇外2013年其余各地區均有1項或多項污染物的治理能力滯后,其中生活廢水治理能力滯后的區域最多;經濟發展水平是影響協調性的重要因素,2013年協調度與地區人均GDP基本呈線性關系。模型實證計算結果與主觀判斷也較為吻合,具有一定的推廣應用價值。
協調度;排污規模;污染治理;區域差異
污染物是經濟發展的“副產品”[1],而污染治理設施是減少副產品對環境系統危害的最后屏障[2-3]。有研究表明,污染治理投資對改善環境質量、遏制環境惡化具有重要意義[4-5]。污染治理能力越強,污染物對環境造成的損害越小,但考慮到經濟成本,污染治理能力理應與污染物產生規模適度協調。目前,協調的概念在經濟與環境系統協調發展方面應用較多[6-9],普遍通過構建協調度模型來衡量系統協調發展程度[10-11]。但將協調的概念運用到排污規模與污染治理能力領域的研究目前尚未見諸報道。
本文借鑒經濟與環境系統協調發展模型,構建排污規模與污染治理協調度模型,并將模型應用到省級行政區進行定量評價,以期為中國污染治理能力建設提供科學支撐。
1 模型構建
1.1 評價模型與步驟
對環境系統而言,污染物產生量越少越好,同時污染治理能力越強越好。但從經濟角度看,治理能力的閑置又是不經濟的。因此,污染治理能力恰好將污染物產生量處置完畢是最經濟且環境擾動最小。基于此,文章模型設計的基本思路為先假設全國當年排污規模和污染治理的平均協調度為1,計算區域協調度。然后,根據全國當年污染治理能力的大小,確定合適的臨界值,作為區域協調與否的閾值。
1.1.1 指標體系設計
人類活動向外界排放的污染物主要包括廢水、廢氣、固廢3大類。由于生活廢氣主要排放形式為面源污染,尚未形成規模化治理,因此研究時,廢氣污染源僅考慮工業廢氣。工業固體廢物的一種重要處理方式是貯存,并未完全處理,因此固體廢物僅考慮生活垃圾。
由此,排污規模和污染治理能力2個子系統均由工業廢氣、工業廢水、生活廢水、生活垃圾4個一級指標構成。在一級指標下,排污規模子系統的指標納入各一級指標的主要污染物產生量,污染治理能力子系統的指標納入治理能力和運行費用。詳見表1。

表1 排污規模與污染治理能力評價指標體系
注:括號內數字為指標權重,權重確定方法見1.2小節。
1.1.2 二級指標數值標準化
為消除不同指標在單位和變異程度上的差異,采用下式對全國各省(區、市)數據進行標準化處理:
(1)
1.1.3 計算一級指標評價值
一級指標的評價值由下式計算確定:
(2)
式中:ωij為指標權重,其他變量含義同式(1)。
1.1.4 計算一級指標子協調度
各一級指標的子協調度定義為污染治理與排污規模的商,即:
(3)
式中:Di為第i個一級指標的協調度。
1.1.5 計算區域總體協調度
對某地區k,系統總體協調度D由各一級指標協調度的平均值計算得到:
(4)
當D值接近于1時,區域污染治理能力建設與污染物產生量兩者的協調程度越接近于全國平均水平,且D值越大,污染治理能力建設越超前于污染物排放規模。
1.2 指標權重確定
對于排污規模子系統的二級指標,考慮到等質量的不同污染物對環境的危害不同,根據原國家計委、財政部、原國家環保總局、原國家經貿委等聯合發布的《排污費征收標準管理辦法》(國家計委、財政部、國家環保總局、國家經貿委令第31號)中關于各類污染物的折算系數對SO2、NOx、煙(粉)塵、化學需氧量、氨氮的權重進行確定。對于一級指標和污染治理子系統的二級指標,采用等權重處理。各指標權重見表1中括號數字。
1.3 數據來源
排污規模、污染治理能力兩個子系統的二級指標數據均來自《中國環境年鑒》[12]和《中國環境統計年鑒》[13]。中國自2006年才開始統計NOx排放量,因此實證分析的年份選擇2006、2013年。由于西藏污染物排放量極少,故所有數據和討論均不涉及西藏自治區。
1.4 協調類型劃分
《中國城市建設統計年鑒》[14]中的數據表明,2012年全國城市污水處理率和生活垃圾無害化處理率分別為87.4%、84.8%,2006年分別為55.7%、53.0%。即2012年全國有15%左右的廢水和生活垃圾未被處理。由此認為,2013年全國污染治理能力評價值高出排污規模評價值15%左右處于基本協調水平;同理,2006年高出45%左右處于基本協調水平。在此基礎上,以協調度提高或降低20%為一個區間,根據協調度評價值將協調類型劃分為7種,詳見表2。

表2 協調類型劃分標準
2 結果與討論
2.1 協調性評價結果
將原始數據帶入評價模型,結果見圖1、圖2。

圖1 2006、2013年中國各地區排污規模與污染治理的協調度
2006年,30個地區中僅6個地區協調類型為基本協調或治理能力超前,其中廣西、天津、上海、貴州地區為基本協調,浙江治理能力略微超前,北京治理能力明顯超前。其余24個地區中,4個地區治理能力略微滯后,6個地區治理能力明顯滯后,14個地區為過度滯后。若將中國作為一個整體進行評價(D=1),2006年中國治理能力剛剛跨越過度滯后階段,處于明顯滯后的最初級。
2013年,8個地區協調類型為基本協調或治理能力超前,其中北京、上海、天津為治理能力略微超前,浙江、河北、江蘇、廣東、遼寧為基本協調。其余22個地區中,8個地區治理能力略微滯后,12個地區治理能力明顯滯后,僅甘肅、寧夏地區為過度滯后。若將中國作為一個整體進行評價(D=1),2013年中國整體處于略微滯后的中期。
2.2 討論
對2006、2013年中國排污規模和污染治理的協調度進行對比發現:
1)各地區污染治理能力普遍滯后。無論是2006年還是2013年,全國70%以上地區污染治理能力均滯后于污染物產生規模。因此,制約排污規模和污染治理協調性的主要矛盾是污染治理能力的落后。并且從2013年僅有8個地區污染治理與排污規模基本協調的現狀看,在未來一段時間,這一矛盾仍將繼續存在。
2)排污規模和污染治理的協調性在提高。2006—2013年,基本協調或治理能力超前地區由6個增加到8個,過度滯后地區由14個減少到2個,中國整體協調程度從治理能力明顯滯后過渡到略微滯后階段,說明國內污染治理能力在不斷增前,排污規模和污染治理的協調性不斷提高。
3)協調度類型分布由“啞鈴型”向“紡錘形”變化。2006—2013年,大部分地區的協調類型由兩頭向中間發展,具體表現為治理能力明顯超前地區消失,治理能力過度滯后地區由14個減少為2個。由于治理能力是制約協調性的主要矛盾,協調度類型的變化體現出國內污染治理能力的建設逐步趨于理性,更加有針對性。
4)排污規模和污染治理協調性的地區差異在縮小。從極值看,2006年協調度數值最高的北京是數值最低的吉林的4.6倍,而到2013年這一數值降低至3.0倍。從總體來看,30個地區協調度的變異系數由0.40減小到0.28。因此,無論是從極值還是總體看,協調性的地區差異均表現出縮小趨勢。
5)除江蘇外2013年其余各地區均有1項或多項污染物的治理能力滯后(圖3)。

圖3 2013年污染治理能力滯后指標的地區分布
雖然2013年有8個地區為基本協調或治理能力超前,但從各地區4項指標看,僅江蘇省4項指標的子協調度均大于1.15,4項指標的治理能力均出現一定程度超前。其余29個地區中,3個地區有1項指標治理能力滯后,4個地區有2項指標治理能力滯后,8個地區有3項指標治理能力滯后,14個地區有4項指標治理能力均滯后。分指標看,工業廢氣治理能力滯后地區有18個,工業廢水治理能力滯后地區有17個,生活廢水治理能力滯后地區有21個,生活垃圾治理能力滯后地區有16個。因此,生活廢水是影響協調性的主要影響指標。
6)協調性與經濟發展水平密切相關。從定性角度看,2013年基本協調和治理能力超前的地區全部分布在東部沿海發達地區,而治理能力過度滯后和明顯滯后的地區全部分布在中西部欠發達地區。從定量角度看,2013年協調度與地區人均GDP基本呈線性關系(圖4),線性回歸方程的擬合優度達0.66。因此,經濟發展水平是影響協調性的重要因素。

圖4 2013年各地區協調度與人均GDP散點圖
3 結論與討論
構建了排污規模和污染治理的協調度模型,并以2006、2013年的數據對模型進行實證分析。模型的構建過程充分考慮了中國污染物排放現狀和污染排放與污染治理的相互關系,實證計算結果與主觀判斷也較為吻合,說明所構建的模型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國內排污規模和污染治理的協調關系,具有一定的推廣應用價值。
模型的局限性在于評價結果不能直接進行縱向對比。由于原始數據標準化方法實際是將數據轉化為區域污染物規模/治理能力占全國的比重,其潛在條件為當年全國整體的協調度為1。因此,不同年份各一級指標的子協調度是針對當年全國平均水平的數值,在進行縱向比較時不能直接比較,而在協調度類型劃分時,各年度協調類型的閾值均不同。以基本協調為例,2006年當協調度1.45≤D<1.8時判定為基本協調,但2013年當協調度為1.15≤D<1.4時即可判定為基本協調。如天津市2006、2013年協調度分別為1.66、1.59,單從數值上看有所降低,協調類型卻由基本協調變為治理能力略微超前。為此,本文根據全國平均治理水平對各地區協調度進行類型劃分,可在一定程度上克服這一問題,但數值本身仍然不可進行直接比較,只能進行區域間的橫向比較。
從實證分析結果來看,國內污染治理整體滯后于排污規模,污染治理能力落后是制約區域排污規模和污染治理協調性的主要矛盾,但治理能力在研究期間不斷提高,區域差異在不斷縮小,治理能力過度滯后的省份由14個減少到2個,區域間協調度的變異系數由0.40減小到0.28,從而推動了協調度的不斷提高。同時看到,除江蘇外,其余地區在工業廢氣、工業廢水、生活廢水、生活垃圾4項污染物中均存在至少有1項治理能力滯后,各地區污染治理能力建設仍任重道遠。
[1] 周生賢.中國特色環境保護新道路的哲學思考[J].環境教育,2009(6):5-12.
[2] 董文福,傅德黔,努麗亞.我國環境污染治理投資的發展及存在問題[J].中國環境監測,2008,24(4):87-89.
[3] 職音.從監測角度對環境污染治理設施存在問題及運行模式的認識[J].中國環境監測,2000,16(2):2-3.
[4] ZHAO J J,CHEN S B,WANG H,et al.Quantifying the impacts of socio-economic factors on air quality in Chinese cities from 2000 to 2009[J].Environmental Pollution,2012,167:148-154.
[5] 楊晨朗,李本綱.基于遙感資料的北京大氣污染治理投資對降低PM2.5的效能分析[J].環境科學學報,2015,35(1):42-48.
[6] TAN F F,LU Z H.Study on the interaction and relation of society,economy and environment based on PCA-VAR model:as a case study of the Bohai Rim region,China[J].Ecological Indicators,2015,48:31-40.
[7] GROSSMAN G,KREUGER A.Economic growth and the environment[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95,110(2):353-377.
[8] 張軍.基于環境庫茲涅茨模型的經濟與環境關系分析[J].中國環境監測,2013,29(2):91-94.
[9] 董廣霞,丁中元,安海蓉,等.三峽地區工業行業環境與經濟行為特征分析[J].中國環境監測,2008,24(4):64-66.
[10] 李名升,佟連軍.經濟-環境協調發展的演變及其地區差異分析[J].經濟地理,2009,29(10):1 634-1 639.
[11] 黃建歡,楊曉光,胡毅.資源、環境和經濟的協調度和不協調來源——基于CREE-EIE分析框架[J].中國工業經濟,2014(7):17-30.
[12] 中國環境年鑒編輯委員會.中國環境年鑒2007—2014[M].北京:中國環境年鑒社,2007-2014.
[13] 國家統計局,環境保護部.中國環境統計年鑒2007—2014[M].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07-2014.
[14] 中華人民共和國住房和城鄉建設部.中國城市建設統計年鑒2012[M].北京:中國計劃出版社,2013.
Regional Assessment on the Coordinative Degree between Regional Pollution Treatment Capacity and Pollution Scale
LI Mingsheng1,CHEN Yuanhang1,ZHANG Fengying1,WU Zhongbo2,GU Ping1,TENG Jianli3
1.Stat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Key Laboratory of Quality Control in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China National Environment Monitoring Centre, Beijing 100012, China 2.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Centre of Jilin Province, Changchun 130011, China 3.China Association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dustry, Beijing 100037, China
To analyze the coordinative relation between regional pollution scale and pollution treatment, a pollution scale-pollution treatment coordinating degree model was established. Data of 2006 and 2013 were used to do empirical analysis on the model in China.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lagging pollution treatment capacity was the main restraint on coordinative relation between regional pollution scale and pollution treatment. The pollution treatment capacity was fallen behind pollution production scale in 70% regions of China. Compared 2013 to 2006, the pollution treatment capacity was improving, and regional differences were continually narrowed. The number of over backward provinces was reduced from 14 to 2. In 2013, all regions had lagged pollution treatment capacity in one or more categories of pollutants except Jiangsu. Most regions lacked the pollution treatment capacity of sanitary wastewater.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was the principal factor affecting the coordinative degree. According to the data in 2013, there was a linear relationship between coordinative degree and regional per capita GDP. The empirical calculation results were consistent with the subjective judgment, and the model is worth being promoted widely.
coordinative degree;pollution scale;environmental pollution treatment;regional difference
2015-09-05;
2015-11-16
國家自然科學基金(41601608,41501556)
李名升(1981-),男,山東安丘人,博士,高級工程師。
騰建禮
X821
A
1002-6002(2016)06- 0020- 06
10.19316/j.issn.1002-6002.2016.06.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