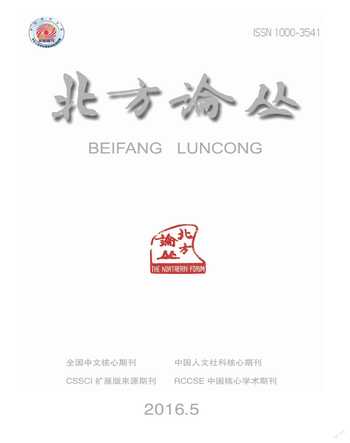武田泰淳反戰思想的生成及價值取向
王偉軍
[摘 要]戰爭與中國是武田泰淳文學世界中不可回避的時代命題。侵華戰爭期間,既是僧人,又是士兵;既向往中國文化,又充當侵略者的青年武田,書寫怎樣的中國觀和戰爭觀。發掘武田從軍思考的要義,結合其青春經歷和戰爭中創作的詩歌、隨筆、報告文學的隱喻,厘清其文學上反戰思想的生成。從武田泰淳反戰思想、反戰姿態和現實價值的意義上,重申日本軍國主義戰爭罪責,駁斥歪曲侵華戰爭歷史、居心叵測日本文人的伎倆,為日本執政當局一意孤行,潛心打造“新安保法案”的謬誤敲響警鐘即為本文之題旨。
[關鍵詞]武田泰淳;反戰思想;現實價值
[中圖分類號]I31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3541(2016)05-0053-06
武田泰淳既是一位熱衷于中國文學研究的學者,也是日本戰后文壇“第一戰后派”的代表性作家之一。1937年10月,25歲的青年武田應召入伍,作為侵華日軍的一名輜重補充兵踏上華中戰場,直到1939年9月退伍回國,他度過長達兩年的戰地生涯。可以說,武田是一個生不逢時的作家。因為在那樣的時代,一個日本文人一旦與中國和戰爭聯系在一起,他的命運便注定是多舛的。在戰爭中,去體驗中國不僅框定武田未來的人生,反省戰爭、思考中國也成為其一生精神探索的命題。那么,戰爭期間武田的生存實態與文學敘述顯露著怎樣的軌跡和傾向,帶給我們怎樣的啟示和借鑒,理應成為有必要探究的課題之一。
一、青年武田和他的苦惱
武田泰淳1912年2月12日出生于東京本鄉區的潮泉寺(凈土宗)。其父親為潮泉寺住持大島泰信。武田出生后,以大島已故師僧武田芳淳養子的名義,被取名為“武田覺”,繼承武田家的佛教衣缽似乎成為他未來的人生宿命。應該說,出生在一個世襲制極具宗教色彩的家庭,成為武田泰淳的第一抹生活底色。“上了初中以后,每晚父親都會給我講授一個小時《十八史略》和《日本外史》。持續了一年之后,父親贊揚我說:‘今年你學習的不錯呀,可是,他并沒有買什么禮物給我”[1](p327)。少年時期的武田泰淳,不僅過著優越的寺院家庭生活,接受良好的學校教育,在佛學典籍和漢學知識的掌故上,也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浦和高中時代的武田經常出入學校圖書館,閱讀唐詩、中國古典小說《紅樓夢》,以及魯迅、胡適等中國作家的作品。《十八史略》故事的熏陶,飽讀漢學書籍,這一系列有關中國歷史、文學、文化知識的了解和介入,成為武田接受初等教育的一個有機部分。
1931年4月武田高中畢業,考入東京帝國大學中國文學專業,5月15日得授僧人度牒并更名為“武田泰淳”。5月30日,因參加無產階級反帝活動,被東京本富士警察署拘留。武田的青春波折和苦惱不僅緣于佛教家庭出身、“紅色僧人”身份,更在于那個不平靜的時代。“從明治時期確立天皇制國家以來,日本一貫繼續執行侵略中國的政策。尤其‘滿洲與朝鮮鄰接,曾經是甲午、日俄兩次戰爭的戰場,因而成了日本大陸政策的中心目標”[2](p12)。1931年,日本悍然發動的“九一八事變”并不是偶然的。在日本帝國主義迫切想把國內金融危機轉嫁給中國,無產階級反帝、反戰運動如火如荼的時代,對熱愛和憧憬中國的一介書生武田和尚來說,他的青春將注定是一個多重苦惱交織的世界。
(一)被捕、轉向、退學與寺院生活
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日本,是軍國主義侵略思想不斷膨脹,積極推行“對外擴張”國策的時代。正值青春期的武田泰淳曾遭兩次被捕、被迫轉向和最終退學與當時的潮流時勢息息相關。
武田參加無產階級反戰運動是在浦和高等學校時代。“那時,正是左翼活動盛行的時期。武田說:“我在浦和高中時代就已經參加反帝組織了……上大學那年(1931年)的五月末,我和同學一行三人去中央郵局散發傳單。隨后兩人被捕,其中一個就是我……我被拘捕到丸之內警察署,之后又轉送到本富士警察署,大約被拘留了三十天左右”[3](p15)。1932年5月,武田因散發《第二無產階級報》再次被警察署逮捕,拘留一個月的時間。一年之內兩次被逮捕拘留的體驗,給武田的內心留下茫然屈辱、消沉苦悶的青春夢魘。正像1949年8月武田的自傳小說名《冷卻的火焰》本文日語原文著作的名稱及引文皆為筆者自譯。一樣,脫離無產階級革命運動,思考“轉向”自然成為被冠以“紅色僧人”名號的武田的必然結局。青年學生武田泰淳覺悟到,日本軍國主義一意孤行,選擇對內打壓、對外戰爭的時局不是他一個人反對得了的,希望成為反帝、反戰無產階級革命斗士的幻想是不現實的。武田泰淳于1949年1月和8月發表的自傳體小說《復仇》和《冷卻的火焰》就充分證實了這一點。正如《復仇》中主人公“大島”所描述的那樣,武田自己被捕入獄給家人帶來的影響,始終縈繞腦海,以至于內心的苦悶一直持續到日本戰敗投降。每個月,警察署特高課來訪的情景,成為他不堪回首又難以忘懷的青春烙印。
1932年以后,被迫“轉向”的青年武田從東京帝國大學退學,寓居于長泉院。此間,武田泰淳接受度牒、登陸僧籍、最終獲取僧侶資格,成為凈土宗名副其實的和尚。武田的人生儼然顯露著邁向僧侶生涯的趨勢,但繼承家傳衣缽,并非武田自我選擇的結果,更不是他的興致所在。
武田描述的情景與感受,與日本明治時代的啟蒙思想家福澤諭吉的論斷不謀而合。福澤諭吉曾在《文明論概略》的“日本文明的來源”一章中寫道:“宗教是支配人類靈魂的東西,本來應該是最自由、最獨立、絲毫不受他人控制,絲毫不仰賴他人力量而超然獨立的。但是,在我們日本則不然……上野的東叡山、東京芝區的增上寺,這些寺院沒有一處不是憑借政府的力量而興建的……皈依佛教的人沒有信教的誠心,也就不足為奇了……政府下令允許全國僧侶食肉娶妻,據這一法令來解釋,以前僧侶之所以不食肉不接近婦女,并不是因為尊奉宗教的教義,而是沒有得到政府的許可,所以才不敢這樣。”[4](p143)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窺見日本近代佛教畸形發展的諸多影像,不僅封建色彩濃厚,具有強烈的政權依附性,還顯露著違背佛教宗旨的欺騙性。武田雖然并不反對佛教的教義,但對日本凈土宗寺院里的夫妻生活、接受布施、近乎不勞而獲的行為卻極其反感。由此可見,寺院生活的實態與熱衷無產階級革命思想,在武田內心的矛盾性存在是尤為明顯的,熟讀馬克思《資本論》的僧人武田的青春體驗,對其形成抗拒當局政治壓迫的意識,以至于反戰思想的萌生,打造至關重要的現實根基。實際上,抗拒時局的情緒、向往中國的熱忱、漢學知識的熏陶使得這位日本青年逐漸擁有屬于自己的知識儲備,只是在等待成為一介文人契合點的出現。
(二)“中國文學研究會”時代
從東京帝國大學退學后,武田與其大學同學竹內好、岡崎俊夫及東京部分中國留學生來往密切。1934年8月竹內好作為發起人,與武田泰淳、岡崎俊夫等5位同人,聯合創立“中國文學研究會”。次年3月,《中國文學月報》創刊,成為其機關刊物。“中國文學研究會”的成立,開啟20世紀日本國內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先河。正如日本文學評論家渡邊一民2010年出版的《武田泰淳和竹內好》后記中所述:“我深切地感到,從一九三零年代直到七十年代末期,始終思考中國和日本問題的學者中,除了這兩位(武田泰淳和竹內好)再無他者。”“中國文學研究會”的成立,給茫然無措的武田帶來新的契機。武田的歸屬,不僅表現他與竹內好、岡崎俊夫的志同道合,而就個人志向而言,他的生活追求是以文人為伍,以感受和探索真實的中國為志趣所在。如果說作為學術骨干加入“中國文學研究會”,致力于中國文學的研究是武田青春軌跡的十字路口。那么,接下來的“謝冰瑩事件”,應征入伍、被派往華中戰場便是武田多舛人生命運的風向標。
作為“中國文學研究會”的核心人物,竹內好和武田泰淳為更加直觀地了解中國,與當時的在日中國文人、留學生積極交往,其中包括郭沫若、王瑩、杜宣、謝冰瑩等。1935年春,以《從軍日記》聞名的民國女作家謝冰瑩來到日本。武田不僅教授謝冰瑩日語,還幫助她尋找公寓,來往十分密切。同年春,偽滿洲國皇帝溥儀應邀赴日,謝冰瑩拒絕參加迎接的隊伍,警方便懷疑她有暗殺溥儀之嫌,將其逮捕。受謝冰瑩的牽連,武田泰淳第三次被捕,關押在東京目黑警察署約一個半月之久。“謝冰瑩女士的風波,給當年二十四歲的我帶來很大影響。那件事以后,我變得十分警惕,碰到任何事首先持懷疑態度,然后再去做。也就是說,我告別天真善于周旋起來了”[5](p175),“每逢臨近五月,我都會變得神情緊張,內心惴惴不安。因為此前的三次被捕都是在五月份”[5](p180)。“謝冰瑩事件”帶給武田的不僅有肉體的痛苦,還有精神的震撼。謝冰瑩在1982年整理出版的著作集《我在日本》的自序中曾寫道:“尤其難得的是武田泰淳。他過去也曾入獄兩次,聽說很快就放出來了,只有第三次,他因受了我的牽累,坐了一個多月的牢,居然沒有半句怨言……。”參見1984年東大圖書有限公司出版的謝冰瑩著《我在日本》自序第2頁。是這種純粹的超越民族主義的友情體現,確乎難能可貴。武田對中國友人的情感是真摯的,對中國文學探索的熱望是強烈的。謝冰瑩事件后,武田泰淳徹底脫離左翼運動。作為“中國文學研究會”同人,此時的武田泰淳全然是一位中國文學研究者的姿態和走向。而對以一個輜重補充兵的身份,拿起三八式步槍,到留學生朋友的祖國參戰是缺乏心理準備的。所以,一直與命運抗爭的武田,在戰場上,生成厭戰情緒、反戰思考恰恰在情理之中。
二、反戰思考的發端
(一)走向戰場的武田
1937年7月武田泰淳的《袁中郎論》發表在《中國文學月報》上,竹內好才開始贊嘆地說道:“武田也寫出這種水準了啊!”[3](p145)遺憾的是,兩個月后,武田就作為侵華士兵奔赴中國戰場了。“那時,我是反對戰爭的”[6](p28),“對我而言,這是非常可恥、痛苦和令人厭惡的”[6](p38)。對武田來說,產生這種“可恥”“痛苦”“令人生厭”的情緒是在情理之中的。“入伍通知書終究還是來了。于是,我作為侵略留學生們祖國的輜重二等兵出發了。曾經自稱深愛中國、中國人、中國文化的我,難道原來的那種愛是虛偽的嗎?槍發下來,那種三八式步槍我會使用。就這樣,我對中國的真情毫無防備地變成了假意。在吳淞口一登陸,滿眼都是平民橫七豎八的尸體,也有被戰車壓碎的戰友。無數的房屋被燒毀,空氣中到處彌漫著尸體的腐臭。原本是個和尚,在這種狀況下,你還能說自己深愛著世上的每一個人嗎?難道中國人不屬于蕓蕓眾生這一群體嗎?我這個二等兵,坐汽車、乘小船繼續走在行軍的路上”[1](p307)。日本軍國主義國家機器的殘酷,對武田的傷害是雙重的。戰爭給中國帶來的滿目瘡痍,行軍途中剪不斷、理還亂的愁緒,無時無刻不在拷問武田的內心。值得注意的是,面對戰爭的殘酷現實,武田并沒有自甘墮落、附庸逆流,而是以登高望遠、明智理性的態度記錄著屬于那一時代的真實情緒,武田的戰爭反思便由此一發而不可收。
(二)戰爭反思的要義
從1937年10月武田泰淳來到中國戰場,直到1939年9月退伍回國前后,他陸續發表《土民的表情》《寄給北京諸位的詩》《關于支那文化的信》《杭州的春》《我在中國的思考》等若干篇反思戰爭的文章。
1938年11月,武田泰淳《土民的表情》一文發表,其中寫道:“即使我們表情極端,中國土民的內心卻似乎毫不動搖,這樣的人我見過很多……也許政治家們真能隨意驅使數千的苦力,我無話可說。但是,夢想著綻放東方及其文明人類知性之花的人,卻不得不具備從一個農民的表情中讀解出人類表情深處情愛的能力……這些土民或許不會入大多數中國研究者和旅行家們的法眼吧。但是,正是他們構筑了成為亞洲及東方文化源流之一的中國,而不是日本的漢學家們和說著高雅的北京話而喋喋不休于古籍新發現的兩三個學者之流。”[5](p58)仰賴中華農耕文明的光澤成長,一直是古代日本的宿命。這種情形到了近代則出現根本性的變化。當崇拜西方成為日本民族的新選擇之時,對中國文化的蔑視甚至成為日本知識界的一種潮流。福澤諭吉的《文明論概略》和中江兆民的《三醉人經綸問答》,都明確表現出對中國的蔑視,甚至露骨地向日本統治階級、知識分子和民眾傳達覬覦中國之意。在文學領域,戰前的許多日本文人,如夏目漱石、佐藤春夫、谷崎潤一郎和芥川龍之介等近代文壇的大家都到過中國,他們對中國的記錄和描述與前人如出一轍,盡顯蔑視和抹黑中國之能事,無法逃脫為日本帝國主義野心去推波助瀾的痼疾與窠臼。武田泰淳作為后輩學人,在戰爭期間,對中國和中國文化的體驗方式、思考方式和思考結論顯然與他的前輩們不盡一致。武田看到的是,中國“土民”面對侵略者內心的毫不動搖,構筑亞洲及東方文化源流之強大能量,日本漢學家的附庸風雅和怠惰可笑。武田的反戰意識的萌生并非僅限于此,1938年9月,武田泰淳在安徽省某鎮創作一首題為《寄給北京諸位的詩》的作品,并轉寄給當時東京的文學會主編松枝茂夫。這首詩和《土民的表情》發表在同期的《中國文學月報》上。這首詩是武田在認同自己侵略者的身份為前提,以呼吁同人覺醒的口吻寫給北京同人們的。當時正在北京城內留學、工作的同人有竹內好、千田九一、實藤惠秀和飯塚朗。武田在詩中寫道:“聚集在北京的諸位啊。我知道,自己在中原說你們的壞話傳不到你們的耳朵。你們這些家伙一旦齊聚一處,就沒有什么話要一吐為快嗎……爾等憧憬之北京的秋,澄澈的只是天空而已吧?黃塵不是污濁了眼睛嗎?滿眼沙塵還談什么幸福啊……北京的家伙們,拿出你們的心肝吧!就算它比豬腸廉價,落在地上染了灰,愚蠢的淚又撲簌其上……”[5](p61)由此可見,土民表情的解讀,中國文化的再認識,中國研究者的自我反省,侵略者身份的認同感等等,已然成就武田認識中國、反省戰爭的堅實基盤。詩中不僅包含諷刺北京同人默認戰爭的隱喻、對戰爭無動于衷的思想控訴,還蘊含武田同情中國、反對戰爭的人道主義精神。我們不得不承認,武田泰淳作為戰場上的日本文人,能以登高望遠之態,俯視今昔的睿智,理性看待客觀世界的態度彌足珍貴。
在1940年1月發表在《中國文學月報》上的《關于支那文化的信》中,武田泰淳曾經寫道:“我最先目睹的是布滿彈痕、殘垣斷壁的支那的房屋,還有腐爛后一言不發的支那人的尸體。學校里倒著的課桌上還有布滿泥塵的教科書,圖書館里成套的《新青年》、《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等雜志已被雨水打濕。此情此景讓我仿佛看到了文化的寂寥和毀滅的無常。”[5](p88)戰爭的殘酷無情地嘲弄武田的最初志向、人文精神和日常的生活感受。在后來武田的隨筆、對談集中,日軍殘忍殺戮平民后的慘狀,砍下中國無辜少年士兵頭顱的情景屢屢出現。可以看出,日本軍國主義當局發動的侵華戰爭,無時無刻不在煎熬著這位輜重補充兵。侵略戰爭不僅傷害人、破壞器物以致文化,還扭曲青年武田的真情、善意和青春熱望,褻瀆一個僧人士兵的博愛、慈悲和信念。
武田泰淳絕不是戰爭的擁戴者,這是被他的文學歷程所證實的真實。文化是一種復雜的存在,以任何簡單的結論面對這種復雜都是行不通的。思想來自體驗,體驗不變,思想絕不會變。武田的戰爭反省意識源于參戰的真實感受,不但與北京的竹內好并不相同,而且他的戰爭認識、中國認識也完全不屬于文壇前輩營壘中的存在。在這個意義上,武田這一時期留下的相關文字顯然是與時代潮流分道揚鑣的。武田的青春期是一個有良知日本知識分子身不由己的時代。1925年日本軍國主義政府制定“治安維持法”,1928年創建“特別高等警察”,在法律和制度上,對言論、行動、集會、結社的自由實行的鎮壓古今罕見。盡管如此,在這樣的時代逆流中,戰場上的武田,并沒有完全被軍國主義國家機器裹挾而言聽計從,他在夾縫中求生存,留下頗具深意的理性思維的文字。當日本國內一些知識分子為法西斯政權所策劃的戰爭表現出狂熱情緒之時,武田能夠在戰場上去識破該戰爭是最不符合正義和人道的,是同歷史潮流背道而馳之暴行的認識,足以說明武田已然具備超越國別的價值觀念。武田從軍期間反戰思想的生成,早已不單純是頭腦里的問題,而是已經滲透到他的生活、情緒和文字之中。
更加可貴并值得注意的是,戰爭中便開始研讀《史記》和《報任安書》的武田泰淳,不但真真切切地注視著中國和戰爭,而且在思想上,破除種種束縛和壁壘理性地記錄細致的觀察和真實的情緒。這些行軍期間的報告文學,也為1943年發表的反戰思想濃烈的評傳《司馬遷》積累不可或缺的養料和素材。一個戰爭中的日本士兵,能以俯視今昔的姿態,“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氣度,去抗拒日本軍國主義時代甚囂塵上的皇國史觀,感知戰爭的非正義性,同情被害國的悲慘遭遇,他的境界對于過去與未來都是值得后人去研究和探討的。武田反戰思想在文學領域的控訴,不僅駁斥近代以來日本文人膚淺、錯誤、扭曲的中國觀,還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侵略者殺戮平民的殘酷事實。盡管在戰爭年代武田的反戰思想只是星星之火,難以形成燎原之勢,但其特定的思想和文學敘述及至今天隨時皆可有力還擊篡改歷史、扭曲侵略戰爭性質的無恥之徒,作為警示文明人類的良好佐證和有力依據。僅從這一點來說,無論是輜重補充兵的武田,還是“第一戰后派”小說家的武田,他的反戰文學意識不僅先于同輩一步,甚至在整個日本近代文學史上同樣意義非凡。
三、武田反戰思想的現實價值
無論是回望政治潮流的桎梏,還是思考戰爭現實的鉗制,寄望于戰爭期間一個戰場上有良知的日本知識分子,為反對戰爭去振臂高呼、搖旗吶喊是不現實的。這是一個為侵華戰爭歷史所證明、毋庸置疑的事實。但是,理性發掘武田反戰思想的萌動,剖析其進步意義和局限性,以此駁斥日本“反戰文學”空白的論斷,重申日本軍國主義侵略戰爭罪責將意義重大。
值得注意的是,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戰爭爆發,1942年5月,日本內閣情報局糾集約4 000名文人組織成立“日本文學報國會”。“日本文學報國會”的宗旨是以文學去鼓動侵略者的戰斗意志,號召創作“國策文學”。隨著戰爭的惡性膨脹,日本文學發展脫榫、人性失守并自然解體。在此期間,武田泰淳的反戰思緒并沒有因退伍回國而宣告結束,他反戰思想的萌動與生成明顯是一個“一以貫之”的過程。當志賀直哉、永井荷風、川端康成、谷崎潤一郎等少數文人拒絕配合戰爭、堅守自己文學世界、消極抵抗現實之際,武田已經開始著手于第一本轟動文壇評傳《司馬遷》的創作。評傳《司馬遷》開手于太平洋戰爭爆發的1941年12月,1943年3月付梓印刷。武田泰淳依托司馬遷的命運和《史記》世界里的歷史空間架構,充分強調對人的重視,以及人在歷史中的象征意義和文化承載功能,完全是對忽視個人存在的“玉碎”圣戰精神的挑戰;他對歷史“萬物流轉”、多元變化、相互作用的認知,是對二戰期間日本“萬世一系”皇國史觀和日本中心論的否定。武田泰淳不僅借助于《史記》中,不同政治立場文人的褒貶評價,構建起心目中理想文人的形象,還為狂熱的軍國主義崇拜者、被蒙蔽的無知民眾注射一劑鎮靜劑。“當時完全沒有言論自由。至少在太平洋戰爭階段,用任何手段公然表明反對戰爭和法西斯政權,原本就是不可能的,甚至可以說是毫無意義的”[7](p138)。日本文人對于戰爭的態度大致分化成三種傾向,即隱秘反戰、避而不談和文學報國。就武田這一時期的報告文學、隨筆、詩歌、評傳而言,無論是寫作切入點的推敲,還是隱喻手法的運用,無不是面對生活的一種無奈選擇。川端康成在文學報國甚囂塵上的民族氣氛里去寫《雪國》,谷崎潤一郎創作《細雪》、潛心打造一個個女性形象,實際上都是趨吉避兇、有意為之的產物。1938年前后,日本軍國主義當局策動大批文人作為“筆部隊”開赴戰場,借助他們美化戰爭、鼓吹圣戰,極盡“報國文學”之能事,盡顯走狗文人的孱弱與丑態。諸如林房雄《上海戰線》、火野葦平《麥與士兵》、上田廣《黃塵》、丹羽文雄《未歸來的中隊》等小說無不如此。有鑒于此,武田在《混沌與創造》中說:“在《史記》作者司馬遷那樣茍延殘喘的命運降臨在日本國民頭上之前,無論書寫何種體驗,都難以創作出像樣的小說。創作也不過是裝腔作勢罷了。當時,雖然也有不少有關中國的小說作品,但我決不認為它們在現實中起到了什么積極作用。我覺得,小說這種東西,畢竟還是應該在現實中發揮積極效應的。”[8](p139)武田的這種姿態和認識,顯然是對戰爭期間“避而不談”“文學報國”兩類文人的鞭笞和影射。因此,在武田反戰思考的生成時期,無論是審視戰爭的角度、剖析軍國主義實質,還是揭露戰爭罪惡、抨擊知識分子丑態等實際行動上,無不顯示出一個熱愛中國、反對戰爭、有良知日本文人的應有姿態。盡管武田反戰發端的聲響是微弱的,但其戰爭反思的要義明確,意味深長,相比之下,他的行動是走在時代前列的。甚至可以說,武田沒有附庸潮流、為天皇的圣戰奉獻一切,他的反戰要義為其走向“第一戰后派”作家的道路奠定理論根基,為其堅決執行和不斷探索戰爭、關注中國、追究戰爭罪責提供有力的依據。
20世紀50年代,加藤周一在《日本文化的雜種性》一書中認為:“當戰爭責任成為問題的時候,曾積極協助戰爭的知識分子提出過‘1億人總懺悔的問題,這可以說盡管有一半正確,但另一半則是具有欺騙性。它有一半正確,是因為戰爭確確實實把整個國家都卷了進去,而知識分子恐怕只有當自己也被卷入其中的時候才開始切實感到同大眾的聯系。戰前,而且恐怕戰后也同樣,知識分子同大眾在精神上的鴻溝是很深的,只是通過戰爭才有了能夠對‘1億人這個詞伴有實感。但是,要把知識分子的責任推卸在一億國民身上,化為烏有,他們所考慮的則是一種欺騙。”[7](p137)很難說,這個戰后思想史上的大事件與武田泰淳毫無關系。眾所周知,日本知識分子戰時不敢反對戰爭,戰后卻百般抵賴,千方百計想把戰爭責任推卸給全體國民。武田泰淳與這個階層的弱點是并無干系的。“我心里清楚得很,自己沒有為中國做過一件好事,盡管中國人常對我說,并非如此……我認為,可以懲罰我的不是日本政府,而是中國人……無論是下地獄,還是登極樂,在最后的一瞬間,它都會從中國的方向朝我走來”[6](p187)。武田作為一生始終熱愛和關注中國的日本人,他的歸屬無須贅言,我們寄望其完全超越民族主義情緒,徹底站在戰爭受害者立場上,去思考問題是不現實的。野間宏和大岡升平,是在戰爭中期或末期才走向菲律賓戰場,從軍時間較短。作為日本文壇“戰后派”著名寫手,他們都是在戰后才開始反戰和揭露戰爭罪惡的文學控訴。但是,無論是野間的《陰暗的圖畫》《臉上的紅月亮》,還是大岡的《俘虜記》《野火》,無不流露出戰爭加害者自憐性的局限。相形之下,無論就武田的個人志趣、中國觀、戰場體驗而言,還是反省態度、文學走向、戰后活動的實際來看,武田泰淳在“第一戰后派”作家中可謂一個在反戰道路上無人出其右的典型。
戰后日本思想史界所倡導的“1億人總懺悔”,今天看來已經成為歷史的笑柄。它所留下的日本知識分子階層的孱弱和病態,不但在當時理所當然地受到批判,而且對今后這樣一個社會階層的走向同樣留下至關重要的警示。作為一介文人,武田能夠做到這一點,應該說他的境界已經不低了。縱觀武田的文學世界,他對自己曾是一名侵略者身份的認同,對中國人民的負罪感,既沒有因1950年“朝鮮戰爭”的爆發戛然而止,也沒有因“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實現而銷聲匿跡。
在當今的時代和世界,再次梳理武田反戰思想的生成,并以此為依據探索武田的戰爭觀、中國觀無疑是意義非凡的。戰爭與中國是武田泰淳文學世界中不可回避的歷史命題,沿著武田的人生軌跡、將其文學的內核層層剝開、發現其文學思想的反戰意識、中國熱望和佛教光彩,理應成為中日兩國學人和有識之士的時代課題。歷史是生存者的意識形態,任何時期、任何場合歪曲侵華戰爭性質,賣弄態度曖昧、推諉塞責、篡改教科書的伎倆皆可視為歷史的倒退、正義的背叛。當日本居心叵測的文人、政客一意孤行,為通過“新安保法案”叫囂乎東西、隳突乎南北的時候,他們更有必要靜下心來,深切體會文壇前輩武田泰淳文學的反戰思想。只有日本人以史為鑒、深刻反省,中日兩國的美好未來才有希望,只有日本人像武田一樣,拿出理性思考的勇氣,摒棄偏見,總結教訓,破除民族優越感的壁壘,正視戰爭歷史和現實中國,中日兩國的和平之樹才能長青,一衣帶水之友好方可長久。如果說,任何時代、任何地點反對戰爭、呼吁和平的文學形式,皆可框定在“反戰文學”的范疇里。那么,武田泰淳顯然是在有限的框架內盡其所能、切實反戰的先驅式人物。武田的反戰思想,不僅應該受到中國人的認可,更應該成為日本人反省戰爭的啟示錄。知識分子向來就是一個特殊的、復雜的社會階層,日本的也好,中國的也罷,多一點誠意少一點欺騙,多一點理性少一點偏見,尤其應該成為當代學人秉持之操守。
[參 考 文 獻]
[1][日]武田泰淳.滅亡について[M].東京:巖波書店,1992.
[2][日]藤原彰.日本近現代史:第3卷[M].北京:商務印書館,1983.
[3][日]中野好夫.現代作家[M].東京:巖波書店,1964.
[4][日]福澤諭吉.文明論概略 [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5.
[5][日]武田泰淳.わが中國抄[M].東京:普通社,1963.
[6][日]武田泰淳,堀田善衛.私はもう中國を語らない[M].東京:朝日新聞社,1973.
[7][日]加藤周一.日本文化的雜種性[M].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1.
[8][日]武田泰淳,佐佐木基一,開高健.混沌から創造へ[M].東京: 中央公論社,1976.
(作者系東北師范大學博士研究生,浙江越秀外國語學院講師)
[責任編輯 吳井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