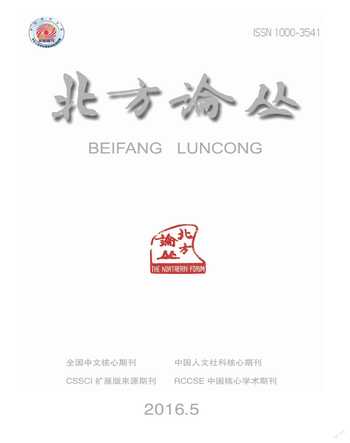英國議會圈地中圈地委員工作的公正性探究
倪正春

[摘 要]英國議會圈地運動中,圈地委員的工作是否公正,對于理解圈地運動的運行機制是一個關鍵問題。圈地委員的任命基于一定的私人意愿,但是,圈地委員的專業化一定程度上抵消了私人意愿在任命圈地委員過程中的影響。圈地委員的工作機制體現出兩個特點:公開化和法制化,這兩種工作機制相當程度上抑制了圈地委員徇私舞弊的行為。圈地委員的職業化是隨著圈地運行機制的完備而出現的一種現象,圈地委員的職業化趨勢使私人利益在圈地委員工作過程中的影響進一步降低。
[關鍵詞]英國;議會圈地;圈地委員
[中圖分類號]K56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3541(2016)05-0098-06
Abstract: The fairness of the commissioners during Parliamentary Enclosure is a key point to understanding the mechanism of enclosure movement. The appointment of the commissioners was based on a certain degree of private will, but the professional of the commissioners partly offset the impact of private will on the appointment. The working mechanism of the commissioners reflects two characteristics: open and legalization, which inhibited the commissioners to engage in malpractices to an extent. The professionalism of the commissioners is a phenomenon that appears with the maturity of operating mechanism of the enclosure, the professional trend of the commissioners further reduce the impact of private interests in the working process of the commissioners.
Key words:England; parliamentary enclosure; commissioners; fairness; professionalism
發生于18—19世紀的英國議會圈地是一次大規模的土地權利重新配置過程。議會圈地時期圈圍土地面積占英格蘭總面積的209% [1](p.32),影響范圍幾乎輻射到整個英格蘭,圈地之后農民的土地私人產權基本得到確立。在圈地過程中,圈地委員(Enclosure Commissioners)是圈地法案的具體執行者,全權負責圈地的各項事宜,這個群體的工作對農民土地權利的確認和補償至關重要。
國內學術界對圈地委員還沒有專門研究,國外對圈地委員的研究自18世紀議會圈地時期就已經肇始,成果比較豐富。一些學者認為,圈地委員代表圈地發起者的利益,工作缺乏公正性。例如,威廉·哈斯巴赫(Wilhelm Hasbach)說:“圈地委員是和圈地利益攸關的人所任命的律師。” [2](p.62)哈蒙德夫婦認為,圈地委員肯定會服務于那些任命他們并在未來能給他們提供類似工作的人的利益 [3] 。另外一些學者認為,圈地委員的工作基本上是公正的。例如,岡納(ECKGonner)認為:“盡管莊園領主和大所有者的影響決定圈地委員的任命,被選中的圈地委員通常都是富有經驗、品格正直的人”,并且“劃分和分配土地的工作總體上是認真公正的。” [4](pp. 94-95)科特勒(WHCurtler)認為,盡管存在一些謬誤和偏頗,沒有理由認為圈地委員的行為存在明顯的不公,圈地委員的工作總體上是誠實、公正的 [5](p.159) 。
圈地委員的工作是否公正是議會圈地中一個關鍵問題,這一問題的解決對于理解整個議會圈地運動的運行機制,議會圈地對農民土地權利的影響等問題都至關重要。但到目前為止,西方學者并沒有就這一問題達成一致意見。筆者擬通過考察圈地委員所代表的利益,圈地委員所維護的利益,圈地委員的職業發展趨勢等問題,廓清圈地委員的工作是否公正這一問題。本文依據的資料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是議會圈地期間保存下來的圈地委員備忘錄(minute books)、圈地判定書(Enclosure Awards)等原始資料;第二部分是英國歷史學者的有關專著與論文。
一、 圈地委員的任命——代表誰的利益
圈地委員是議會圈地法案在圈地教區的具體執行者,執行一個教區圈地法案的圈地委員數量不等,所有圈地委員組成一個圈地委員會,圈地教區的所有圈地事宜都由這個圈地委員會全權負責。圈地委員的權利有多大呢?圈地委員是“大約從1745年至1845年頒布一般圈地法令期間,被法律賦予絕對權利去圈圍和重新分配公地和敞田的人”[6]。圈地委員是由誰任命的呢?一般來說,圈地倡議者向議會遞交的圈地請愿書上就已經確定了圈地委員的人選,圈地請愿書在議會獲得批準成為圈地法案之后,圈地委員的任命也就正式得到法律認可。也就是說,圈地委員是由圈地倡議者任命的。那圈地委員是否完全代表圈地倡議者的利益呢?
圈地倡議者確實有權決定圈地委員的人選,甚至按照自己的意愿反復任命同一圈地委員。例如,在牛津郡1787—1814年進行的圈地中,馬德林·科利奇(Magdalen College)在圈地倡議者的名單上出現了三次,其中兩次馬德林任命羅伯特·韋斯頓(Robert Weston)為圈地委員。伊頓·科利奇(Eton College)先后五次倡議進行圈地,其中四次都選擇托馬斯·伊格爾(Thomas Eagle)作為圈地委員以維護他的利益。達什伍德(Dashwood)家庭兩次都任命了亨利·奧古斯塔斯·比德曼(Henry Augustus Biederman);埃克塞特·科利奇(Exeter College)兩次都選擇了約翰·戴維斯(John Davis)為圈地委員;塞西爾·畢曉普爵士(Sir Cecil Bisshop)兩次都任命了托馬斯·霍普克拉夫特(Thomas Hopcraft)。馬格斯菲特伯爵(Earl of Macclesfield)共發起三次圈地,其中兩次任命了理查德·懷亞特(Richard Wyatt)為圈地委員。牛津主教發起的五次圈地中,都任命約翰·霍斯曼牧師(Rev. John Horseman)為圈地委員 [7] 。上述事例說明,圈地倡議者在任命圈地委員方面有自己的偏好,而不是任意為之。圈地倡議者反復地任命同一人為圈地委員這一事實表明,這些圈地委員能代表他們的利益。圈地倡議者和他們中意的圈地委員之間有什么樣的私人關系呢?目前還缺乏關于這兩者之間關系的資料,但有一點卻可以得到肯定,圈地倡議者任命圈地委員的時候不是基于私人關系,而是更多地考慮自己的土地權利是否能得到有效地維護。隨著議會圈地的進行,不同的圈地委員,似乎已經專門代表不同種類土地所有者的利益。也就是說,在他們中間已經出現了某種程度的專業化。一些圈地委員專注于維護莊園領主的利益,一些圈地委員專注于各種形式的什一稅所有者,一些專門維護其他普通土地所有者的利益。
圈地委員的專業化趨勢是一個逐步形成的過程。一個圈地委員在一次圈地中給他的任命者提供了很好的服務,就有可能在另一次圈地中服務于同樣的利益。例如,亨利·狄克遜(Henry Dixon)參加了五個圈地委員會,其中四次代表了“所有者”的利益。塞繆爾·德魯斯(Samuel Druce)也服務于五個圈地委員會,其中四次代表“所有者”和“其他所有者”的利益。服務于7個圈地委員會的托馬斯·霍普克拉夫特(Thomas Hopcraft),似乎專門代表莊園利益,因為他曾經在4個圈地委員會中是如此。隨著圈地的進行,圈地委員的專業化也逐步增強。米德爾塞克斯郡胡克·諾頓的史蒂芬·戈德森(Stephen Godson of Hook Norton)和黑爾菲爾德的約翰·特朗普爾(John Trumper of Harefield)僅僅擔任了兩次圈地委員,每次擔任圈地委員都代表莊園利益(兩個不同的領主)。托馬斯·詹姆斯·泰瑟姆 (Thomas James Tatham)四次都代表除了莊園領主和什一稅所有者的“其他人”的利益。約翰·霍斯曼牧師(Rev. John Horseman)服務于9個圈地委員會,每次都代表教區牧師,代牧等教會人士的利益[7]。圈地委員的專業化說明圈地倡議者任命圈地委員時,更在乎圈地委員的專業素養,以及自己的土地權利是否能得到維護。既然圈地倡議者任命圈地委員的初衷是圈地委員是否能代表自己的利益,那圈地倡議者的利益都能得到代表嗎?
一般來說,圈地委員會通常由三名成員組成:一名代表莊園領主,一名代表什一稅所有者,一名代表其他的土地所有者。也就是說,圈地教區中大土地所有者的利益都會有所代表。但在圈地實踐中并不一定如此。在牛津郡早期的圈地法案中,圈地委員會通常包括五或六個人。該郡最初20個圈地法案任命的圈地委員數量平均超過4個。但在最后的20個法案中,平均每個法案的圈地委員數量是12個,這段時期沒有法案任命超過2個圈地委員。也就是說,在牛津郡由三個成員組成的圈地委員會不是普遍情況。后期議會圈地的費用高昂招致社會廣泛的批判,結果是任命兩個圈地委員甚至僅僅一個圈地委員成為普遍現象。甚至一些地區的圈地法案直接由圈地涉及到的相關群體(party)執行,根本沒有任命任何圈地委員。這種情況說明圈地教區中的各種利益群體在圈地過程中不一定能得到代表。
綜上,圈地倡議者在任命圈地委員時,不能完全排除私人因素,但圈地倡議者更多的是考慮圈地委員的專業性素養,以及自己的土地權利是否能得到代表。另外,某些圈地中圈地委員數量的不均衡導致一些圈地倡議者的利益無法得到有效代表。
二、 圈地委員的工作——維護誰的利益
圈地委員是議會圈地法案的具體執行者,自始至終全權負責圈地地區的各項圈地事宜。圈地委員的工作過程是否公開公正?圈地委員的工作維護了誰的利益呢?圈地委員通過召開圈地會議逐步完成各項圈地事宜。圈地委員會成立以后,首先要在當地報紙上刊登出被任命的公告,并告訴公眾其第一次會議召開的時間地點,該公告也會被粘貼在當地教堂的大門上。自就職之日起,圈地事宜全部處于圈地委員會的指導之下。在第一次會議上,圈地委員們宣誓就職并對書記員(Clerk)和土地測量員(Surveyor)進行任命。土地測量員掌管土地的測量和設計,以測量數據為依據,經過仔細的斟酌,對現存的敞田和公共權利進行劃分,規劃出新的份地(Allotment)。同時,土地測量員還對公路、步行道、排水溝,以及圍田未來的管理和養護進行設計規劃。書記員對圈地委員會的仲裁決定進行詳盡的紀錄,對土地的分配比率進行計算。在接下來的圈地會議上,圈地委員會要確定教區居民的土地權利,用份地等形式補償土地權利,規劃教區道路、排水溝等公用設施。最后,圈地委員要制定圈地判定書,所有圈地事項要用書面的形式記錄下來。
綜合考察圈地判定書及圈地委員備忘錄,可以發現圈地委員的工作過程體現出兩個機制:公開化和法制化。
公開化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圈地委員在進行圈地期間召開的所有會議都會公布時間地點,圈地過程中各個階段的決議也要公開張貼。圈地委員會召開會議的地點一般選擇在圈地教區的酒館(inn)中,因為“這是合適的會議地點,地理位置居中,態度中立,并且能為到此開會的圈地委員提供食宿”[8]。例如,萊斯特郡紐伯德·威登(Newbold Verdon)和紐伯德·希思(Newbold Heath)教區的圈地委員會召開會議的地點是博斯沃思的公牛頭領酒館,紐伯德的喬治和龍酒館,拉夫伯勒的錨酒館和萊斯特的撒拉遜首領酒館,以及三王冠酒館。按法律規定,初步形成的議案,并討論議案的會議通知,議會審議通過的法案,圈地委員的任命,圈地委員開會的通知,直到最后經過圈地委員討論和測量而通過的圈地判定書等都要公布。公布的方式一般有兩種:一種是張貼在當地教堂的門上;另一種是在當地的報紙上登出公告啟事。例如,北安普頓郡韋斯特·哈登村的圈地者就非常樂于發布公告,方式是定期貼到教堂的門上或是借助當地的報紙——《北安普頓使者》(Northampton Mercury)[9](p.192)。在金斯頓·德夫里爾的圈地中,圈地委員首次開會的通知被張貼在教區教堂的門上,同時在當地的主要報紙,《索爾茲伯里和溫切斯特雜志》(Salisbury and Winchester Journal)上登出了公告 [10](p. 72)。
二是圈地事項的公眾參與。圈地教區的居民,無論是大土地所有者、小土地所有者,還是無地的農民,都能參與到圈地的過程之中。不僅教區中所有居民要把自己的土地所有狀況以及公共權利狀況上報給圈地委員會,任何利益攸關者都可以參與圈地委員的會議。如果教區居民對所有者的權利要求或是份地和道路選址持反對意見的話,圈地委員有責任聽取這些反對意見,同時要求所有者呈遞支持自己權利要求的證據。圈地委員會基于反對意見和支持權利要求的證據,做出最后的判決。議會圈地期間保存下來的圈地委員備忘錄是雙方之間商討的證明,從這些備忘錄中可以發現圈地教區的居民參與圈地事項等情況。
白金漢郡韋斯頓·特維爾(Weston Turville)教區的圈地委員在議會圈地期間召開了16次會議,這16次會議的備忘錄有幸保存至今,因此,可以通過這些珍貴史料,解教區居民參與圈地過程,以及圈地委員和教區居民之間的互動。圈地委員于1798年6月20日召開了第一次會議,在這次會議上做出決議:“圈地委員的書記員分別寫信給所有者,要求他們在圈地委員將于7月18日星期三召開的會議上,以書面形式呈遞他們各自對于可耕地、草地或牧場的包括估算面積的權利要求,各自的馬、奶牛和羊、公地的數量,以及莊園和其他權利。” [11]圈地教區的所有者在圈地委員召開第二次會議時,把他們的權利要求提交給圈地委員會。圈地教區的居民可以對這些權利要求的合理性提出質疑。1798年8月20日,在喬治·艾爾斯伯里酒館(George Inn Aylesbury)召開的第三次會議發布了這樣一個通知:“如果任何人或群體對上述提到的任何權利要求有任何反對意見的話,他們可以在下次會議召開的時候,通過書面的形式把他們的要求提交給圈地委員。”[11] 1798年9月24日,在文多弗的紅獅酒館(Red Lion Inn Wendover)召開的第四次會上,圈地委員收到了大量教區居民對權利要求的反對意見。1798年10月18日,在喬治·艾爾斯伯里酒館召開的第五次會議上,圈地委員依照上次會議的決議開會,開始聽取那些提出的權利要求遭到反對意見的所有者,對自己權利要求的證明和辯解。圈地委員依據這些提供的證據判斷其權利要求是否正當合理。
萊斯特郡紐伯德·威登和紐伯德·希思教區的圈地委員從1810年7月至1811年8月,召開了25次圈地會議,這些會議的記錄也表明,圈地教區的居民能參與各項圈地事宜。53名圈地教區居民向圈地委員會呈遞了土地權利的聲明,其中14項受到了其他教區居民的反駁[8]。圈地教區居民也參與了教區道路的重新劃定。例如,一條圈地會議的備忘錄如是記載:“我們圈地委員因此發布通告,1810年10月27日星期六我們將于萊斯特的三王冠酒館召開會議,任何可能因為上述道路劃定或是因為忽略了任何其他公共運輸道路的劃定而受到傷害或是侵害的人,都可以參加此次會議,任何反對意見都可以當場按照喬治三世的第41號法令進行判決。”[8]
議會圈地程序的公開化是圈地委員和圈地教區所有居民的共識。正如英國農業史學家明格所說,盡管研究過這個題目的人不會認為法案的制定完全不受個人的壓力,或重新分配的結果對所有利益都完全公平,不論大小。但這個過程確實提供了一些有限的保障,而且確實表現出相當程度的公開[10](p. 58)。議會圈地不僅是一個公開化的過程,也是一個法制化的過程,圈地委員工作過程的法制化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首先,圈地委員按照法定程序工作;其次,圈地委員按照法定的土地分配標準對土地所有者和公權持有者的土地權利進行份地補償。
圈地委員工作的每一個步驟都按照圈地法案中規定的法定程序進行,其職權不能超出法案的授權范圍。有時候,因為一個法案的授權范圍太有限,為了工作的順利進行他們不得不申請第二個法案。例如,圈地法案規定使用籬笆作為地塊之間的分界,但如果籬笆被鬧事者破壞的話,圈地委員擬使用壕溝作為分界,這時他就不得不請求議會批準第二個圈地法案。又如,通常的慣例是,圈地委員賣掉部分荒地來支付圈地的費用,但如果土地所有者覺得保留所有的荒地更適宜的話,圈地委員就要申請第二個法案,授權他保留荒地[10](p. 81)。圈地教區中,所有土地所有者和公權持有者的土地權利,都能得到相應的份地補償。圈地委員在進行份地補償的過程中,也要按照法律規定進行,因為圈地法案中對各種土地所有者的土地分配規定了標準。例如,萊斯特郡紐伯德教區的圈地法案是這樣規定土地分配標準的:教區土地的1/16分配給領主,以補償他的領主權利。紐伯德教區的牧師得到敞田的1/5,荒地的1/9,以補償他作為什一稅所有者的土地權利[8]。其他教區土地所有者或公權所有者的土地權利,也要得到相應補償。例如,在牛津郡的黑丁頓教區圈地中,圈地判定書記載了圈地委員對教區居民的土地權利進行補償的情況。無論是自由持有地,還是公簿持有地,甚至租借持有地,都能得到相應的份地補償。圈地法案對圈地委員的限制以及圈地委員自身按照法律行事的愿望保證了議會圈地大體上是一個法制化的過程。
綜上所述,圈地委員在執行圈地法案的過程中秉持公開化的原則,并且按照法定程序工作。圈地委員在重新配置土地時,也基本按照圈地法案的規定進行,對教區居民的土地權利進行了相應補償。公開化和法制化雖然不能保證徹底的公正,但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圈地委員徇私舞弊的行為。當時大量的圈地記錄也表明,圈地委員是多么“小心而仔細”地履行他的職責。圈地委員的工作既維護了圈地倡議者的利益,也一定程度上維護了其他土地所有者的利益。
三、 圈地委員的職業化
議會圈地過程中出現了一個引人注目的現象,即圈地委員的職業化。18世紀30—60年代是議會圈地的早期階段,這一階段的圈地委員會規模非常大,并且通常由地方人士組成。18世紀60年代之后,隨著圈地進程的加快,人們越來越關注圈地委員會的花費問題,小規模的圈地委員會成為普遍現象,并且出現了以擔任圈地委員為職業的人。
在議會圈地過程中,某些圈地委員承擔圈地工作的頻率已經遠遠超出其他圈地委員,這一部分圈地委員逐漸成為職業圈地委員。弗蘭西斯·伯頓(Francis Burton)被認為是最早的職業圈地委員,他在1777年去世之前服務于至少64次圈地中,去世的時候仍然同時服務于幾個圈地委員會中[12]。因為頻繁地承擔圈地工作,職業圈地委員工作異常繁忙。亞瑟·艾略特(Arthur Elliot)被稱為“職業圈地委員”,他的日記表明,1797—1798年間,他花費了105天召開正式的圈地會議,14天從事協商工作;1795年中的8周,用來協商8個教區的圈地事宜,接下來的一年里,為12個教區的圈地召開了117次會議[6]。
圈地委員的職業化趨勢基于圈地委員需要具有的一定的專業技能,因為他們要完成許多專業性比較強的任務,而這些工作不是任何人都能勝任的。首先,圈地委員要具備管理和協調能力;其次,還要具備評估教區居民的土地權利要求、劃分道路和分配份地方面的專業技能和實踐經驗。更重要的是,委員們在圈地期間要組織村莊的經濟事務,一定意義上成為領地法庭和教區委員會,肩負管理村莊土地的職責,命令老休耕地的犁耕,調節殘茬的共同使用權。
歸納起來,圈地委員所需的專業技能涉及兩個方面:土地測量方面的技能和土地耕作方面的知識。因此,具備土地測量技能的土地測量員和具備土地耕作經驗的約曼,成為圈地委員的主要來源。事實的確如此,到18世紀90年代中期,圈地委員會越來越多地被土地代理人和測量員所主導。一些著名圈地委員都在之前當過一段時間的測量員。白金漢郡佛斯科特的約翰·費洛斯(John Fellows of Foscott)是這個郡中最繁忙的圈地委員,1788—1825年之間從事了29次圈地,但在他擔任圈地委員之前有一段非常長的學徒期,1773—1781年間,在11次圈地中擔任測量員。諾森伯蘭郡布拉克利的威廉·科利森(William Collisson of Brackley)是另外一個活躍的圈地委員,也擔任了很長時間的測量員。約瑟夫·伯納姆(Joseph Burnham)是艾爾斯伯里的一名律師,在18世紀90年代,擔任了三次圈地委員,但他在擔任圈地委員之前,曾在幾個圈地委員會中擔任律師和書記員,已經積累了豐富的經驗[12]。也有為數不少的圈地委員出身于約曼。白金漢郡的約翰·費洛斯在成為一名土地測量專家之前是一名約曼,他的“約曼出身”表明他與土地有更加直接的聯系,具有耕作土地的實踐經驗。從1807年開始,文獻中把他稱為一名白金漢的紳士,與此同時,他的名字也從土地稅記錄中消失,這表明他已經從直接經營土地的約曼成為一名職業土地代理人和測量員。英國農業經濟學家阿瑟·揚在參觀布洛克瑟姆(Bloxham)時,對一位名叫戴維斯的農場主印象深刻,認為他是一位實踐經驗豐富的農場主,具有圈地委員所需的大量經驗,“同時在26個圈地委員會工作” [12] 。
職業圈地委員的工作區域遠遠超出其本身所在的地區。例如,在白金漢郡,1790年之前的早期圈地一般任命當地人擔任圈地委員,隨著圈地的進行,以及職業圈地委員的出現,圈地倡議者開始尋找本郡以外的圈地委員,1790—1819年間,僅僅1/5的圈地委員來自本郡 [12]。下面是幾個著名的職業圈地委員,他們活動的區域已遠遠超出本身所在的郡。約翰·張伯倫(John Chamberlain)在沃里克郡,伍斯特郡和斯塔福德郡三個郡中擔任了12次圈地委員,在牛津郡中擔任了8次,在白金漢郡中至少擔任了1次。[6]北安普敦郡的弗蘭西斯·伯頓,1762—1777年,在白金漢郡擔任了15次圈地委員,在牛津郡擔任了28次,在威爾特郡擔任了1次,在伯克郡擔任了5次,在赫特福德郡擔任了1次,在北安普敦郡擔任了14次[12]。弗蘭西斯·伯頓在外郡擔任圈地委員的次數已經遠遠超過本郡。牛津郡班伯里附近的約翰·戴維斯的圈地活動更加引人注目。18世紀90年代到19世紀20年代,他在英格蘭南部的許多郡工作。在白金漢郡,戴維斯是13個圈地委員會的成員,圈圍起1958萬英畝土地;在伯克郡圈圍了529萬英畝土地(32次擔任圈地委員,3次擔任仲裁人);在牛津郡圈圍了516萬英畝(34次擔任圈地委員);在格洛斯特郡圈圍2237萬英畝(6次擔任圈地委員);在威爾特郡圈圍1309萬英畝(4次擔任圈地委員,3次擔任仲裁員);在北安普頓郡圈圍1148萬英畝(7次擔任圈地委員);在貝德福德郡圈圍8 920英畝(4次擔任圈地委員);在萊斯特郡圈圍7 345英畝(5次擔任圈地委員),在漢普郡圈圍2 380英畝(擔任圈地委員2次)。約翰·戴維斯擔任圈地委員圈圍的土地總面積達到18075萬英畝,參加了113個圈地委員會 [12] 。約翰·戴維斯參與的113次圈地中,只有34次是位于他所在的牛津郡,比例不足1/3。圈地委員工作范圍的擴展某種程度上規避了圈地委員和本地土地所有者的私人關系,杜絕了圈地委員為本郡的親屬或朋友謀取利益的可能性。
隨著圈地委員職業化趨勢的發展,一些圈地委員還組成團隊來進行圈地工作。例如,在劍橋郡,黑爾(Hare)和麥斯威爾(Maxwell)在3次圈地中一起工作;特拉斯洛夫(Truslove)和康絲坦斯(Custance)在8次圈地中一起工作;韋奇(Wedge)和康絲坦斯在5次圈地中一起工作;索普(Thorpe)和康絲坦斯在3次圈地中一起工作[6]。 1790—1819年間,白金漢郡圈地史上最活躍的幾十年中,數量相對比較小的圈地委員被任命。某些圈地委員的名字反復出現在圈地判定書中,約翰·費洛斯,威廉·科利森,約翰·戴維斯,理查德·戴維斯和托馬斯·霍普克拉夫特出現在79個圈地委員會中。這些圈地委員也往往組成團隊進行圈地工作。例如,托馬斯·霍普克拉夫特和約翰·戴維斯在一起工作了四次,威廉·科利森和約翰·費洛斯在一起工作了六次[12]。團隊工作說明圈地倡議者按照自己的意愿任命某位圈地委員的情況更加少見。
在議會圈地過程中,某些地方甚至成為圈地委員和測量員的專門產地,某些家族成為專門培養圈地委員和測量員的家族,圈地委員成為一種專業化特征更明顯的職業。例如,北安普敦郡的一個小鎮布拉克利出現了一批圈地委員和測量員:包括韋斯頓(Westons)家族的測量員,羅素(Russells)家族的測量員和科利森(Collissons)家族的圈地委員,以及一個名叫詹姆斯·科靈里奇(James Collingridge)的測量員,他18世紀60—70年代期間,在該郡擔任了五次的測量員。這個北安普敦郡小鎮出產圈地委員和測量員并不僅僅在本郡工作。例如,1760—1820年間,白金漢郡的88個圈地委員會中,圈地委員和測量員中的一個來自于布拉克利,或者兩個都來自于布拉克利的圈地委員會至少有52個[12]。除此之外,布拉克利出身的圈地委員還大量的在其他郡中從事許多相關工作。
圈地委員的職業化表明圈地委員和圈地倡議者之間基本上排除了私人關系,已經接近于律師和當事人之間代理與被代理的關系。圈地委員所要代理的土地權利不僅包括圈地倡議者的土地權利,也包括圈地教區其他土地所有者的土地權利。
綜上所述,英國議會圈地中圈地委員的公正性問題可以通過如下幾點加以說明:首先,圈地委員的任命不排除私人因素,在議會圈地早期尤其如此,但圈地委員的專業化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個人意愿在任命圈地委員過程中的影響。其次,圈地委員的工作過程基本上公開,按照法定程序執行圈地法案。圈地過程的公開化和法制化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圈地委員在執行圈地法案過程中的徇私舞弊行為。最后,圈地委員的職業化趨勢使私人利益在圈地委員工作過程中的影響進一步降低。職業圈地委員的出現意味著圈地委員工作已經基本上秉持公正性的原則。
[參 考 文 獻]
[1]Turner, Michael, English Parliamentary Enclosure: Its Historical Geography and Economic History[M]. Folkestone: Dawson·Archon Books, 1980.
[2]Hasbach, W. History of the English agricultural labourer[M]. London: King & Son, 1908.
[3]Hammond, J. L. & Hammond, B. The village labourer[M]. London; NewYork: Longman, 1978.
[4]Gonner, E. C. K. Common land and Enclosure[M]. London: Macmillan and Co., Limited, 1912.
[5]Curtler, W. H. R. The Enclosure and Redistribution of Our Land[M], Oxford: Clarendon press,1920.
[6]Beresford, M.W. Commissioners of Enclosure[J],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1946, 16 ( 2).
[7]Tate, W. E. Oxfordshire Enclosure Commissioners, 1737-1856[J], 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1951, 23 (2).
[8]Beresford, M. W. The Minute Book of a Leicestershire Enclosure[J], Transactions of the Leicestershire Archaeological Society, 1947, 23.
[9]Neeson, J. M. Commoners: common right, enclosure and social change in England, 1700-1820[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
[10]Mingay, G. E. Parliamentary Enclosure in England: An Introduction to its Causes, Incidence and Impact 1750—1850[M], New York: Addison Wesley Longman.
[11]Shigetomi, Kimio, Enclosure Commissioners Minute Book: West Turville in the County of Buckingham[J], [日]愛媛經濟論集,1989, 9(1).
[12]Turner, Michael, Enclosure Commissioners and Bucking- hamshire Parliamentary Enclosure [J], Agricultural History Review, 1977, 25 (2).
(作者系南京師范大學講師,歷史學博士)
[責任編輯 張曉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