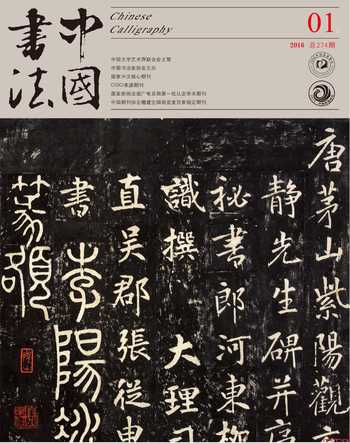叢文俊書學體系研究
張金梁
叢文俊先生是一位集書法研究、創作、教育于一身的大家,僅就書學成就來說,可謂是大學者、真學問家。
一、中國書法史研究的開拓者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書法學術研究方面取得了豐碩成果,而叢先生的書法史研究成果顯得尤其厚重。叢先生的書法史研究可分成書史通論和斷代個案兩個方面:
書史通論是指其對于中國書法史上的各個時代及書體、流派、書家的研究和論述,此最能體現作者的學術思想、解決問題的方法和理論提升能力。這一部分內容涉及了整個書法史及各個時期的重大問題。諸如:書法史學與文化含義,規范正體、實用草體、裝飾性書體的性質及用途,漢字書寫的藝術化歷程,隸書正體化與八分藝術化的區別,隸變分解仿形線條與今文諸體的筆書部件化,隸書與碑別字、俗體字,『善史書』及其文化含義,草書體書法藝術的自覺與『翰墨之道生焉』,魏晉出土文字遺跡的分類、性質與學術意義,魏晉南北朝出土文字遺跡之作者身份的考定及其書法史學意義,魏晉士大夫書法風尚之真實狀態,『蘭亭論辯』與《蘭亭》真偽,北魏崔、盧二門楷法的傳承與魏碑體的形成,古代書家兼擅諸體之傳統的形成,歷代書體與書法發展的不平衡狀態,『民間書法』和『非自覺書法』問題?等等,這些無不涉及書法史上的重大關節和要害焦點。之前,這些問題大都沒被人們發現和認識,通過叢先生的挖掘、探討、研究,不但給書法史增添了豐富、鮮活的內容,而且建立了適用于古今各種書體之科學的書法研究方法和書體考察標準,為解決各個時期書法史問題提供了方便。
叢先生的先秦書法的斷代研究,是眾所周知的重大突破。之前,古今學者在論述先秦書法時,大都假以神話傳說并加以附會,即便有征之實物者,也是孤立無援,不成體系,故而在書法上表現出了先秦無史的狀態。叢先生借助于對先秦史、古文字諳熟的優勢,獨辟蹊徑,大膽探索,厚積薄發,主編了《中國書法全集·商周金文卷》和《中國書法全集·春秋戰國金文卷》等,發表了《象形裝飾文字:涂上宗教色彩的原始書法美》《商周金文書法綜述》等一系列有關先秦文字書法演進的重要文章,而《中國書法史·先秦秦代卷》的面世,填補了先秦書法史的空白。
《中國書法史·先秦秦代卷》的貢獻有四:
一是確立了先秦書法史的框架。在深入研究探討先秦社會和文化背景的基礎上,仔細分析研究了存世的甲骨文字、銅器銘刻、石刻文字、陶器文字、簡帛文字等書法載體,以商、西周、春秋、戰國、秦朝時間順序為縱線,以諸侯國地域文字書法變化為橫線,進行文字書法縱橫交叉、多方疊加的立體分析研究。特別是再將書體劃分出正體、草體、美化裝飾性書體的類別,進行體用之間的推測和認定,從而全面科學地勾勒出了先秦書法史的整體框架,再巧妙地集腋成裘,使支離破碎的先秦文字書法載體融匯成名副其實的書法史。
二是理清了先秦書法的發展脈絡。先秦書法史與文字史的區別在于,書法史關注的更多的是書寫狀態,而最直接表現書寫狀態的是文字的線條。因此,叢先生以商周金文的發展為依據,重新解釋了『篆引』的內涵。他認為『篆』指圖案紋樣,『引書』即篆體線條之粗細勻一的書寫方法和式樣特征,相合而為『篆引』,并用來作為衡量古文字各種書體的基本標準。并創造性地將象形字的線條稱為『仿形線條』,大篆為『準仿形線條』,六國文字為『準仿形簡化線條』,小篆為『圖案化仿形線條』,這一線條系列的劃分,開創了人們重新識讀先秦古文字書法的新篇章。繼之總結出了古文字書寫的三種筆法:一是貫穿于先秦書法的古文筆法;一是篆引筆法;三為簡化篆引筆法,即大篆的草率書寫所產生的現象,它推動了隸變的形成。這高妙的歸納和科學的總結,使研究擺脫了文字學的束縛,讓先秦書法發展的脈絡鮮活明亮了起來。
三是劃分了地域書法風格。春秋以后禮崩樂壞,諸侯各自為政,書法的地域性特點逐漸形成。叢先生通過仔細考察,以重要的諸侯國為中心,劃分成幾個區域:秦國因地處偏僻西部,與東南各諸侯國交流不便,比較全面地保留了西周正體大篆風貌;齊國雖守舊制,然在傳統樣式之外,也有新面目的大篆書法出現;晉走得頗遠,后期在契刻文字上潦草變異現象非常嚴重;楚國較早地拋棄傳統,重視美化裝飾性書法,蔡、越等東南各國隨之風行。并以不同的文字書法載體,結合各種書寫的正、草、美化性書體進行比較,非常清晰明了地將春秋戰國復雜的文字書寫狀況呈現在人們面前,為人們研究欣賞學習此時期的書法提供了方便。
四是確定『隸變』發生在秦書日常書寫中。隸變是中國文字史及書法史上的一件大事,文字以其為分水嶺而有『古文』『今文』之分;在書法上,隸書的出現,使筆法逐漸豐富多變起來,為后來的各種書體的書寫筆法的出現打下了基礎。關于『隸變』,古往今來有眾多學說,叢先生認為:『必須建立起一套關于書體考察的標準,以確保學術研究的嚴肅性和科學性。』于是他通過對眾多的秦國簡牘墨跡的深入探討和研究得出如下結論:一是揭示出了在秦簡中早期『隸變』特征為,在筆勢的變化中出現了超長的筆畫,并出現了新的筆順連結方式和新的體態樣式;二是確定了隸變在秦國日常手寫體中發生,它以獨特的書寫性簡化為基礎,與六國文字的潦草簡率有別;三是澄清了以往關于隸變和隸書體的各種誤解,證明了遲至戰國中期隸變即已經開始。使『隸變』這一重要及復雜的書法現象,有了科學可信的結論。
二、書法批評理論的構建者
叢先生是書法研究的思想者,在書學理論方面亦成果斐然。叢先生認為,中國書學理論體系是以史學為主的,它包括:研究書法在依附于文字變革中所出現的各種本質元素問題的本體論(書法史論);抽繹書法及與社會文化融合規律的闡釋論(書法理論);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對書家、書法的認識和評論的風格論一書法批評);對書法創作中實際操作技術的研究的創作論(書法技法)。叢先生始終將書學理論體系作為一個整體來研究對待,但在書法批評方面似乎著力較多,且獨辟蹊徑,自成家數。其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書法批評詞語方面的分析綜合;二是書法批評方法的探索歸納,高層面地構建了真正的古代書法批評研究的理論體系。
1 書法批評詞語及詞群譜系
叢先生認為,今人對古時書論的理解大都加入現代思想意識,帶有極大的理性化和主觀性。事實上古人的書法評論并不像今人所想象的那樣有既定的方法,但也并非無一點規律可循,只要深入細致地對古人書論進行研究挖掘,就會發現他們面對不同的書家、作品、風格、美感,往往會選擇熟悉的帶有個性色彩的表達方式和詞語來達到理想的效果。但古今語言懸隔,價值觀念和審美旨趣也都發生了很大變化,要想全面深入地把握古人書論,必須將古代書論中的有關語詞弄清楚。于是叢先生將傳統書法術語逐一深入研究,取得了眾多的研究成果。
一是發現了書法批評的詞群譜系,即由核心詞、原生詞、衍生詞依次而成。如書法中的『力』是核心詞,由『力』產生審美感受到的『骨』『筋』『勢』等都是原生詞,而又產生出『神采』『雄強』『道媚』等衍生詞。了解這些,既可準確地把握古人是在哪個層面進行審美批評的,又能追根溯源找到書家或作品的基本風格或美感類型,判斷出批評者的觀念、能力、價值取向等。
二是掌握了詞義選擇組合與書法藝術風格的對應規律。叢先生在研究中發現,古人在書法審美或批評時,往往會把不同的書家、不同的書體、不同的作品中相同或相似的部分,如風格或美感的基本特征劃歸一類,選定一個詞來概括,個性部分則另行擇詞,分別與其組合,詞義的選擇組合,其歷史因循和時代風尚都比較清楚。如宋人書法重個性,對雅俗看得很重,凡與眾不同的作品,便因為是脫俗而冠之以『清』字,以示清流的美質。而由于批評者的審美感受不同,便會產生清雅、清新、清幽、清瘦、清秀、清和、清遠等詞語。『清』代表的時尚是共性,而不同的組合詞所反映的是不同鑒賞者的審美,和不同書家作品的個性差異,對古人來說極具普遍性。概括詞與個性選擇部分的不同組合,大都能表現出對風格美感的細微區別與判斷,并極具普遍性,從而可避免錯誤理解古人書論的問題。
2 古人書法批評方法
古人在評論書法的時候,不像當今書法批評那樣近乎程式化。當他們面對書家、作品、風格、美感時,往往會習慣性地選擇熟悉的帶有個性色彩的表達方式和詞語,以達到理想的批評效果。歷史地看,無數的個性會表現較強的共性,為我們今天抽繹規律、歸納方法提供了可能。當然,這還要有語言的發展與時尚書面語言的文學描寫特征作為參照,應注意到不同的文體對書法思想的表述以及閱讀對象,都有可能產生一定的約束和影響。但仔細分析就會避免走入誤區,可以從眾多的側面來了解古人及其審美和闡釋,進入古人的思想心靈深處,還原一個批評的整體和歷史的真實。
經過大量的研讀思考,叢先生在對眾多個案進行深入分析研究的基礎上,向古代書法批評理論的全面綜合歸納方面展開,將古人對書法批評的類型進行了詳細的搜索和科學的歸類研究,非常準確形象地抽繹出了其中的規律,總結出了古人常用的四種書法批評方法:
形象喻知法:以那些為人們所熟知的物理形象來比喻、來說明書家作品的美感與風格,這是傳統文藝批評普遍應用的方法之一;
比較分析法:對書家之間的藝術造詣和風格特點、類型特征、優劣得失進行比較,也可以用到不同時代的縱向比較和同一時代不同地域的橫向比較,以及不同美感意蘊與書寫要領精義等內容的比較;
經驗描述法:以作者自身經驗為批評依據來進行書法評說。所謂經驗包括兩個方面:一是書寫經驗,它直接與實踐相聯系,二是審美經驗,來自于書寫者的美感體味和總結;
倫理推闡法:即以『知人論書』為前提,將作者的性情、胸次、學養、君子小人之心等與書法聯系起來,進行『書如其人』的主觀性書法批評。
從書法批評的詞語分析到批評類型的歸納,縱橫有象地將古代書法批評的框架結構搭建起來了,其如同一部結構合理、量化準確的分析儀,用之研讀古代書法批評文獻,可非常方便地析離獲得、其中的批評方法及各種文化信息,從而把對古代書法批評的研究推向了一個新的階段。
三、學術思想及意義
1 堅守書學『傳統』
書學『傳統』是當代書學發展的根源和原動力。傳統并不等于保守和固執,創新與傳統并不背離。割斷了傳統,便會使學術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使發展成為空談。叢先生認為要解決中國書法的問題,必須側重運用中國傳統思想智慧,首先要看懂書法,并能了解其產生的社會背景及諸多因素,也就是人的問題;其次是一個學科、一個課題,都有圍繞著它的基本文獻,對其必須爛熟于心,如果對其置若罔聞,就無異于緣木求魚;再次是要重視前人的研究成果,但不受其束縛。在借鑒外來文化思想方面叢先生認為:人們用西方理論、概念和語言表達方式來討論中國書法問題的銳意圖新精神是可取的,但用之全方位地來詮釋和解決中國書法問題是非常困難的。其缺陷在于:由于東西方文化精神及審美意識的差別,若不關注研究對象的時代背景、地域區別、性格特點、評價標準等,一味生吞活剝運用西方詞匯來標新立異,便會以空泛的書法美學掩蓋書法本質,使研究與事實南轅北轍。因此提倡,要打開中國書法問題的寶藏,必須運用中國傳統文化打造的金鑰匙。
2 提倡『博而后精』
叢先生具有非常淵博的學識,從其研究的問題來看,涉及的面非常廣,在古文獻、古文字、書法史、書法理論、書法技法等方面皆有重要成果面世。他認為『書法研究兼乎文史哲及藝術,內涵信息量極大,不下大功夫是搞不好的』。他所說的功夫指兩個方面:『一是讀書不厭其多,不厭其熟,既多且熟才能思想活躍發現問題;二是對發現的問題兼做證實和證偽,證實是廣泛取證,以使觀點成立。』然后由點到線,由線到面,不斷地擴大自己的知識面和研究對象。他曾提出了做學問的必備條件和步驟:一是首先從目錄、版本、校勘等人手,對現存古代書論進行整理;二是要熟悉古代文體,以較好的古代漢語、古典文學知識去準確解讀文獻;三是全面把握古代書論,確認研究課題所在位置、內部結構與基本性質、意義,梳理出來龍去脈,再嘗試用現代的眼光去解釋之;四是發現問題要有能力證明疑點、考察正誤,為研究掃清障礙;五是由一個或幾個問題逐漸擴展到一個領域,以便做專精的深入研究,先具備專家的才能,之后再向通才方面發展。
3 『無法至法』
對于書學的研究來說,方法是非常重要的,它決定著研究的成功與否。《中國書法》雜志所開展的由叢先生主持的書法研究方法的大討論,成為近年來書學研究的一個熱點和焦點,具有極大的現實意義。方法就是指研究問題、解決問題的基本途徑和手段。叢先生認為:『書法研究的理論和方法是以研究對象為前提而存在的,它們因實用而產生,應該是能解決問題,不是給人看、供人清談的。』也就是說,所謂方法是有針對性,如同醫生治病一樣,對不同的病則用不同的藥,若不管什么病都用一樣的藥,不是偽醫便是庸醫。書法研究也是如此,沒有什么統一的研究方法,根據發現的問題,尋找合理的解決方法,即所謂靈活實用的『無法至法』。而要達到如此境界,要從基本方法上下功夫:『所謂基本方法,指怎樣讀書,讀懂本學科的基礎書及必要的相關學科書,怎樣從中發現問題并占有全面、翔實的資料,以科學而有效的手段來解決問題。怎樣對紛雜的現象做出合乎客觀實際的歸納概括,怎樣從具體問題的研究升華到理論層次,怎樣區別問題的性質、特點,并找到合理的解釋,怎樣確定領域,逐步形成自己的學術風格,怎樣學會做新的探索和闕疑,等等。』可以看出,這種基本方法,正是鍛造『無法至法』的秘方所在。
4 『適我無非新』
孫過庭《書譜》云:『自漢、魏已來,論書者多矣,妍蚩雜糅,條目糾紛。或重述舊章,了不殊于既往;或茍興新說,競無益于將來;徒使繁者彌繁,闕者仍闕。』當今假學問、偽學術仍然泛濫流行,令人無可奈何。叢先生對此特別反感,所以在學術研究上其一直遵循『寧缺勿濫』的原則。嘗云:『正誤鉤沉,建樹出新,寫文章沒有證據的話不說,沒有創見不寫。』無獨有偶,當代著名學者李學勤《綴古集》亦云:『論文應有新見解,沒有創見那就不必寫,至少不要發表。』兩位大家可謂是英雄所見略同。王羲之《蘭亭詩》有云:『群籟雖參差,適我無非新。』這一『新』字代表了『書圣』的人生追求。『新』也是叢先生為藝的一個特色,故其每一篇文章都有新資料、新觀點、新成果出現,故而含金量特別高。
5 『平實中見大氣象』
人們搞藝術、做學問皆追求『大氣象』,叢先生在做學問上特別重視之。其一貫倡導書法研究要『守拙持重,平實中見大氣象』。那么什么是『大氣象』?氣象大就是作品、文章所含有的信息多,內涵豐富,境界高深,氣勢逼人。其大概應具備如下幾個條件方能產生:一是學識淵博,心胸寬廣, 二是高屋建瓴,居高臨下;三是意識超前,引導風尚。叢先生在中國傳統文化上博古通今,在書法研究上廣采博取,如同海納百川;叢先生做學問皆追根溯源,取法乎上,每有議論可謂大氣磅礴,勢來不可止;叢先生能對學術走向有較準確的預測判斷,而其諸多論文恰好是新學術思想的前沿和開端。如此,『氣象』便隨之而生。
6 開宗立派獨樹一幟
叢先生書法研究往往從具體的書法現象和文本體裁出發,對其潛在的書法內涵和文化意義進行深入的闡釋,從而表現出其獨立的文化關懷和理想取向。新的思想、新的方法、新的結論,無不充斥在其書法史學、書法理論以及書法技法、書法教育等的一百六十余篇論文和十數部專著中,構成了當代書學研究較為完整的體系。十幾年前白謙慎先生非常謹慎地說:『后人在研究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至二十一世紀初的書學成果時,一定會發現我們這個時代的研究特點。后人將作何評價,我無從預測。但我敢斷言,叢文俊必將被后人視為我們這個時代書學研究的一個重要代表人物。』以叢先生的眾多成果和產生的巨大影響而論,當代中國書壇學術研究上開宗立派的『叢學』已經形成,其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越來越完善和明晰,而其學術意義亦會顯得越來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