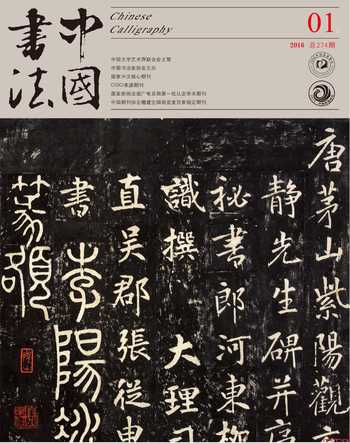雕版印刷與書法傳播
祝帥
【摘要】刻帖與版刻書法,是中國雕版印刷的重要組成部分。關于刻帖與版刻書法的研究,也是一個出版史與藝術史交叉的新興研究領域。它既需要研究者具備古代印刷史和出版史的一般常識,又需要熟悉書法史和書法風格變遷,特別是對于書法創作與欣賞具備一定的藝術標準與眼光。但在出版史研究領域,長期以來,由于二者在古代雕版印刷中并不占據主流,所以在中國古代文字學、圖書史、編輯史、出版印刷史研究領域中都沒有形成研究熱點。相對而言,反而是在藝術史特別是書法研究領域中,卻積累了大量的研究成果。
【關鍵詞】雕版印刷 刻帖 版刻書法
書法史界在古代刻帖和版刻書法相關領域的研究成果,從民國時期便開始有現代學術意義上的積累,研究持續時間長,成果數量眾多。究其原因,一方面取決于書法藝術在中國有強大的群眾基礎,從事書法研究的隊伍規模也遠遠勝于美術、出版等相關領域。特別是近年來隨著書法專業教育的開展與書法專業碩博士培養的擴張,越來越多的書法專業研究生把刻帖或版刻書法作為自己的研究方向,甚至召開了多次以『刻帖』為主題的學術研討會。另一方面,也是因為二十世紀書法與古籍收藏的熱潮,榮寶齋、朵云軒等老字號文物商店大多把刻帖列為單獨的收藏品類,逐漸聚集了專門的研究隊伍。其研究者廣泛分布于中國大陸、北美及日本等國家和地區。尤其是近年來隨著藝術品市場的持續升溫,又有大批文獻出現在拍賣市場上,從而在商品經濟的刺激下,許多收藏界人士對刻帖版本、流傳、鑒定等問題展開了深入的研究,其中不乏根據一手資料提供的可靠的資料或結論,為后續的研究進行了重要的技術準備。這些成果雖然多是從藝術學視角出發,著意于書法風格等問題,一些研究是為密切聯系書法創作的問題而展開,但由于涉及大量版本學、出版學、書籍史議題,這些成果也有必要整合到近年來中國雕版印刷史研究領域中加以綜述。
一、刻帖通史研究
古代刻帖源流與目錄整理方面,民國以來研究者不乏其人,其中尤以張伯英和容庚的研究成果最為突出。
張伯英(一八七一——九四九)是晚清民國時期著名的書法家兼學者,早年從政,晚年專注于金石碑帖研究。張伯英盡管從事法帖的研究,但在他個人的學術研究中也是與碑學研究相提并論的,以至于后人把張伯英重要的書法史著作《法帖提要》和其他大量論碑帖的文獻一起,編入《張伯英碑帖論稿》。《張伯英碑帖論稿》共三冊,收入張伯英畢生研究碑帖著述多種的手稿。其中,第一冊收入《帖平》《庚午消夏錄(碑帖部分)》《說帖》《清芬閣米帖刊誤》《心香閣集帖》《碑帖評鑒校勘文稿》等;第二冊收入《閱帖雜詠》《碑帖題跋》《右軍書范》等;第三冊為《法帖提要》。其中,除《閱帖雜詠》為詩歌體外,其他著述多為帶有古風的學術文章,受現代學術著述文體的影響不大,但作者的個人觀點卻見乎其中。其中尤其重要的是《法帖提要》,這是一部『命題作文』,即作者一九三五至一九三八年參加《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寫作中所負責撰寫的法帖部分。作者對當時根據各大圖書館和私人、海外藏書匯集,并經本人寓目的法帖五百一十余種一一作目錄學式考訂與編目,一一敘述其版本、內容、真偽、優劣等做出點評。該書在未出版時就引起了與張過從甚密的容庚的注意,曾為全文抄錄,并在后者自撰的《叢帖目》這部部頭更大的目錄學著作中大量加以援引,進行高度的評價。《法帖提要》為后人的研究進行了大量基礎性的積累,功不可沒。如果說,近代以降研究刻帖源流目錄,當以張伯英為開山第一人,此話并不為過。
作為古文字學者和書法家的容庚,則是刻帖史研究中的另一位里程碑式人物。容庚是一位著作等身的學者。除了編纂《金文編》等大型工具書之外在他全部著述中部頭最大的,就要算是四大冊《叢帖目》了。這也是迄今為止我們見到的最全面的對于古代刻帖的目錄學整理。雖然對刻帖及其子目的整理者并非旨在『辨章學術,考鏡源流』,因此嚴格地說這種目錄整理與古典學術中之『目錄學』還是有所差別,但這畢竟是一項浩大的工程,在整理目錄這一點上與目錄學的方法并無二致,只是所處理的對象并非文字性書籍,而是書法類書籍,因此把刻帖目錄整理看作一種特殊的目錄學工作似也無可厚非。《叢帖目》將歷代刻帖按照歷代一宋、明、清一、斷代、個人、雜類、附錄分為五類,編為四冊。其中所收刻帖,絕大多數為作者所藏,也有其他寓目而非個人收藏者。除刻帖外,也收入了少量近代以來珂羅版、石印法帖。每種刻帖都詳列其所刻子目,并對其中收帖加以真偽判斷,附收刻帖后附有價值的題跋,部分刻帖目錄最后又以『案』的形式稍述個人觀點。
從今天的觀點來看,雖然限于當時的技術條件,《叢帖目》的編纂方式仍有不盡如人意之處,特別是全書在編排上沒有圖版,是一大憾事,并且遺漏、舛誤之處也在所難免。但就其資料的完備性而言,它已經成為今天書法史研究者一部必備的工具書。其著述體例為傳統學術中的目錄學,并不具備現代學術的形態,但卻是現代學術必備的參考資料,也就是說,它的價值在于把古代叢帖文獻集大成,提供給了后人一個繼續深入研究的起點,使它在刻帖史上成為一部承上啟下的重要作品。有意思的是,容庚雖然是刻帖研究的大家,但他本人的書法創作卻似乎并沒有宗法『帖學』的路線,而是直取三代吉金文字,行楷書中也更多有北碑的色彩。這或許有老一輩學者『書』與『學』各自獨立、涇渭分明以免有失客觀的立場的緣故,但也應該看作是在『碑學』余波尚存的時代中,『帖學』的復興必須經歷一番學術先行,進而才反應在藝術創作中的啟蒙進路。
除了張伯英、容庚兩家,民國以降從事刻帖目錄學的學者及其著述,還有許多。整體來看,這些著作都停留在傳統學術中的『目錄學』,講求文獻與史料的準確性,從而為后來者提供一個按圖素驥的樣本,但還算不上現代意義上的學術研究。在近年來陸續出版的《中國書法史》一類的著述中,大多為刻帖設置了單獨的章節。如聯合書法史界多位一線學者寫作的七卷本《中國書法史》,在宋遼金、元明、清代等各卷中,也都有本時期『法帖匯刻』的內容。
一部真正按照現代學術規范,從朝代源流來敘述刻帖發展歷程的通史性著作,還要推杏林一彭興林一所著《中國法帖史》(上、下冊)。刻帖研究著述的形態,從古已有之的『目錄學』~,發展到現代學術的『通史』,應該說是學術史上的一個重要推進。該書系在吸收晚清民國以降帖學研究著作之成果的基礎上,按照現代學術中『通史』之體例編纂完成的。上冊按照時間線索,詳述法帖匯刻伊始、宋代、金代、元代、明代、清代法帖,每章之前有對本時期政治、社會、文化背景和當朝刻帖情況的綜述,下以重要刻帖為題分為各節,每節對此種刻帖又有基本情況概述和歷史定位;下冊詳述民國法帖(含『近現代研究帖學的論著』一節)、單刻帖以及詳細的『歷代法帖史料編年』,可以看作是此項研究的『附錄』。該書的功績在于,把法帖研究從一種傳統學術推向現代著述體例,把此前支離破碎的『編目』放到整個大歷史的發展框架中加以評述和觀察,資料完備,體例規范。但相對于當代學術進展而言,這部著作只是一部泛泛敘述之作,有些像是教材,對每個章節、每則法帖敘述的篇幅均等分配,其中不免還要介紹大量人云亦云的常識。這種寫法并不利于對作者個人的新見展開深入研究和充分闡述,也沒有按照專題研究的體例發展出作者獨特的問題意識。但所謂『萬事開頭難』,作為第一部《中國法帖史》著作,作者又并非專門學術研究機構或高校的專業研究者,能夠形成現有的規模與讀者見面,已屬不易。
當然,無論是古典形態的《叢帖目》還是現代學術著述《中國法帖史》,應該說都還是屬于通史的范疇,他們的收入或者研究對象,并非根據學術價值和作者對它們的獨到觀點而確定,而是旨在求大、求全。也就是說,無論作者對于此種刻帖是否有基于自家研究所得出的新的學術主張,無論這一通刻帖本身的價值和水準如何,作者都要把他們納入自己的研究視野。尤其是對于容庚來說,他所處理的刻帖,以作者本人收藏和曾經寓目者為對象,一一列入,盡力做到在作者目見的范圍內沒有遺漏。但其實,這種『述而不作』的方式仍然屬于一種基礎文獻整理,從而與現代學術講求『問題意識』『每論必出新見』的主張并不一致。
總的說來,目前通史研究范式存在的主要問題有:(一)樣在研究視角和理論基礎方面,目前刻帖研究屬于書法史研究的副產品,基本上缺乏圖書史、出版史等上級學科的介入與參照,而以藝術學式研究居多;(二)相對集中于刻帖、叢帖編輯、內容等本體的研究,而比較忽視刻帖的出版、流通、銷售等外部研究視角;(三)相對重視刻帖的編纂者和所收入書法家的研究,而忽視對于刻工、刻坊等的個案研究;(四)關于刻帖的起源問題約定俗成地解釋為宋代官刻的《閣帖》,而對此前是否民間已有近似于刻帖的出版行為有欠詳細考察;(五)對于刻帖與后世形成的『帖學』概念的關系流變欠缺學術史式的梳理,對于后來石印技術、照相制版技術之間的承續關系也有欠專門研究。
二、刻帖個案研究
從研究主體來看,從事刻帖及版刻書法個案的研究者,既有受過嚴格的學術訓練的學者,也包括一些常年與刻帖原石或原拓打交道的博物館或文物商店工作人員、收藏家、拍賣工作者等,作為流通領域中的人士,他們常年與刻帖善本等打交道,相對于象牙塔之中的高校研究者而言,他們更具備根據原作展開一手資料研究的條件。其中,尤以王壯弘、施安昌、馬成名等人的成果較為引人注目。
王壯弘是改革開放之后碑帖史研究領域的一位重要學者。《崇善樓筆記》是作者一九五六至一九六六年間在上海古籍書店碑帖書畫部、朵云軒等國營機構工作時所作的筆記,所論皆圍繞工作中過眼善本或照片札記而成。按照該書作者『序言』,這些札記在『文革』中損毀大半,部分稿件則劫后余生,整理后曾以連載的形式發表于《書法研究》雜志。《崇善樓筆記》包括石刻、刻帖、器物、雜記四大類,仿古人宋元明清筆記體淺近文言寫作,雖非實際題跋于每種碑帖拓本之后,但與此種題跋文風頗為類似。其中每條字數長短不一,短則一兩句話,長則作千字文,唯所論皆于實有據,言簡意賅。其中一刻帖』部分,分為『歷代叢帖』和『歷代單刻帖』兩部分。除紀錄作者所見出該帖特出之處、擇錄歷代題跋外,還有關于該帖如何經作者寓目或經手的經過的簡要記述,其中一些記述頗具傳奇色彩。作者也會根據自己的判斷,對所論刻帖真偽問題做出論斷,唯這種論斷均系根據作者常年工作中所積累的目鑒經驗,而無需加以理論的或者科學的證明。
相對于《崇善樓筆記》,則作者的《帖學舉要》顯得更加系統和深入。這本書寫作于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因有感于缺乏一本實用的查考法帖的著作而編撰。彼時雖然有容庚的四大冊《叢帖目》已經編竣,但因該書系在香港出版,而且部頭太大,翻閱不便,故書法界人士很難做到人手一冊。而《帖學舉要》則可以說是一個精簡版的《叢帖目》。作者與容庚有通信之誼,有《叢帖目》作為參照系,一些學術觀點又可互通有無,故《帖學舉要》成為一部兼具實用性與學術性的工具書。作者并非詳細列出歷代刻帖,而是從中選擇了一些常見且著名的帖目,加以詳述其源流及版本,對書法愛好者和書法史學者均有極大的幫助,一些重要刻帖的源流梳理則不厭其詳。其中尤其重要的是,比之《叢帖目》的編排,《帖學舉要》已經有了大量圖版,圖文混排,為讀者提供了直觀的便利。然而,如果據此認為,《帖學舉要》只是一部普及性的著作,而沒有學術上的價值的話,難免有失公允。這是因為雖然這部著作的目的在于普及,但作者一些獨特的研究心得,正是通過這種『舉要』而不是學術論文的方式提交給學術界的。其中關于叢帖中的《淳化閣帖》、單刻帖中的《王羲之十七帖》的論述尤其詳盡,特別是補充了大量民國以降珂羅版影印或日本等國出版的信息,新中國成立后作者寓目或親自經手的一些善本流傳掌故也偶現于其中,讀來饒有興味。
雖然王壯弘刻帖研究中所采用的『筆記體』并非一種現代學術的文體,按照現代學術規范的要求來看一些論斷也缺乏證明和注釋,但就是這種近似于古代筆記、題跋等文體的著述體例,在碑帖研究領域中可謂開辟了一種著述的范式,引發了諸多效仿。其中,馬成名于二0一四年出版的《海外所見善本碑帖錄》就是延續此一著述范式的一部最新力作。而除了在記錄盡量客觀詳盡這一點上一脈相承之外,馬成名的著作與王壯弘著作體例上的一個區別在于,該書沒有過多依據個人書寫經驗而做出真偽的斷言,相反更加注重于法帖的收藏與流傳譜系。在著錄方面,作者詳細錄入了每冊法帖的封面題簽、鑒藏印、題跋等,所附圖片也基本上涵蓋了上述主要信息,而作者體現個人觀點的『按』,只是以小字體附收于每條目之后,這種編排方式令人一目了然,較之王壯弘個人觀點與基本信息混排的方式,當為后來的研究者提供了更多的信息。而該書作者馬成名早年在朵云軒門市部碑帖柜臺接受師徒傳授,曾與王壯弘等人同事,后來擔任紐約佳士得拍賣公司中國書畫部工作人員,使他得以利用常年旅美的地理和職業便利,對流傳海外的碑帖善本做詳盡的考察。因此此書收錄的法帖,全部以作者目見的海外流傳者為限。特別是作者對于宋拓《閣帖》紹興國子監本十冊的『合璧』之功,尤其具有學術史上的意義。
除了古董商人外,還有一類研究者來自干收藏機構,或者其個人本身就是收藏大家。其中,故宮博物院院藏的一些善本刻帖,由故宮的研究員施安昌主持研究,并輯為《名帖善本》出版,成為研究者了解故宮收藏的一個重要窗口。該書編印精美,著錄相近,特別是該書的彩色圖版,不僅收錄了刻帖拓片,而且還提供了部分裝潢成冊的名帖善本在故宮編目收藏原樣的照片。只是這些圖片都只是部分或者局部,應該說只是故宮收藏的一個簡要的目錄。我們還期待故宮博物院等國家文物收藏機構在今后能夠視學術研究為『天下之公器』,進而為全社會的研究者提供更多的目鑒便利,或者至少是發表更清晰、更完整的圖片,而不是突出本機構內部研究人員的『優先研究權』,將大量珍貴的藏品束之高閣。
近年來古代書法史研究領域,對于刻帖和書法傳播領域有兩位學者的著作給筆者留下比較深刻的印象。一是南京藝術學院教授薛龍春的專著《雅宜山色
王寵的人生與書法》,另一位是四川大學教授侯開嘉的論文《照相術的東傳與二十世紀初中國書法的變革》。㈨這兩位作者對于刻帖史料的熟悉程度當然不可能與收藏家同日而語,但難能可貴的是,他們都在開展史料工作的同時,提出了自己創新性的論點并加以論證。
薛龍春的著作從題目來看似乎并沒有『問題的提出』,而是一部書家生平與藝術的泛論,然而與其說這是一部著作,不如說是作者關于王寵研究的系列論文結集,其中多篇論文提出了有創見的學術觀點。該書第五章為《金石氣與木板氣:兩種截然不同的歷史際遇》,提出由于雕版印刷的普及,使得明清書家所接觸和臨摹的經典法帖的母本往往是木板刻帖,這種刻帖不可能真實還原墨跡原作的神韻,相反由于木板介質自身的局限性,使得諸如棗木紋理等在不經意間影響到了點畫的形態。而王寵等書家在真實模仿古人杰作的同時,也在有意無意之中學到了這種介質所造成的『木板氣』。同時,薛龍春也論述了這種帶有貶義的『木板氣』與學習金石碑版而帶來的『金石氣』,何以在書法史上有截然不同的評價等問題。這是一個在書法史上有重要新意的論點,即作者從宗法母本的傳播介質及其傳播特點方面,解釋了王寵等書家書風形成的技術原因及其在后世的歷史定位。
侯開嘉的論文旨在尋求二十世紀上半葉時代書法風尚變化的技術原因。作者所論雖然不是作為雕版印刷的刻帖,但由于二十世紀初石印術和珂羅版印刷術在中國普及開來,珂羅版精印的碑版法帖已經逐漸取代了傳統的刻帖在書法傳播中的重要性,無疑,就復原原作的真實性方面來看,因照相術而誕生的珂羅版印刷具有無可比擬的優勢。包括梁啟超在內的碑學倡導者們普遍意識到,珂羅版興起,一改傳統法帖刊刻失真的弊端,則帖學振興有望。但作者的創見在于,珂羅版印刷碑帖的興起,并不僅僅為帖學復興提供了技術準備,更重要的是它在更深刻的層面上影響了二十世紀書法風格的變遷。這一方面體現在,珂羅版對于法帖筆法的精確復原讓『用筆千古不易』這一帖學圭臬為更多人所接受,從而迎來帖學在二十世紀的復興;另一方面,則體現在珂羅版印刷術的照相技術使得印刷品對于原作隨意放大、縮小輕而易舉,因此過去鑄刻于青銅器上的小字金文可以放大后出版,后人用作大字之法臨寫金文為二十世紀大篆的復興提供了可能。因此,中國碑帖出版主流從雕版刻帖向珂羅版照相影印的技術轉換,是導致二十世紀書風轉換的重要支配性因素。這種問題意識,應該講是囿于善本考證的鑒藏家和博物館系統的研究者所不注意提煉的。
三、版刻書法研究
版刻書法與刻帖,都是與書法關系密切的雕版印刷門類。只不過刻帖多為陰刻,而版刻則多為陽刻。這可能是因為在視覺效果上,陽刻的文字自身內容更有閱讀中的便利,而陰刻則提示接受者更多關注于點畫形態本身的緣故。畢竟從功能性這一點來審視,如果說印行刻帖的側重點就是書法藝術自身的傳播,那么版刻書法則是因為其內容,在可讀性的基礎上提出美化的要求時才會涉及書法的問題。因此相對于刻帖,版刻書法的研究似乎還沒有得到學術界的充分重視。這倒不是說目前對于古籍善本、書籍史、出版史、印刷史研究的數量不夠多,而是說對于善本中的字體這一邊緣性的問題,似乎沒有引起研究者多大的興趣。
其實,這些珍貴的古籍在出版史和版畫史上歷來不乏研究者,可是在書法史的視野中卻備受冷落。不但距離藝術比較遠的書籍史、出版史研究領域不太關心善本古籍的手寫體序跋書法的問題,就連鄭振鐸的版畫史研究奠基之作《中國古代木刻畫史略》中大量介紹中國古代木刻畫書籍,但對其中的書法卻未置一詞。以往對于版刻字體的研究,局限于美術設計研究領域,主要是字體設計和美術字研究。人們關于宋體、仿宋、明體等印刷字體的形成與演變,書籍形態與版式設計以及『聚珍』字體字模等問題或個案展開了比較深入的研究,在應用研究領域,『版刻體』也已經被開發成多種電腦字庫字體,為現代設計領域所廣泛采用。但是關于版刻字體的研究,更多是由美術、設計界的研究者來從事的,書法史界的人對此著墨不多。并且基于活字印刷而展開,而沒有充分注意到雕版印刷中更多非規范化形態的『字體』。
版刻書法通史性的研究目前所見不多,并且多為外國學者所展開。其中資料最全、系統性最強的一部著作,當推廣州美術學院教授祁小春在就讀日本立命館大學文學(東洋史)博士后期課程期間所撰寫的《中國古籍板刻書法》一書。該書為日文,圖版較多,可以說是一部圖錄。作者曾長期從事古籍整理工作,也是書法史研究領域的專家,因此該文是書法史研究中對于版刻書法研究較為全面的一篇綜論。作者受過『京都學派』嚴格的實證史學訓練,既重視『問題的提出』,也重視史料和史實挖掘的準確與深入。該書從『時代與真偽』『序跋內容』『序跋文的相互關聯性』『書風判定』等角度人手,使用文獻資料參照、筆跡比較對照一包括版刻書跡的相互比較對照、版刻書跡與傳世書跡的比較對照一等方法,對宋、元、明、清四代的版刻書跡進行了綜述。其中,對歷來被認為是出自趙孟頫的手筆、備受藏書界重視的《兩漢策要》的個案解析,以及將《程氏墨苑》和萬歷年間中國雕版印刷的高峰聯系在一起的有關敘述尤其精彩。《中國古籍板刻書法》一書所附的大量圖版,也是研究版刻書法必不可少的基礎資料。應該說,這是一部積累性的著作,它所做的是一種開創性的工作,也是一個起始階段,作者以日本京都學派書法史研究的『實證』精神,為后來版刻書法的深入研究進行了重要的文獻梳理和資料準備。
而在北美,相關學者關注書法與古籍的問題時間至少要追溯到一九八九年,這一年,漢學家牟復禮(Frederick W.Mote)和朱鴻林(HungLamChu)合作撰寫的《Calligraphy and the East AsianBook》一書正式出版。㈣這本書本是為美國普林斯頓藝術博物館所舉辦的一次『書法與古籍』的展覽所作的文字描述。參與撰寫者,還有陳葆真、蕭蕙芳、柯偉勤等臺灣學者或漢學家。應該說,由于這本書是一次展覽的注記目錄,并不是一本獨立意義上的海外漢學研究的專著,所以該書并沒有像一般海外學者的研究著作那樣集中于一個較為窄小的領域,并提出鮮明的問題意識,相反,該書也像是一本版刻書法研究的通史,其中包含一些泛泛的介紹。該書在研究方法方面的特點在于,將版刻書法放在整個中國書籍史的長河中關注其流變,同時,在古籍研究中突出一條書法的主線,既看到書法在書籍史中的重要作用,也看到了書籍載體在多大程度上反過來影響了時代書風的變遷。在書法研究已然遠遠遜色于繪畫研究的北美漢學界,出現這樣一本打通印刷史、出版史與書法藝術史的著作,雖然所論尚嫌粗淺和普及,但無疑為后來的研究開辟了一種彌足珍貴的研究范式。
此外,相比較祁小春的著作,本書所牽涉的時間段更長,即不僅僅是著意于書法與雕版印刷之關系,就連雕版印刷出現之前的書籍形態,如簡牘、碑刻、卷子本等,也納入『古籍』的范疇。這與一般國內習慣所說的古籍特指印刷書籍大不相類。因此,該書上接錢存訓等人關于『書于竹帛』的早期圖書史研究,下連雕版印刷發明之后刻書的創新。其中尤其值得關注的是對于敦煌經卷的研究。眾所周知,敦煌藏經洞既是研究政治史、軍事史和社會史的寶藏,也是研究中國書籍制度史的淵藪。敦煌藏經洞經卷所涵蓋的時間階段,即歸義軍統治時期一直到藏經洞封閉的這段時間,恰好相當于中國雕版印刷術普及期,所以敦煌文獻忠實地保存了中國書籍出版由手寫卷子本向雕版印刷轉型這一關鍵時期的諸多實物史料。
只是限于展覽目錄的體例,該書這方面的資料和研究都還顯得粗淺,倒是近年來書法史界出現的一些研究已經逐步走向深入。如蘇州大學副教授毛秋瑾在《墨香佛音 敦煌寫經書法研究》一書中所指出的,雕版印刷形成之初所采用的字體,多系根據顏真卿、歐陽詢等中原書家的字體加以規范而成,因而在雕版印刷普及特別是四川地區的『西川印本』在敦煌流行之后,『老百姓將其作為臨本抄寫《金剛經》等佛經,因而在書法上不自覺地受到了顏真卿、歐陽詢等人書風的影響』。這種發現,對于書法史而言,很好地解釋了在敦煌地區流行一時、橫細豎粗、捺腳粗大的『六朝寫經體』(亦稱為『經生體』『北涼體』等)為何在后來逐漸減少,并為一種新的接近中原地區書法規范的新字體所取代的外部原因;同時對于雕版印刷史而言也不啻是一種新的發現,即以往的研究總是側重于『書法如何影響雕版印刷』,而新一代的學者已經開始注意到『雕版印刷如何影響書法』,即雕版印刷普及之后如何反作用于書法風格變遷的深層問題。至此,新的學術范式實際上已經呼之欲出了。
而中國美術學院教授范景中的《書籍之為藝述——趙孟頫的藏書與一汲黯傳一》更是一篇改變書法史研究范式的代表作品。該文的研究對象是歷來歸于趙孟頫名下的一件小楷作品《漢書·汲黯傳》。由于這件作品與趙孟頫其他傳世的法書相比,字形似更硬朗,筆道似更峻挺,因而歷代均有研究者斷定其為俞和所書。關于俞和此人生平正史上缺乏詳細記載,但他極有可能是趙孟頫身邊的一位關系很近的晚輩,比如他的學生或者外甥。其書風極似子昂,一些作品幾可亂真。以往研究者正是根據此帖與趙書極其類似,但又有上述與其他作品不同的特點猜測為俞和作偽。然而,范景中敏銳地從該帖后附題跋中發現有『此刻』之說,大膽推斷該帖不但是子昂真跡,而且是他難得一見的臨摹作品,并且更重要的是,其所臨摹的對象并非經典書家作品,而是一部宋刻本《漢書》上的雕版版刻字體。這種版刻字體系根據唐代書法家歐陽詢的書風而刻制,因此當刻本成為臨本,趙書墨跡中自然就有了歐書的提按頓挫,而與其其他墨跡有所差異。為了論證這一假設,范景中從論證趙孟頫的藏書中有一部宋刻本《漢書》開始,直到引用中西經典著述論證善本書籍自身所具有的藝術性和審美價值。全文旁征博引,縱橫捭闔,談論書法作品而不囿于書法史這一個研究領域,不但完成了書法史研究中的一次考證,而且通過從藝術史、文獻史到書籍史的跨界與穿越,向其他學科也提出了帶有啟發性的追問。結語
整體而言,目前書法界關于刻帖和版刻書法的研究,可以稱得上是『盡精微』,但還不能算是『致廣』這是因為,書法史研究領域的成果,或出自非專業學術人員之手,或出自鑒賞家、收藏家、博物館、賣主根據自家或經手藏品而得出,因此雖然考證詳細,觀察細致周密,但常常缺乏現代學術所要求的問題意識,無法從某一件作品中提出有可能形成理論、進而對其他學科有影響的規律或者范式。與此同時,由于書法研究領域相對封閉,一些書法史研討會多局限于本專業人員參加,所以常常無法通向出版史、古籍史、圖書史、檔案史等其他領域。學術壁壘的森嚴,也使得出版史等領域關于通史研究的相關進展、學術觀點與理論等無法對書法史研究產生更加深刻的影響,反過來,其他領域的學者也極少有機會接觸到書法史研究領域的成果。面向未來,這種局面亟待改觀。而在筆者看來,穿越藝術史與出版印刷史的邊界,呼喚一種書法史與書籍史交融的研究視角,似應成為當務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