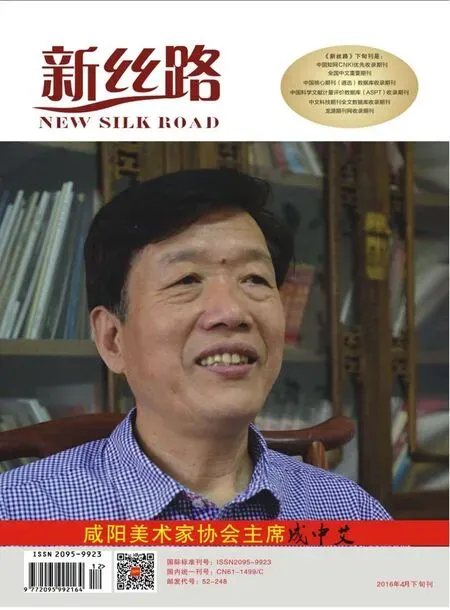論我國民事再審程序的完善
許誼珈(中共和田地委黨校 新疆和田 848000)
?
論我國民事再審程序的完善
許誼珈(中共和田地委黨校新疆和田848000)
摘 要:民事再審程序,其存在的根本是為了糾正司法裁判的錯誤,以便于更好地保護當事人合法的民事權(quán)益。但是隨著社會的不斷發(fā)展,法治文明的不斷進化,我國的民事再審程序在實踐中存在的弊端也越來越明顯,當事人的私權(quán)和國家機關(guān)的審判監(jiān)督權(quán)沖突不斷。這嚴重破壞了我國司法的權(quán)威性。本文如何改革與完善民事再審程序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
關(guān)鍵詞:民事再審;弊端;完善
【DOI】10.19312/j.cnki.61-1499/c.2016.04.022
民事再審程序作為民事訴訟法中一項不可或缺的訴訟程序,其不同于民事一審二審程序,民事再審程序并不是訴訟中的必經(jīng)程序,但其存對維護我國司法權(quán)威性和保護當事人的合法利益有著不可估量的意義。
一、民事再審程序概述
1.民事再審程序的概念
民事再審程序是指為了糾正已經(jīng)發(fā)生法律效力的裁判中的錯誤,而對案件再次進行審理的程序。
再審程序并不是每個案件的必經(jīng)程序,其存在是對我國兩審終審制的一種必要補充,它只對已經(jīng)發(fā)生法律效力并且符合再審條件的判決、裁定、調(diào)解協(xié)議有約束力。民事再審程序作為民事訴訟程序制度中一項不可或缺的訴訟程序,不僅有利于保證辦案質(zhì)量,維護法院的司法權(quán)威,更有助于保護當事人合法的民事權(quán)益。
2.民事再審程序的特征
(1)程序性質(zhì)的救濟性
救濟性是民事再審程序的本質(zhì)特征。為了維護司法權(quán)威,實現(xiàn)法律公平正義的價值目標,民事再審程序的存在本身是為了糾正生效裁判中的錯誤,從而保障當事人的合法權(quán)益。作為一種事后補救的程序,其本身存在明顯的救濟性。
(2)啟動主體的特定性
我國民事訴訟法規(guī)定,提起民事再審程序的主體有三:當事人,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
當事人申請再審必須滿足以下條件之一:有新證據(jù);原判認定事實的證據(jù)有偽造或者未經(jīng)質(zhì)證的情形;法院未依申請調(diào)取證據(jù);原判適用法律確有錯誤;違反回避規(guī)定的;必要當事人因客觀原因未到庭的;損害當事人辯論權(quán)利的;未經(jīng)傳喚,做缺席判決的;裁判超出訴求的;據(jù)以做出原裁判的法律文書被撤銷或者變更;審判人員有徇私枉法裁判行為的。通過以上條件可以看出,將當事人列為申請再審的主體之一主要是為了保護當事人的合法權(quán)益,考慮到裁判出現(xiàn)錯誤時,會對雙方當事人會造成很大損害,故賦予當事人申請再審的權(quán)利,以此保障其合法權(quán)益。
人民法院決定再審,是指人民法院對己經(jīng)發(fā)生法律效力的判決和裁定,發(fā)現(xiàn)其確有錯誤,依其審判監(jiān)督職能對案件提起再審。人民法院決定再審要滿足以下條件:必須是發(fā)現(xiàn)已經(jīng)生效的裁判確有錯誤,各級法院院長,最高人民法院,上級人民法院,發(fā)現(xiàn)本院或者各下級人民法院已經(jīng)生效的裁判確有錯誤的,有權(quán)提審或者指令下級人民法院再審。生效的判決、裁定確有錯誤,包括其在認定事實方面存在的錯誤,也包括在適用法律方面存在的錯誤。將人民法院列為提起再審的主題之一主要是為了督促法院自身的辦案水平,保證案件準時辦結(jié)的同時提升案件的質(zhì)量。
人民檢察院抗訴引起再審的條件和當事人申請再審滿足的條件一致,最高人民檢察院、上級人民檢察院發(fā)現(xiàn)各級或下級人民法院裁判錯誤的案件都能提出抗訴,同級檢察院只能向同級法院提出檢察建議,或者向上級檢察院申請抗訴。賦予檢察院此項權(quán)力主要是考慮到檢察院作為國家檢察機關(guān),理應(yīng)履行其監(jiān)督權(quán),確保法律的公平正義,維護當事人的合法權(quán)益和法律的威嚴。對原裁判確有問題的,其有權(quán)提出抗訴保護當事人權(quán)益。
(3)審理對象的有限性
再審程序并不針對所有的案件材料,其針對的是已經(jīng)生效的判決,裁定或者調(diào)解書這三樣法律文書,另外,離婚判決不得申請再審。對上述三樣生效的法律文書申請再審的人必須提供出確切證據(jù)證明其的確存在錯誤,如此才能推動案件再審程序的啟動。
(4)執(zhí)行的暫停性
按照審判監(jiān)督程序再審的案件,應(yīng)當裁定中止原裁決的執(zhí)行。
二、我國民事再審程序存在的問題及危害
1.對再審當事人的合法權(quán)益保護不到位
我國 《民事訴訟法》從制定到修改,法院和檢察院一直具有啟動再審程序的權(quán)利,從現(xiàn)行《民事訴訟法》的規(guī)定看來,只要法院和檢察院發(fā)現(xiàn)生效裁判出現(xiàn)法律規(guī)定的能夠啟動再審程序的情形,它們雙方就可以依職權(quán)主動發(fā)起再審或者提起再審抗訴,從而啟動再審程序,當事人是否申請再審并不影響法院和檢察院的再審決定,而眾所周知,案件本身的裁判對當事人的利益影響非常大,法院和檢察院不問當事人意見就對案件發(fā)起再審,有些當事人并不同意發(fā)起再審,如無疑是侵犯了當事人的處分權(quán)。而眾所周知,當事人的處分權(quán)是“私法自治向民事糾紛解決領(lǐng)域的直接延伸,保障了當事人的意志自由,獨立和自主”。
法院,作為我國的司法機關(guān),本身應(yīng)當保持中立的法律地位,其作為提起再審的主體,雖然糾正了自身存在的錯案,卻否認了自身曾做出的判決,損害了司法的權(quán)威同時,使得公民對法院的信賴也有所降低。而我國的審判制度遵循的是不告不理原則,法院主動提起再審明顯違背了此項原則,侵害了當事人的自由處分權(quán),原判案件的審理是否有錯誤,是否損害了當事人的合法權(quán)益,是否應(yīng)該提起再審;這些問題本來就應(yīng)當由當事人決定,而不應(yīng)當由法院來決定是否提起再審。
檢察院,作為我國的監(jiān)督機關(guān),其本身有權(quán)對法院審判的案件進行監(jiān)督,賦予其再審抗訴的提起職權(quán)是理所當然的,但是其監(jiān)督范圍應(yīng)當僅限于法院在審判過程中出現(xiàn)的程序性差錯,對于當事人自身的實體權(quán)利應(yīng)當由當事人自身進行處分,而其提起再審的權(quán)力,無疑是幫助當事人處分了自身的實體權(quán)利,這與我國私權(quán)自治的法律理念是相違背的。依照現(xiàn)行《民事訴訟法》可知,檢察院提起再審抗訴,一般法院是不能拒絕的,這就使得檢察院作為再審抗訴的提起主體,其自身提起抗訴時缺乏有效的監(jiān)督機制,這就可能導(dǎo)致檢察院出現(xiàn)濫用權(quán)利的情況。侵害了當事人合法權(quán)益的同時,同時會導(dǎo)致訴訟資源的浪費。
2.對再審有關(guān)期限的規(guī)定不明確
2012年修改后的民事訴訟法規(guī)定:當事人申請再審的時間為判決、裁定發(fā)生法律效力后的六個月內(nèi),雖然將原先兩年的申請時間縮短為了六個月。但是其只規(guī)定了當事人申請再審的一般期限,并沒有給出一個最長的申請時間,另外并未對法院決定再審和檢察院抗訴的期限進行規(guī)定,也未對當事人申請抗訴或者提出檢察建議的期限予以限制。這就使得在實踐過程中,當事人可能會出現(xiàn)反復(fù)申請抗訴或者提出檢察建議,這會造成很大的司法資源的浪費,加重法院和檢察院本身的職務(wù)負擔,降低案件的結(jié)案效率。
3.對我國的二審終審制度的沖擊
我國目前實施的是兩審終審制度,即:一個民事案件經(jīng)過兩級法院審判就宣告終結(jié)的制度。而再審制度的存在,就是說,對于滿足法律規(guī)定條件的生效判決,當事人、法院和檢察院,他們?nèi)我环蕉伎梢陨暾垎釉賹彸绦颍賹彸绦虻膯樱瑹o疑是出現(xiàn)了第三次審判。比如說,法院自行決定再審,會產(chǎn)生一審判決后當事人未上訴,案件不經(jīng)二審程序,而是直接經(jīng)過再審程序改判,當事人還有權(quán)利上訴或申請再審,從而破壞二審終審制度,擾亂司法訴訟秩序。
現(xiàn)行《民事訴訟法》第二百零七條規(guī)定:人民法院按照審判監(jiān)督程序再審案件,發(fā)生法律效力的判決、裁定是由第一審人民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一審程序?qū)徖恚鞒龅呐袥Q、裁定,當事人可以上訴。這一規(guī)定即意味著已經(jīng)經(jīng)過一次再審的一審案件,如果當事人認為還有錯誤依舊可以再次提起上訴,進行二審。而二審結(jié)束后,依照法律規(guī)定,如果當事人認為還有錯誤,依舊能夠申請再審,那么一個案子就總共出現(xiàn)了四次審理。這嚴重背離了我國二審終審的審判制度,同時浪費了大量的司法資源。
三、其他地區(qū)的民事再審程序的相關(guān)規(guī)定
1.臺灣地區(qū)的民事再審程序
臺灣地區(qū)的民事訴訟法將再審程序直接定義為為“再審之訴”。按照法律規(guī)定,“于再審之訴得為原告被告,即有當事人之適格者,為原訴訟之當事人及原判決之既判力所及之人。原訴訟之參加人,不得提起再審之訴,因再審之訴為聲明不服之一種非常手段,且屬新訴故也。至再審之訴不得以原訴訟之參加人為相對人,更不待言。”由此可見臺灣地區(qū)民事訴訟法將提起再審的主體嚴格定義為訴訟的當事人。提起再審的事由包括:
(1)適用法律顯有錯誤者;
(2)判決理由與主文顯有矛盾者;
(3)判決法院之組織不合法者;
(4)依法律或裁判應(yīng)回避之推事參與裁判者;
(5)當事人于訴訟未經(jīng)合法代理者;
(6)當事人知他造之居所,指為所在不明而與涉訟者;
(7)參與裁判之推事關(guān)于該訴訟違背職務(wù)犯刑事上之罪者;
(8)當事人之代理人或他造或其代理人關(guān)于該訴訟有刑事上應(yīng)罰之行為,影響于判決者;
(9)為判決之基礎(chǔ)之證物系偽造或變造者;
(10)證人、鑒定人或通譯就為判決基礎(chǔ)之證言,鑒定人或通譯人為虛偽陳述者;
(11)為判決基礎(chǔ)之民事或刑事判決或行政處分,依其后之確定裁判或行政處分已變更者;
(12)當事人發(fā)現(xiàn)未經(jīng)斟酌之證物或得使用該證物者,但以如經(jīng)斟酌可受較有利益之裁判者為限。
此外,臺灣民事訴訟法第 497 條規(guī)定:依第 466 條不得上訴于第二審法院之事件,除前條規(guī)定外,其經(jīng)第二審確定之判決,如就足影響于判決之重要證物,漏未斟酌者,亦得提起再審之訴。
再審之訴,應(yīng)在判決確定時 30 日之不變期間內(nèi)提起,再審之理由知悉在后者,自知悉時起算。另外,再審之理由發(fā)生于判決確定后者,自發(fā)生時起,如已逾五年者,不得提起再審。
2.日本的民事再審程序
日本審級制度采取四級三審制,最多經(jīng)過三級法院審理,裁判即發(fā)生法律效力。對于已確定的終局判決因法定理由不服的,可以提起再審之訴。按照《日本民事訴訟法》的規(guī)定,在下列事由的情況下,對于確定的終局判決,當事人可以提起再審之訴,但是,當事人已經(jīng)以控訴或上告主張該事由時,不在此限:
(1)判決是沒有依照法律規(guī)定組成的法庭作出的;
(2)根據(jù)法律規(guī)定不能參與判決的法官參與判決的;
闞夕國也表示,近5年,行業(yè)發(fā)生了巨大變化,隨著土地流轉(zhuǎn)的加速,農(nóng)民用肥更加理性,單純的提供肥料已經(jīng)不能滿足種植戶的需求,好的技術(shù)服務(wù)和支持變得越來越重要,云圖控股也在積極籌備從一個復(fù)合肥的生產(chǎn)提供商轉(zhuǎn)變?yōu)槿蝾I(lǐng)先的高效種植綜合解決方案提供商。
(3)對法定代理權(quán)、訴訟代理權(quán)或代理人為訴訟行為欠缺必要授權(quán)的;
(4)參與判決的法官,犯有與案件有關(guān)職務(wù)上的犯罪的;
(5)根據(jù)他人在刑事上應(yīng)懲罰的行為而自認或妨礙提出可以影響判決的攻擊或防御方法的;
(6)作為判決證據(jù)的文書其他物件是經(jīng)過偽造或變造的;
(7)以證人、鑒定人、翻譯或經(jīng)宣誓的當事人或法定代理人的虛偽陳述作為判決的證據(jù)的;
(8)作為判決基礎(chǔ)的民事或刑事判決以及其他的裁判或行政處分,根據(jù)其后的裁判或行政處分而變更的;
(9)對于能影響判決的重要的事項遺漏判斷的;
(10)聲明不服的判決,與此前確定的判決相抵觸的。

綜上所述,可以看出臺灣和日本地區(qū)的再審制度存在以下幾點特點:首先,其對提起再審的主體做出了明確的限制,即只允許當事人提起再審申請,法院和檢察院并無權(quán)提起再審之訴。其次,其嚴格規(guī)定了再審之訴的提起條件,即只有原生效裁判切實損害了當事人的實體權(quán)益才允許向法院提起再審之訴。最后,其明確規(guī)定了當事人提起再審之訴的期限,并對該期限給出了一個最長期限,即判決被確定之日起超過五年的,當事人就不能提起再審之訴。
四、我國民事再審程序的完善
1.確立當事人在再審啟動程序中的中心地位
眾所周知,案件的再審對雙方當事人的影響十分重大,其直接涉及到雙方當事人的合法利益。人民法院可以在當事人未提出再審申請的情況下依職權(quán)主動引發(fā)再審程序,既有違“私權(quán)自治”的原則,也有違法院司法的中立性和被動性。故為了更好的保障當事人的合法權(quán)益,應(yīng)當將案件提起再審的主動權(quán)交給當事人,限制法院和檢察院依職權(quán)主動提起再審程序,即建立當事人申請前置的再審啟動程序,這也是對當事人自由處分權(quán)的保護,防止國家公權(quán)力干涉公民的私權(quán),保護公民的合法私權(quán)利益。
盡管前面提到,賦予法院和檢察院提起再審的職權(quán),會對司法權(quán)威和生效裁判的即判力造成損害,但是考慮到當事人自身的能力有限,對法律的認知水平也不同,在某些確有錯誤的裁判中,并不懂得如何保護自身的合法權(quán)益,同時考慮到個別特殊的案件會牽扯到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或第三人利益,因此應(yīng)當保留法院和檢察院提起再審的職權(quán),但再審的發(fā)起還是應(yīng)當由當事人承擔中心角色,法院和檢察院在這里只是起一個保障作用,也就是說法院和檢察院可以依法申請啟動再審程序,但再審程序的啟動必須征求當事人的意見,除非涉及國家,社會公共利益、第三人利益的情況下,法院和檢察院可以不經(jīng)當事人同意依職權(quán)啟動再審程序,其他一切關(guān)乎到當事人自身實體權(quán)益的案件的再審啟動程序,必須征得當事人的同意方可啟動。建立這樣一種以當事人為中心,當事人申請再審前置的再審程序啟動模式,就使得當事人的合法權(quán)益能夠得到更高的保障,體現(xiàn)了民事再審程序的救濟性特征,也符合法律公平正義的價值追求。
另外,針對檢察院提起再審抗訴問題,應(yīng)當對其提起抗訴的次數(shù)加以限制,從法條看來,只要是檢察院提出的再審抗訴,人民法院基本是必須要接受的,如果不限制人民檢察院提起抗訴的權(quán)利,那么由于檢察院和法院二者所處的法律地位不同,二者對案件的理解水平也不同,就容易導(dǎo)致法院裁判的某個案件總是讓檢察院覺得存在錯誤,而案件存在錯誤,檢察院就可以向法院提起抗訴,如果不對抗訴次數(shù)加以限制,就會使得檢察院和法院的關(guān)系由于抗訴的原因變得越來越緊張,不利于雙方日后的相處,同時會影響到法院的終審裁判權(quán)。故應(yīng)當限制檢察院的再審抗訴次數(shù),檢察院的再審抗訴應(yīng)當以一次最佳,最多不超過兩次。
2.明確再審申請最長期限,限制申請次數(shù)
我國現(xiàn)行《民事訴訟法》第二百零五條規(guī)定:當事人申請再審,應(yīng)當在判決。裁定發(fā)生法律效力后六個月內(nèi)提出;有本法第二百條第一項、第三項、第十二項、第十三項規(guī)定情形的,自知道或者應(yīng)當知道之日起六個月內(nèi)提出。從該法條中我們可以看出,當前我國的民事訴訟法只規(guī)定了當事人提起再審申請的一般期限,但并未給出最終期限。這從法條看來也就是說,當事人不論事隔多久,只要發(fā)現(xiàn)了能夠提起再審申請的事由,都能夠提起再審申請,這就使得已經(jīng)形成的法律關(guān)系長期處于不穩(wěn)定的狀態(tài),不利于保障對方未提起再審申請當事人的合法權(quán)益,因此,在這方面我們應(yīng)當借鑒臺灣和日本地區(qū)的民事再審程序,給我國當事人申請再審的定下一個最終期限,即從原裁判生效之日起,一定期限屆滿后,超過此期限的,當事人不得申請再審。
對于當事人向檢察機關(guān)申請抗訴或者檢察建議的期限,我國當前的《民事訴訟法》也缺乏進一步的規(guī)定,但是可以參照現(xiàn)行《民事訴訟法》的第二百零五條的規(guī)定來確定當事人申請抗訴或檢察建議的期限,即:當事人應(yīng)當在知道或者應(yīng)當知道申請抗訴或者檢察建議情形之日起,六個月內(nèi)向上級或者同級檢察院提出申請,也就是說在法院駁回再審申請;逾期未對再審申請作出裁定;在當事人發(fā)現(xiàn)或者應(yīng)當發(fā)現(xiàn)再審判決、裁定有明顯錯誤之日起六個月內(nèi),當事人可以向人民檢察院申請抗訴或者檢察建議。對該項申請制定一個特定的期限,有助于推動司法程序的進一步進行,從而避免司法資源的過度浪費。由于當事人申請抗訴和檢察建議的期限和當事人申請再審的期限是一致的,因此,也就是說當再審申請期限屆滿時,當事人也就不能夠再向檢察機關(guān)申請抗訴或者檢察建議了,其申請權(quán)利隨著期間的屆滿一并消除了。
我國現(xiàn)行《民事訴訟法》只規(guī)定了啟動再審程序的主體,啟動事由,申請啟動的期限,但是對再審程序的申請次數(shù)并沒有給出具體的說明,雖然再審程序是一種救濟性的程序,其主要是為了糾正法院在裁判中的錯誤,但是如果不限制當事人申請再審的次數(shù),允許當事人無限申請再審,那么不僅會加大法院和檢察院的工作負擔,造成司法資源的大量浪費,更重要的是,他對司法的權(quán)威性有很大的沖擊作用,使得某項法律關(guān)系長期處于不穩(wěn)定的狀態(tài),不利于保護當事人的合法權(quán)益。所以限制當事人的再審申請次數(shù)是十分有必要的,最好是以申請一次為限,當然也有特殊情況,比如說碰到當事人人數(shù)在10人以上的較大型的,并且案情比較復(fù)雜的案子,可以給予兩次的再審申請次數(shù),但最高不應(yīng)當超過兩次,這對法律的公平正義和司法權(quán)威的保護十分重要。
3.在再審程序中確立再審之訴
在我國的再審程序中,為了避免無限申訴和無限再審的情況不斷出現(xiàn),使得司法資源被大量浪費,同時也為了更好的保護當事人的合法權(quán)益,我國的民事訴訟法可以借鑒臺灣及日本的民事再審制度,可以在再審程序中確立再審之訴。
再審之訴,顧名思義是指當事人或者案件的利害關(guān)系人,由于不服原審法院的生效裁判,依照法律規(guī)定要求法院撤銷該裁判并對案件進行重新審理和裁判,以保護其訴訟利益的一種訴訟模式。它是以訴訟程序來構(gòu)造再審程序,將再審主體、再審理由、再審對象都賦予訴的要素。大陸法系國家基本都認為申請再審的權(quán)利是一種訴權(quán),也就是說只要當事人及其利害關(guān)系人的申請在法律所允許的范圍內(nèi),就會引發(fā)再審程序。縱觀我國民事再審程序的設(shè)計不難發(fā)現(xiàn),我國的民事再審程序并沒有把當事人的訴權(quán)放在一個較高的位置上,再審中強調(diào)的是公權(quán)力對再審的提起,不論公民是否申請再審,法院和檢察院都能依自身的職權(quán)推動再審程序的進行,這對于公民自身的訴權(quán)是十分不利的,嚴重損害了公民的憲法權(quán)利,故“申訴難”和“再審難”問題才不斷出現(xiàn),因此在民事再審程序中確立再審之訴是十分必要的。
當事人通過再審之訴,以訴權(quán)的形式保障了其申請再審的權(quán)利,行使自身的處分權(quán),保護自身的合法權(quán)益,其提起再審不需要經(jīng)過國家任何機關(guān)的同意。只要滿足法定要求,再審程序就可以依當事人申請啟動。需要注意的是提起再審之訴的訴訟時效,對于該訴訟時效我國可以參照臺灣或日本的相關(guān)規(guī)定,將該時效定為:當事人應(yīng)當在判決被確定之后,得知再審的事由之日起 30 日不變期間內(nèi)提起再審之訴。判決被確定之日起經(jīng)過 5 年時,不得提起再審之訴。這樣確立一個最高的時效期間,便于保護法律關(guān)系的穩(wěn)定性,維護司法的權(quán)威。堅持確立再審之訴的制度,不僅完美的化解了國家公權(quán)力干涉公民自由處分權(quán)的矛盾,使得公民的憲法性權(quán)利,即申訴權(quán)和申請再審權(quán)得到了更大的保障,同時也解決了“申訴難”和“再審難”這兩大一直困擾著公民的大難題。
4.確立再審一次終局原則
我國民事訴訟法第二百零七條規(guī)定了再審案件的審理情形,其指出民事再審程序按照一審程序?qū)徖淼模斒氯藢υ賹彶门幸琅f不滿的還能夠提起上訴。就如同前面說到的,對一個案子可能會出現(xiàn)連續(xù)四次的審理。這嚴重違反了我國二審終審的審判制度。
為了避免啟動再審程序的盲目性、隨意性,應(yīng)注重對當事人如何行使訴權(quán)的引導(dǎo)作用,采取必要措施對當事人的申訴權(quán)、再審申請權(quán)加以規(guī)范。
顯而易見,民事再審制度其存在是為了保護當事人的合法權(quán)益,是一種事后救濟的程序,但是并不意味著再審的次數(shù)越多對當事人的救濟程度就越到位。恰恰相反,某個案件進行再審的次數(shù)越多,越說明法院辦案工作做的不到位,辦案質(zhì)量低下,司法效率低下,不僅浪費了訴訟資源,增加了當事人的訴訟負擔,同時也使得我國的司法權(quán)威受到挑戰(zhàn),進一步使得公民們對法院解決糾紛的能力產(chǎn)生懷疑,這樣最終大家都不會想要選擇用司法手段來解決自身糾紛,寧愿選擇仲裁機關(guān)也不愿選擇法院,這對我國的司法機關(guān)的發(fā)展會產(chǎn)生不利影響。
因此,為了維護司法權(quán)威,更好的保障當事人的合法權(quán)益,節(jié)約當事人的訴訟成本,避免訴訟資源的過度浪費,我們應(yīng)當追求高質(zhì)量的再審程序,把所有的工作一次性做到位,嚴格限制民事再審次數(shù),同時要堅持當事人申請再審的條件應(yīng)當以其自身已經(jīng)對一審案件上訴過為前提,再審程序作為當事人救濟自身合法權(quán)益的最后一道防線,理應(yīng)是當事人用盡所有已經(jīng)能夠使用的手段,仍舊無法保護自身的合法權(quán)益才來選擇的最后的一道保障。法律賦予當事人上訴權(quán)就是為了保護當事人的合法權(quán)益,而當事人本身應(yīng)當積極履行自身的這項權(quán)利以維護自身合法權(quán)益,在一審案件中,當事人明知法院判案不公而不以上訴為途徑維護自己的權(quán)益,為了規(guī)避法律以申請再審的途徑維護自身的利益,這就代表當事人主動放棄了自身的上訴權(quán),這種放棄保護自身合法權(quán)益的做法,從本質(zhì)上就違背了法律賦予其申請再審的基本權(quán)利。其怠于行使自身的上訴權(quán),那么對于其基于上訴權(quán)而產(chǎn)生的申請再審權(quán)也就不應(yīng)當予以保障。因此綜上所述應(yīng)當注意,當事人的再審申請權(quán)應(yīng)當建立在其已經(jīng)積極履行了自身的上訴權(quán)的基礎(chǔ)上,但不排除有些當事人并非由于自身主觀原因而不提起上訴,對于這些人主觀上沒有規(guī)避法律意圖的人,可以不要求其必須行使其上訴權(quán)后方能獲得申請再審的權(quán)利,這也符合民事再審程序一次終局的要求,并不違背我國二審終審的審判制度。
雖然我們倡導(dǎo)應(yīng)當堅持民事再審一次終局的原則,但是并不是沒有變通空間的,對于某些在全國內(nèi)影響較大的案件等特殊案件,可以不受此原則的限制,具體什么類型的案件還需要立法去進行進一步的規(guī)定,但最多不應(yīng)該超過兩次。這對維護我國的司法權(quán)威,和二審終審的審判制度有著重要的意義。
五、結(jié)語
縱觀我國的民事再審程序,不難發(fā)現(xiàn)雖然現(xiàn)行的《民事訴訟法》對民事再審程序中出現(xiàn)的“申訴難”和“再審難”問題有了一定的調(diào)整,但是在實踐中還存在著諸多的法律問題需要我們?nèi)ヒ灰唤獯稹A硗夤P者認為,我國的民事再審程序,缺乏對當事人自由處分權(quán)的保護,把重點再審啟動的權(quán)利都放在了法院和檢察院身上,這樣做顯然是不合理的,這就使得檢察院和法院在行使再審啟動職權(quán)時,可能會干預(yù)公民的實體權(quán)利,這種安排本就違背了司法中立和不告不理原則,與民事再審權(quán)利的救濟性特征也是相違背的,更容易侵害到當事人的合法權(quán)益。所以我國現(xiàn)今的民事再審程序應(yīng)當重點將提起再審的權(quán)利放到當事人身上,建立以當事人為中心,法院檢察院為輔助,以再審之訴方式提起再審的民事再審程序。這對于維護我國司法權(quán)威,加強司法建設(shè)和發(fā)展有重要意義。
參考文獻:
[1]常怡:《民事訴訟法學(xué)》(第二版),中國政法大學(xué)出版社,2010年版。
[2]袁亞偉:“我國民事再審制度的改革與完善”, 《蘭州大學(xué)》,2008年04期。
[3]趙麗萍:“論我國民事審判監(jiān)督程序的改進與完善”,《山東大學(xué)》,2012年04期。
[4]韓靜茹:“錯位與回歸:民事再審制度至反思——以民事程序體系的新發(fā)展為背景”,《現(xiàn)代法學(xué)》,2013年第2期。
[5]冉君怡:“民事再審制度之比較研究——兼論我國審判監(jiān)督制度改革”,《中國海洋大學(xué)》,2009年02期。
[6]陳勇:“論我國民事再審制度的缺陷及完善”,《吉林大學(xué)》,2007年05期。
[7]翟慧溟:“我國民事再審程序啟動主體探析”,《太原科技大學(xué)》,2013年。
[8]候惠珍:“完善我國民事再審程序的理性思考”, 《法制博覽》,2012年07期。
[9]趙安龍:“論民事再審程序”,《中國政法大學(xué)》,2004年03期。
[10]王曉東:“論申請再審制度的改革與完善”,《鄭州大學(xué)》,2004年04期。
[11]鄧成明:“構(gòu)建民事再審之訴論”,《華東政法學(xué)院》,2005年01期。
[12]李光旭:“論我國民事再審程序之重構(gòu)”,《四川大學(xué)》,2005年02期。
[13]杜聞:“民事再審程序研究”,《中國政法大學(xué)》,2005 年05期。
[14]田海:“我國民事再審制度改革研究”,《西北大學(xué)》,2006年03期。
[15]俞成琪:“民事再審制度的理論反思及重構(gòu)”,《安徽大學(xué)》,2006年04期。
[16]田光耀:“重構(gòu)我國民事再審制度之理性思考”,《湘潭大學(xué)》,2006年05期。
[17]羅麗娟:“我國民事再審啟動機制研究”,《南昌大學(xué)》,2007年06期。
[18]宋宜長:“我國民事再審程序啟動機制的反思與重構(gòu)”,《山東大學(xué)》,2008年07期。
[19]田春陽:“我國民事再審程序研究”,《吉林大學(xué)》,2009年07期。
[20]夏陽:“民事訴訟再審事由研究”,《廣西民族大學(xué)》,2012年03期。
[21]栗闖:“論我國民事再審制度之完善”,《鄭州大學(xué)》,2012年04期。
[22]李浩:“論民事再審程序啟動的訴權(quán)化改造_兼析_關(guān)于修改_民事訴訟法_的決定_第49條”,《法律科學(xué)》,2012年06期。
[23]崔卉鵬:“民事再審事由研究”,《黑龍江大學(xué)》,2012年07期。
[24]粟曉露:“我國民事再審程序的反思與重構(gòu)”,《云南大學(xué)》,2013年01期。
[25]關(guān)晶:“民事再審程序與既判力價值衡平的研究”,《吉林大學(xué)》,2013年0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