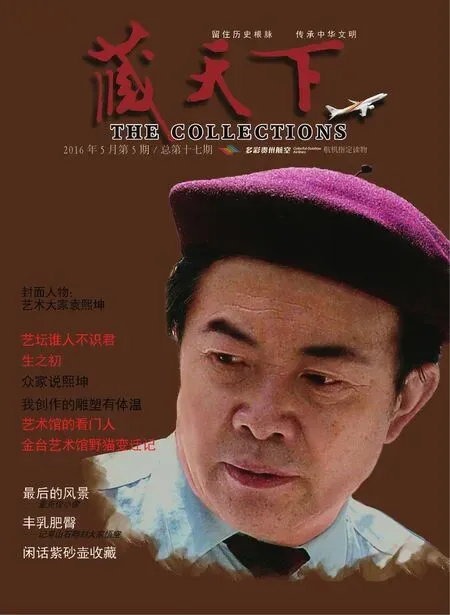人 物·PEOPLE
?
人 物·PEOPLE
吳冠中:我一生只看重三個人 魯迅、梵高和妻子

吳冠中是當代中國不可多得的美術大家,更是不可多得的散文大家,藝術與文學是他終生的情人。他所有的成就都是源自真情,對親人、對土地、對祖國、對人民的真情。
吳冠中17歲的時候投身藝術,他不顧父親的強烈反對,從浙江大學工科轉學到杭州藝專學畫。1946年吳冠中留學法國巴黎,4年后,他徘徊于西方藝術與祖國之間,最終決定回國。回國后,吳冠中經人推薦到中央美術學院任教,當時的院長是徐悲鴻。那個時候,為政治服務的寫實主義正是中國畫界的主流。吳冠中“橫站”在東西之間,兩面受敵,格外吃力。他先后在中央美院、清華大學建筑系和中央工藝美院幾個院校間輾轉,始終處于邊緣。從上個世紀50年代末開始,吳冠中被迫開始轉而嘗試風景畫。當時幾乎沒有人畫風景,認為不能為政治服務。但吳冠中不管,他要探尋自己藝術的獨木橋,這卻成為他后來一生的藝術道路。
此后不斷地為興趣而畫,吳冠中的精神正可用他后來的一本書名來概括:“要藝術不要命”。1960年,他不顧生命危險,將西藏雪域高原的圣潔、神秘呈現在了畫布上。吳冠中開始漸漸步入人們的視野。
學畫之后,吳冠中有些惋惜。齊白石利用花鳥草蟲創造了獨特的美,提高了社會的審美功能,但這比之魯迅的社會功能,其分量就有太大的差異了。他晚年感到自己步了繪畫大師們的后塵,有違年輕時想步魯迅后塵的初衷,并感到美術的能量不如文學。一百個齊白石不如一個魯迅對社會的作用大。
后吳冠中自己認為,我一生只看重三個人:魯迅、梵高和妻子。魯迅給我方向給我精神,梵高給我性格給我獨特,而妻子則成全我一生的夢想,平凡,善良,美。我感覺以后我散文的讀者肯定比欣賞我的畫的人要多,因為我的終生情人是文學。
蔡國強:對藝術的態度要有個人主張
1957年生于福建泉州的蔡國強,20年前旅居紐約后,他頻繁活躍于世界各地,曾獲威尼斯雙年展金獅獎。他最為公眾熟知的一件作品當屬2008年北京奧運會開幕式上,用焰火組成的29個大腳印,沿著中軸線一路“踏”進奧運場館。
2016年3月14日,蔡國強策展的《藝術怎么樣?來自中國的當代藝術》在卡塔爾多哈Al Riwaq展覽館展出。這場構思三年的展覽展示了15位在中國大陸出生的藝術家作品。與此相配合的是一本記錄參展藝術作品,參與此次展覽藝術家觀點的書和一部記錄蔡國強策展過程的紀錄片。紀錄片中,“你的獨到之處是什么?”是蔡國強屢屢提及的一個問題。事實上,他甚至將這個問題提給了幾乎所有出現在本次展覽中的中國藝術家。對此,他表示,對藝術的態度和觀念,藝術方法的切入點,以及藝術所表現的問題,要有個人的主張。一件作品也許只是談自己的性經歷或失戀的痛苦,但它也能形成真正個人主義的多元。
他認為,展覽不是對中國當代藝術的回顧,或是試圖給予歸納現象和趨勢,更非體現何為中國特色的創造力,而是回歸藝術家個人的創造力。這個創造力不僅是在美術,是面對著文化,也面對著整個國家,都要有創造力,都要提出一個新的理念。

藝術家對藝術的態度要有個人的主張。他也在書中寫過“好的藝術家似大自然,有自己的春夏秋冬和生、長、收、藏。能吸收艱苦,也能淡定富貴。能保持童真、一直熱愛藝術,這是恩賜。做一個創造美的天才,將調皮好玩、幻想好奇融入人類的精神長河,可以帶給別人,首先是自己無限的意外驚喜。”這樣的話聽起來既說教又普通乏味,可是藝術家還要什么呢?
竇唯:畫畫是一種修行

竇唯是在1990年開始突然對畫畫特別感興趣的。他并不在乎畫畫的好壞,主要是喜歡畫畫的過程。在1997年6月30日,他自己開著車去龍慶峽,把車停在龍慶峽旁邊的古城村,坐在車子里,開始畫這個村子。就是那天他突然覺得自己喜歡畫畫完全是喜歡畫畫的過程。
竇唯最喜歡的就是走到哪兒畫到哪兒,前幾年夏天,竇唯去陽朔的時候,有一天下著小雨,是特別柔的那種小雨,他走在柏油馬路上,旁邊是農田,不遠處的天空下映襯著山,他一時興起,拿起畫筆就在雨中開始作畫了。
竇唯自己認為,他更奢望自己能夠追求那些古時的圣人先賢,他們的生活可能非常平淡,他們的一切也不是那么的光輝燦爛,但是他們有一份從容和自在。畫畫是除開他音樂之外的修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