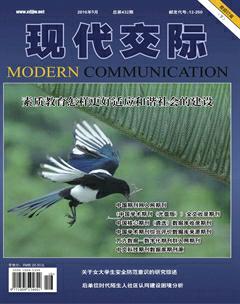論后現代主義批判的思想邏輯
曹宇鵬
[摘要]后現代主義批判主要來自新左派學術陣營,他們堅持反后現代主義的立場具有“家族相似性”。我們可以將其看作是某種格瓦拉的幽靈在當代的重現。
[關鍵詞]后現代 后現代主義 思想邏輯
[中圖分類號]I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5349(2016)10-0086-02
20世紀90年代,后現代主義逐漸在中國學術界興起,并隨著大量的譯著的出版面世,人們也對這種新的學術主張有了感覺。但要從新鮮感提升到學術立場,顯然需要時間和觀念的沉淀過程。而要將一種新異的經驗感受與學術知識結合并使人們能夠根據這種學術模式去理解周遭的事態,那么新的知識總要盡力去說明生活經驗與此理論認識的相關性。從這個視角看20世紀90年代構建起來的后現代主義學術知識,其局限性在于它不合時宜地突出了自己的知識分子話語特性,或許這正是其在很長一段時間受人詬病的要因。隨著整個20世紀80年代造就的啟蒙氛圍的消退,人們投入到廣闊的市場社會并確立起一種實用主義的信念。以精英主義的姿態來標舉其學術話語的權威性便具有一種自我諷刺的意味。在西方,后現代論者反對現代性論述的理據,就是認定后者虛構了一種“也許是世上最后的神秘祭儀”。齊格蒙特·鮑曼將后現代主義概念的出現并挑戰現代理性文明的變化,看作是知識分子作為“立法者的沒落”的征兆。而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我國文化轉型時期被橫移到中國的后現代主義論述卻以精英話語的方式,被引進、研究和流傳。
在20世紀90年代,后現代主義批判主要來自新左派學術陣營。論題的展開,與學術界對現代性和后現代性的關系、新左派與自由主義的論爭,尤其是全球化反思和文化工業批判等問題密切相關。后現代主義批判作為一個文化闡釋對象來看,正是由上述的話語關系的爭論和交鋒編織而成的機體。汪暉的《當代中國的思想狀況與現代性問題》一文,勾勒了一系列的主義話語,從“三種馬克思主義”到啟蒙主義和新啟蒙主義、新權威主義、儒教資本主義一直到后現代主義,等等。由于汪暉的新左派學術思想傾向,他對泛濫于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后現代主義給予了理性批駁。歸納其觀點,大致如下:一是后現代之興起的時代原因在于20世紀80年代的啟蒙無望之后向西方轉向的態度;二是直接拿來西方后現代主義,以為可以作為批判中國新啟蒙主義的思想武器;三是以大眾文化的名義將人民的需要欲望化,由此為資本主義的市場體制提供意識形態上的合法根據。[1]上述批評所立足的,似也可概括出幾個根據:一是將對后現代主義的批判一概歸到對資本主義總的批判根據上,這是新左派的思維方式;二是以中國當代的思想任務來說,反后現代主義的理性根據在于20世紀80年代的中國思想界的啟蒙話語所提出的任務尚未完成也就談不上終結,“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已經造就了它自己的代言人,啟蒙知識分子作為價值創造者的角色正面對深刻的挑戰”。這種挑戰又因為啟蒙知識分子在諸多范疇上的含混性而導致“中國的所謂后現代主義者正是利用了這種含混,把西方的后現代主義直接作為批判中國新啟蒙主義的武器”。后一個根據來自批判者對自我歷史處境的清醒和自知的反思。
后現代主義批判在汪暉的現代論述中是不能輕描淡寫的問題,他在多處都涉及到這一話題,可見其重視的程度。[2]當然,不只汪暉堅持反后現代主義的立場,新左派另一些學者在此問題上可以說都有“家族相似性”。甘陽1992年就曾在芝加哥寫成《中國的后現代》一文,以極具調侃意味的筆調對20世紀90年代初中國的“毛澤東熱”作了后現代式解讀。文章的一個重要意圖是隱含著對西方思想界通行的政治意識形態批評的思維方式的質疑,但更明顯而直接的意趣是,順手操起在西方已炙手可熱的后現代剃刀,來解剖那時正在發芽中的中國后現代文化(整篇文章讀來充滿了一種我姑且用來玩味的術語“啟蒙主義的童貞”氣息[3])。我在這里提到這篇冠以后現代之名的文章,主要目的是提醒人們,一個思想者的批判形象未必總是令人畏懼的,他也會在思想工作的邊緣閑談,這是再正常不過的。但另一新左派學者韓毓海不負干將之名,我們讀他的《當代中國的啟蒙主義遺產》一文時,不難被尖銳的理性批判激情所觸動。尤其是在批判全球化背景下后現代主義論述的形成時,他認為:“當代中國曇花一現的所謂后現代思潮則顯示了新啟蒙陣營向右的方面的瓦解。十分特殊的僅僅是,后現代思潮完全缺乏對于市場社會及其文化的切實分析與思考,缺乏當代條件下資本、市場活動與文化活動之間的關系的反思,也絲毫沒有涉及在全球化背景下國家政策的改變和國家角色的調整等基本問題。恰恰相反,中國的后現代思潮作為市場的樂觀主義者比人文精神論者有過之而無不及。這表現在:后現代把人文精神的討論視為精英主義的敘事,用解構的策略為商業和消費主義文化提供合法性論證,顯示出更為空前的擁抱市場的熱望。實際上,中國的后現代思潮既沒有任何社會分析能力,也沒有任何社會批判的對象,只不過是按照現代性的當下性邏輯,不得不需要一個對立面來確立自身以便進行文化生產。中國的后現代本身就是市場消費主義文化的一部分,他動用傳媒進行炒作的方式為此后的文化、理論的商業化生產提供了仿效的范本。”[4]之所以不耽冗長地整段摘錄韓毓海的觀點,一方面是力圖再現其批判的激情,更主要的是為了呈現那個具有連貫性的批判中國后現代主義的思想氣質的“家族相似”。應該說,這是新左派在20世紀90年代登臺并閃爍其思想的深沉道義光芒最具代表性的氣質。這一支出沒于90年代思想叢林的小股隊伍,亦如他們排演的《切·格瓦拉》一劇所帶來的異乎尋常的轟動一般,我們可以將他們看作是某種格瓦拉的幽靈在當代的重現。
但這些幽靈只能飄蕩在有限的思維王國,相對于有限的思維,后現代消費市場仿佛無比的巨大、能動、自由,它所帶給身體選擇享樂的目的讓人無法抵御。以消費文化而論,齊格蒙特·鮑曼甚至借用了“消費者合作社”這一概念來隱喻今天這個已經全球化了的后現代消費社會的文化本質:消費者合作社的一個基本特征是,它特別贊成這一選擇,在共同努力中,每個成員的份額都是由其消費而非生產貢獻所決定。成員消費得多,其在合作社的共同財產中的份額就越大。因此,是分配與占有——而非生產——是合作社活動的軸心。[5]“消費者合作”這一概念,對于中國人來說,不會顯得陌生。齊格蒙特·鮑曼盡管是用敘述語氣闡釋這個后現代消費社會的產生和生活事實,但還是激起我們無盡的妄想,甚至以為他在本質上已經與共產主義生活重合了。后現代消費社會等同于共產主義社會的想象浮現出來。但正如齊格蒙特·鮑曼所言,“消費者合作社”這一形象的比喻,“在此,人們能觀察到發生于主要文化領域的個體生活的過程。選擇的自由有賴于大量的可能性;然而,它將是一個虛假的自由,因為它否認了這樣的權利:賦予一種可能性先于其他可能性——縮減了大量的機會,關閉與拒絕了其他的可能性——換言之,它完全減少或取消了選擇。猶如只要這些符號是無意義的,它們就充滿了各種機會,所以,自由選擇的本質是努力廢除選擇。”[6]對于進入20世紀90年代之后的文化趨向,可以說最具后現代生活典型的事件,莫不與齊格蒙特·鮑曼描摹和揭示的“消費者合作社”生存形態相仿。自由與對自由的廢除、大量的自由與機會的縮減、生活的符號化與價值的斷裂都構成一個奇怪的解釋循環。歷史進步到今天,我們似乎獲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盡可能享受著世界上能食用的一切美味,有更多的時間可供我們娛樂,但有一點也許被遺忘了,這一點卻是不經由我們選擇的:在消費者取代個體的出發點上,個體被先行置換,“而且,商品化進程同時也是消費者的誕生行為”。進一步問,人們放棄個體選擇自由,他們就能夠如齊格蒙特·鮑曼所說的,同時也獲得最多的自由嗎?如果上述提問是身處20世紀90年代以來后現代生活的歷史代價的話,我們還能心甘情愿地認定,在巨大的商品化歷史和同樣巨大的主體思維邏輯之間,二者是渾然一體的統一關系嗎?具體的問題是:在后現代消費社會里,人們還具備相應的思維能力,可以區分歷史中的偶然性以及隱蔽的必然性形式嗎?
我們似乎必須承認,作為歷史現實的后現代消費生活形式已經來臨了,它并非在價值上給出的判斷,而是舉出一個生活事實。在市場經濟已深刻體制化的前提下,它的到來具有了經濟基礎;在大眾生活已以消費為指針的前提下,它的到來具有了文化基礎;在思想觀念的多樣化以及零散化的前提下,它的到來具有了思想基礎;在藝術再無美丑之別的迷惑下,它的到來具有了感性基礎。當然,這一切似乎都是在不知不覺中發生的,好像歷史扮演了潘多拉的角色,打開了手中的盒子。于是新左派憎惡從漂亮盒子里飛出來的災禍,但這一切都已發生。他們從根本上堅持后現代與中國問題的不相關性。而通過張旭東的一系列論述,我們看到了站在新左派立場上從另一種視角對在20世紀90年代興起的后現代主義與中國文化的相關性的肯定論述,它的理論價值是提高了新左派對后現代主義批判的論述水平。張旭東在發表于《讀書》上的兩篇文章《重返80年代》和《后現代主義與當代中國》集中表述了張旭東對中國后現代思想的反思傾向。這種傾向是一種將對自由主義的批判與重構一種新的后現代歷史感受的敘事結合起來的反思,與前述新左派學者的批判立場是內在溝通的。
【參考文獻】
[1]汪暉.死火重溫[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65-70.
[2]汪暉,余國良.九十年代的“后學”論爭[M].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8.
[3]甘陽.將錯就錯[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2:76-79.
[4]韓毓海.當代中國的啟蒙主義遺產[J].文藝理論與批評,2002(05):38.
[5][6]齊格蒙特·鮑曼.后現代性及其缺陷[M].上海:學林出版社,2002:165-166、169.
責任編輯:張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