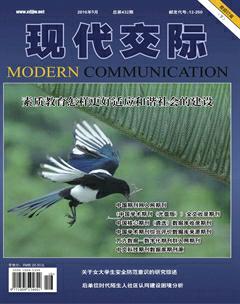論《刑法修正案九》對第二百八十條的修改
廖良壽
[摘要]刑法是我們的基本法,關乎我們公民的切身利益,對于刑法修正案九對第二百八十條的修改駕駛證不應該規定在刑法中,同時從法益的解釋機能等方面提出了一些關于該法條的完善,嚴格明確和限制嚴重的情形的處理,增加明知與真實身份不相符合的情形而使用的處罰。
[關鍵詞]罪責刑 相適應 謙抑性 完善
[中圖分類號]D92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5349(2016)10-0027-02
我們在這次的刑法修正案意見征求稿中可以看到不少的一些法條的修改,而這些修改之處是我們應該重點關注的地方。從理論和實踐的角度來看待它的變動,以期尋找到一個合理合法的刑法規定,這里我重點關注的是和我們生活息息相關的、平時生活就接觸到的各種證件問題。主要修改的地方有法條對適用對象和適用情形的修改。下面我對這一法條的修改進行自己的分析。
一、刪除該法條中的“駕駛證”
對于駕駛證是否應該包含于該犯罪的對象中,亦或是動用刑罰來懲罰偽造、變造、買賣駕駛證以及在依照國家規定應當提供真實身份證的活動中,使用偽造、變造的行為,筆者認為必須基于刑法的基本內容回答以下三個問題:第一,什么樣的情況下可以動用刑罰來規制某一類行為?第二,刑罰是否具有萬能性?在其他手段能遏制和解決問題的情況下,有無必要動用刑罰這一社會控制的最后手段?第三,刑罰權發動的我們是否應該考慮清楚它具有合理性的根據?如果答案是肯定,則應當入刑,反之則不應當。
對于這一法條的駕駛證問題,筆者的回答是否定的,具體分析如下:
從刑罰手段的不可替代性來看,上述相關的關于駕駛證的行為可以通過刑法以外的治理手段來抑止,并非刑罰不可。在治安處罰等方面可以進行完善,但是不應該放到刑法當中,不是靠增設個新罪就可以解決的。交由其他的法律部門來規范會收到更加好的社會效果,實現成本收益的最大化。
從處罰的實效性來看,以刑罰制裁上述相關的駕駛證行為未必能收到實效。增設新罪的目的是要保護駕駛證的社會公共信用,但目的的正當性不能證明手段的正當性。一種新的東西沒有得到很好的論證,就簡單粗暴地加入刑法,認為只有刑罰才能起到良好的效果,這顯然過于自我感覺良好了,沒有考慮到定罪量刑的問題。國家制定一項法律要對其進行“成本—效益”分析。將上述駕駛證行為定為犯罪行為后,在執法和司法環節必然耗費大量的社會成本,這樣的立法實效性是較差的。正如英國的法學家彼德·斯坦所說:“法律所存在的價值,并不僅限于秩序、公平和個人自由三種,許多法律規范首先是以實用性、以獲得最大效益為基礎的。”刑罰不是解決相關駕駛證問題的必要手段和首要目標。所以這一法條中對于駕駛證的相關規定沒有達到處罰的實效性,是不適宜規定在刑法當中的。
刑法具有謙抑性,刑法應該是被動的而不是主動的,刑法的界限應該是收縮的而不是向外主動擴張的。事物都具有兩面性,要用得恰如其分,趨利避害。刑法作為基本法,應該是對抗違法行為的最后一道防線,在其他控制手段或者說法律規范能夠發揮其應有的價值,對這一行為能夠進行很好的規范時,我們就不應該簡單、粗暴地對這一行為采取刑事制裁手段。法律部分要各司其位,否則就會越位,就會造成司法的混亂。刑法干預范圍首先就是要收縮,通過罪之謙抑與刑之謙抑這兩種實現途徑對刑法進行有效控制。沒有其他制裁力量可以代替刑法;運用刑罰不會導致禁止對社會有利的行為。顯然關于駕駛證就不應該入刑,駕駛證已經成為大眾生活的一部分,不是說成為生活的一部分就必然要上升到刑法來規范,而是要考慮到其他的社會規范能否進行有效的規制,這一行為對社會造成了怎么樣的危害,這一危害在社會上造成什么樣的影響等等因素。一般的駕駛證不當行為已經有相關的行政治安條例進行規制,我們不能把行政執法的不足拋給刑法來規制,我們不能指望刑法來代替行政執法。刑法是要有效控制的,而不是萬能的,不能因為目的的正當性而去破壞社會的公平性。不是所有的社會行為納入到了刑法之中都會運行得很好,歷史已經給了我們答案,我們要做的是疏而導之,而不是堵塞它,以高壓來壓制。
二、添加“情節嚴重的”限制
罪責刑相適應原則,要求我們做到犯罪、刑事責任和刑罰三者之間的平衡,三者要相互對應,而不是罪重的輕罰,罪輕的重罰。罪輕的刑事責任就輕,所承擔的刑罰相應也就輕。為此,刑法分則具體設置罪名的各個法條之間對罪責刑的規定要統一平衡,實現罪重和罪輕之間的合理劃分。做到:其一,有罪當罰,無罪不罰。即刑罰只能施于犯罪的人,不能罰及無辜,無犯罪即無刑罰。其二,輕罪輕罰,重罪重罰。其三,一罪一罰,數罪并罰。其四,同罪同罰,罪罰相當。即同一性質、情節相近的犯罪,應當處以輕重相近的刑罰。其五,刑罰的性質應當與犯罪的性質相適應。
刑罰不僅應當在量上,而且應當在形式上與犯罪相均衡,并認為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做到罪責刑相適應。在這一法條中我們要明確相關情節,雖然我們不能窮盡所有的情況,但是常見的情況必須界定清楚,規定好具體的嚴重情形,只有這樣我們的法律才具有該有的權威,實現預見性,而不是單純依靠發生了之后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來判決,也不是簡單地以一個兜底的形式來規定。這樣會造成許多不應有的危害:在刑法的整體上打亂了統一性,司法機關無法可依,造成一行為全國判決都不一樣,受到的刑罰也完全不一樣,造成司法資源的浪費,損害刑法的公開性、公平性和約束性,達不到立法應有的目的和效果,不能促使公民去認真的遵守和執行,損害司法權威。
三、增加明知與真實身份不相符合而使用的情形
在刑法第二百八十條后增加:“明知居民身份證、護照等證件中的身份與真實身份不符合而使用的,處拘役或者管制,并處或者單處罰金。”
刑法的修改要考慮社會實際,對社會的實際中的問題進行規制,從而解決好社會實際當中的問題。針對當前社會誠信缺失,欺詐等背信行為多發,社會危害嚴重的實際情況,要發揮刑法對公民行為價值取向的引領作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九)(草案)》對該條款進行修改的目的就是要解決社會誠信的問題。我們可以從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九)(草案)》的說明中看到這點。立法者針對在應當提供真實身份的社會活動中,卻使用偽造變造的居民身份證件、護照等證件的行為,規定其為犯罪,其目的之一就是要保護居民身份證、護照等證件的社會公共信用。該罪的保護法益即為居民身份證、護照等證件的社會公共信用。對該法條進行細致分析,我們可以發現該條規定情形應當涵括兩類行為:一是一個國家對身份證、護照和其他證件制作的專有權利,即“國家規定必須有活動的身份證明文件,如身份證,護照和其他文件的變化”,這是指“依照國家規定應當提供居民身份證、護照等證件的活動中,使用偽造、變造的居民身份證、護照等證件”的行為。二是侵害居民身份證、護照等證件的身份真實性之行為,這是指“明知居民身份證、護照等證件中的身份與真實身份不符合而使用”的行為。
在我國目前的相關法律法規中可以看出,我國居民身份證、護照等證件的制作機關只能是國家相關機關,其管理也是國家的相關機關,只有這樣的證件才能表明公民的真實身份。只要我們細化這類證件具備的社會公共信用就不難發現其具有兩方面:其一,公眾認為國家對相關證件的制作具有專有權,相信這類證件為國家所制作,并且是專屬制作;其二,國家的專屬制作權使得社會大眾相信這類證件是具有唯一性,對公民身份的描述具備真實性,即這類證件的身份真實性。以上任何一方面被侵害,這類證件的社會公共信用就受到侵害。比如,行為人使用偽造的身份證,讓社會大眾相信這是國家制造的身份證,就侵害了國家對身份證具有的專屬制作權;再比如,行為人使用他人的身份證,讓社會大眾相信這是其本人的身份證,就侵害了身份證的身份真實性。以上任何一種情況,都致使身份證的社會公共信用受到侵害。
我們可以看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九)(草案)》規定的犯罪之保護法益是居民身份證、護照等證件的社會公共信用,這一條就有兩個問題:第一,其下第一款的用語“在依照國家規定應當提供真實身份的活動中”欠妥。因為這一用語暗示該罪的保護法益是居民身份證、護照等證件的身份真實性,而不是完整的社會公共信用。這會造成一種不合理情形:行為人使用的假身份證如果反映了其真實身份,并沒有侵害身份證的身份真實性,卻因符合“使用偽造、變造的身份證”的構成要件,也成立犯罪,這就喪失了法益的解釋機能,導致構成要件擴大化。第二,沒有規定“明知居民身份證、護照等證件中的身份與真實身份不符合而使用”的行為。這類行為包括兩種情形:其一,國家有關機關制作的居民身份證、護照等證件中的身份與行為人的身份不符合,行為人明知而使用;其二,使用他人的居民身份證、護照等證件。這類行為也侵害了居民身份證、護照等證件的身份真實性,卻因不符合“使用偽造、變造的居民身份證、護照等證件”的構成要件,不能成立犯罪,忽略了對居民身份證、護照等證件的身份真實性的保護,也導致構成要件限縮化。這顯然是與我們的立法背道而馳的。
四、結語
刑法的修改必須慎重,通過理論和實踐的論證來規定,做到應然和實然的統一,只有這樣我們的刑法才會具有頑強的生命力和權威性。所以我覺得刑法對于第二百八十這一條文的修改,應該刪除駕駛證,添加情節嚴重的限制和增加明知相關證件與真實身份不相符而使用的情形。
【參考文獻】
[1]馬克昌主編.近代西方刑法學說史略[M].中國檢察出版社,1996.
[2]陳興良.刑法哲學[M].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2.
[3]銘暄.論刑事責任[J].中國人民大學學報,1988(02).
[4]趙秉志,吳振興主編.刑法學通論[M].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
[5]肖介清.刑法真空與刑法泛化[J].刑法學研究新視野,1995.
[6]貝卡里亞.論犯罪與刑罰[M].西南政法學院出版社,1980.
責任編輯:楊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