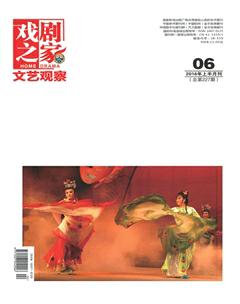元雜劇中的神仙道化劇
【摘 要】神仙道化劇的產(chǎn)生與底層文士的不平之鳴有關(guān)。劇中的儒生其實既有用世之意,也有避禍之心,劇中主要宣揚神仙的超然生活、抒發(fā)隱士隱逸之樂,當然也有消極厭世的成分。
【關(guān)鍵詞】神仙道化;不平之鳴;用世;避禍;超然閑適
中圖分類號:J827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7-0125(2016)06-0035-01
朱權(quán)在《太和正音譜》中對元雜劇題材進行了“雜劇十二科”分類,并把“神仙道化”類置于首位,他的分類中神仙道化和隱居樂道是分開的,而當今許多人都把隱居樂道類歸入神仙道化劇范疇內(nèi),本文所舉的作品都在此范疇內(nèi)。
一、不平之鳴
神仙道化劇的產(chǎn)生與底層文士的不平之鳴有關(guān)。《錄鬼簿·后序》中說:“文以紀傳,曲以吊古,……。鬼簿之作,非無用之事也。大梁鐘君,名嗣成,……,累試于有司,命不克遇;從吏則有司不能辟,亦不屑就。故其胸中耿耿者,借此為喻,實為己而發(fā)也。”①說明鐘嗣成著其《錄鬼簿》實則是抒發(fā)胸中不平之氣。李開先在《張小山小令序》中寫道:“夫以是人而居卑秩,宜其歌曲多不平之鳴,然亦不但小山,如關(guān)漢卿乃太醫(yī)院尹,馬致遠為江浙行省務(wù)官,鄭德輝杭州路吏,……中州人每每沉抑下僚,志不獲展。”②此是李開先引胡侍《真珠船·元曲》中的話,李、胡皆認為元劇興盛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劇作家的“不平之鳴”,此主張是承司馬遷的“發(fā)憤著書”和韓愈的“不平則鳴”說。他們何不曾有儒家濟世救民之志,但是在元朝的統(tǒng)治下,集體性的悲劇命運便來了,儒生地位一落千丈,科舉考試中斷七八十年,“學(xué)而優(yōu)則仕”的路徑被打斷,再加上蒙古統(tǒng)治者實行的民族歧視政策,漢人、南人地位之卑賤,即使為官,也是久年沉居下僚,很難升遷,成為高官的更是寥寥無幾,有志不獲騁,所以或隱居丘壑山林,或浪跡于市井,或找到一種精神寄托,來抒發(fā)自己的不平之氣。
二、用世之意,避禍之心
“學(xué)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這是元代儒生士子們的心聲。即使在這神仙道化劇中,儒生的形象到處可見,如馬致遠《太華山陳摶高臥》中道士陳摶本隱居在太華山,但是見五代動蕩局面殺伐不斷,百姓生靈涂炭,于是出山到長安集市上賣卦,專門等待未來天子趙匡胤的到來,欲為其指點迷津、出謀劃策。山中隱士也如此關(guān)心帝王功業(yè)。況且陳摶本就是儒生,雜劇第二折開頭,陳摶就唱道:“我往常讀書求進身,學(xué)劍隨時混,讀書匡社稷,學(xué)劍定乾坤。豪氣凌云,心志如伊尹。本待交六合入并吞,伐天下不義諸侯,救數(shù)百載生靈萬民。”如宮天挺《嚴子陵垂釣七里灘》中,嚴子陵也是歌頌,第三折【四煞】:“為民樂業(yè)在家內(nèi)居,為農(nóng)的欣然在壟上耕,從你為君社稷安,盜賊息,狼煙靜。九層春露都恩到,兩鬢秋霜何足星。百姓每家家慶,慶道是民安國泰,法正官清。”這種境界,何曾不是儒士通過輔佐君主而達到的太平治世。另外,嚴子陵又說:“你也不是我的君,我也不是你的卿”,讓人覺得有孟子的“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
然而,在仕與隱、入世的得失問題上,儒家知識分子何嘗沒有心理矛盾?無論怎樣,文士還是有避禍之心的,《嚴子陵垂釣七里灘》中嚴子陵唱道:“觀了些成敗興亡閱了些今古,浪淘金千古風(fēng)流人物……”。同樣是以史為鑒,后來又說:“重呵止不過些俸祿,輕呵但抹著滅了九族。”當皇帝劉秀作書邀請嚴子陵到宮中來時,出于禮節(jié),嚴子陵索禮一賀,但到了朝廷中,他小心翼翼,如履薄冰。伴君如伴虎,這何嘗不是曾經(jīng)為官的士人普遍的心理,嚴子陵最終還是跳出了十萬丈風(fēng)波是非海。
三、贊美神仙道化生活,抒發(fā)超然閑適之樂
神仙道化劇中,無論是神仙,還是隱居樂道之人,無不宣揚神仙生活之美好、隱逸生活之超然自在,這其實亦包含著劇作家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對自由人生的追求。如《太華山陳摶高臥》中:“身安靜域蟬初蛻,夢繞南華蝶正飛。臥一榻清風(fēng),看一輪明月,蓋一片白云,枕一塊頑石。”總之,既有抒寫常人的自得恬淡的田園生活之樂,也有神仙般的超然飄逸,那些失其志、命運否、沉抑下僚、志不獲展的儒家士子,寓意于此,維劇是作,未為不可。
注釋:
①中國戲曲研究院.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二)[M].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59.138.
②蔡景康.明代文論選[M].北京: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1993.147.
參考文獻:
[1]徐沁君.新校元刊雜劇三十種[M].北京:中華書局,1980.
[2]中國戲曲研究院.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M].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59.
[3]蔡景康.明代文論選[M].北京: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1993.
[4]袁行霈.中國文學(xué)史(第三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5]王亞偉.馬致遠神仙道化劇研究[D].桂林:廣西師范大學(xué),2014.
作者簡介:
路朝棟(1991-),男,山西師范大學(xué)戲劇與影視學(xué)院2014級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戲劇戲曲學(xu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