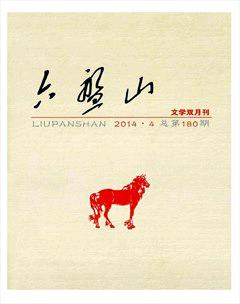山里人
劉國君
一
車子一過馬兒溝,就看見一座連一座的山了。
山其實不大,走進去你看到的是一座連著一座,一層隔著一層,蜿蜒起伏,層層相連,沒有華山的高聳,也沒有泰山的雄偉,只是一片被溝壑縱橫了的黃土坡。
在黃土坡的深處有一個扭結陜甘寧三省的小山村。村子不大,埋在群山里,一條條溝畔旁都住著幾戶人家。黃色的窯面,黃色的院墻,黃色的土地,只有窯門前的幾株綠樹才映出了一線生機。
這里是被歲月封閉著的一個天地,重疊又重疊的峻嶺,曾經阻塞了山里山外的信息,也收藏了山里人的酸甜苦辣。一灣又一灣的溝壑,曾經流淌了山里人的生活,也飄逝了山里人單調而又悠長的日子。
這村叫打虎店。這里曾經有過無數只野狼,野狼與野兔、黃羊以及山里人相處了許久許久,孱弱的野兔和黃羊用生命維系了一方土地的和諧。一日,一只餓虎闖進了這里,吞噬了野兔,吞噬了黃羊,吞噬了山里人家圈養的山羊。餓虎解除了饑餓,卻惹惱了山里人,四周八鄰成群結伙在火把的照耀下,驚跑了野狼、嚇呆了黃羊、藏匿了野兔,擊斃了那只域外游來的餓虎。這個從沒有大號的山村有了打虎店這一村名。
這個故事演繹了無數的版本,經過無數人的傳播飄得很遠很遠。而真正地名的來歷卻一直藏在打虎店人的心里,那是打虎店遠逝的輝煌。
宋夏之爭緣由很多,但有一項就是爭奪古鹽州的鹽。夏據興慶,占宥州,扼環州,把持鹽州鹽湖,而多少年憑借鹽湖食鹽生存的鹽州人,車拉驢馱地背著食鹽,躲過西夏兵丁的看守,避開官道的盤查,從鹽湖畔,到芨芨壕,從紅柳溝進山,沿著一條曲折蜿蜒的溝壑向南路,向西峰塬上伸去。精明的打虎店人望著腳下走過的一隊隊商旅,他們也看到了賺錢的商機,在那肘形的溝彎里,在商旅們走過的商道旁掛起趙家車馬店、張家車馬店的招牌。店不大,只有幾孔土窯,每孔窯里只有一盤燒得熱乎乎的土炕,不管是南來北往的,不管是騾子是馬,統統請了進來。大伙擠在一起海闊天空,神吹胡諞,飲酒賭博,洽談生意,把個窯頂抬得熱烘烘的。于是,這條山道成了鹽馬古道,這里的客店成了搭伙店。千百年來,從這客店里走出了鹽州城里最富有的鹽商,也飄出了鹽商們風花雪月的韻事。
歷史為這個從沒有大號的山村封了搭伙店這一村名。
無論是打虎店還是搭伙店,早已經沒有人關心這個符號式的名稱了。因為它偏僻,走進它時道路曲折,多少年山外的人把這里的人一直和愚昧連在了一起,就連和他們一溝相隔的村民們都稱他們是山里人。
二
山里人的日子,清苦而又漫長。清晨,晨暉映紅群山,喜鵲和麻雀把山里人喚醒了,山里人在太陽升上來之前就爬了起來,吆喝上牲口,扛著犁出了門。牧羊人把羊放出欄圈,一路的咩咩聲撒在晨霧繚繞的山道上。
等到太陽從東邊的山里爬出來,磕磕碰碰地翻過一座又一座大山,山里人已經犁完了一塊地,坐在地頭一邊歇緩,一邊張望著村里的人家。女人們起來,還沒有洗把臉,把揉散了的頭發束起來,就端起簸箕煨起炕來,接著,窯畔上響起了“咕,碌碌”的喚雞聲,聲音急切而悠長,等雞兒跑來了,撒上一把玉米或糜子,望著自己喂養的雞叼來刨去地吃食,女人的心里也是樂滋滋的。
山里的地沒有一塊是平的。多么好的農耕機械在這里都無法使用。一開春,幾乎所有的男人做著一樣的事情:套上一對牲口,手里拿著個鞭子,吆喝著犁過一行一行的黃土地,看著從犁鏵尖子滾過的一坨坨黃土,山里人蹲在地上捧起一把放在鼻子下面嗅一嗅,用自己皴裂的手用力捏在一起,心里盤算著地里的墑情適合種植什么。山里人是靠天吃飯的,雨水就是他們的糧倉,雨水足,糧倉滿。就在看墑的時候,牲口也停了下來,趁機歇緩一陣。中午時分,牲口乏了,男人也乏了,估摸著女人在家里把飯已經做好了,男人們吆著牲口,唱著自己都說不清楚的小調,搖搖擺擺地回去了。
一個長長的午覺后,等到下午時分,山里人搖搖晃晃地又來到他們的地里,這一去,直到黃昏,晚風拍打著樹葉,鳥兒嘰喳著歸林,山村的土窯頂上升起縷縷炊煙和叆叇的霧靄匯在一起的時候,勞累了一天的山里人,在蒙朧而神秘的暮色中,踏著山道上潮濕的夜露,慢悠悠地向村子里走去。
山里人的日子就這樣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地流過,山里人也從山里娃長到山里爺,一代一代地繁衍傳承。山里人的夜生活也是平淡的。月明星稀,山里的天是蔚藍的,山里的夜是靜謐的。吃過晚飯,勤快的男人叫上自己的婆姨或娃娃給牲畜鍘些草,或干些并不覺得辛苦的碎活,這樣比干坐著還愜意。活干完了,點上一袋煙,美美地咂上幾口,長長地舒一口氣,一天的疲乏全吐了出去。
也有些在家里呆不住的男人們,吃過晚飯,望著月上樹梢,抖掉身上的土,再找個樹干或石碾子、石磨,脫掉衣服摔打幾下,彈掉衣服上的灰塵就開始走東家轉西家,趁著夜色帶來的蒙眬心境,在這月朗星疏的夜晚談天說地,或講點酸溜溜的故事,或是尋上幾個閑散的人到那家抿上幾盅。更有些不安生的,在村里,或是溜進臨近的村子里,會會自己的相好,敲敲寡婦家的門,做些不咸不淡韻事。這種事山里人給它起了一個通俗的名字:“串門子”。這個世界,有男人,有女人,就有男女關系,在這個偏遠的缺乏夜生活的地方,“串門子”已經成了填補心里寂寞的一種生活。
三
山有多高,水有多高,山里的溝雖在海拔近2000米的高原之上,溝里依舊流淌著溪流,那水很小,細細的,涓涓的,卻是那么有滋有味,情意綿綿地緩緩地流淌著。
一條羊腸小道馱進了山外的女人,馱出了山里的姑娘。山外的女人在這里發了芽,生了根,開了花,結了果,又肥沃了山里的土地;山里的男人在這里耕了地,撒了種,澆了水,留了種,也肥沃了這塊土地。山里的男人和女人們,用柔情和生命傳承了一代又一代的山里人。
山里的女人大都是從更深的山里流出來的,她們在脫掉嫁衣,換上從娘家帶來的幾件舊衣服時,便拾起在娘家學會的鍋碗瓢盆、針頭線腦等日常過日子的手藝時,她們又恢復了過去的靈性。
在人生長河中,歲月洗去了身上的稚嫩,孩童催生了身上的母性。山里的女人在大山中度過了一代又一代,歷經了一個又一個春秋,當山外的春風吹進山里的時候,山里的女人們開始蠢蠢欲動,她們開始在男人們的耳邊吹枕邊風。當綿綿情話浸軟了男人的耳根后,山里的女人就像溝里的水一樣,又緩緩地流向了村外。走出大山的女人,帶著幾分好奇,帶著幾分靦腆融入了山下的女人河中,時間一長,她們就和山下的女人一樣,融入在姹紫嫣紅的城鎮生活之中。
山里女人的愛恨剛柔相濟,綿里藏針。她們的心氣很高,卻又能夠著眼現實,關起門在家里,女人們口里總罵自己沒心肝的男人,會把男人對她不好的地方一件一件地數落個清清楚楚,尤其是發生男人晚上在外過夜的事情后,女人們也會摔碟子砸碗,也會哭鬧,也會嚷嚷著要離婚,但事過之后吃飯時還是忍不住往男人碗碟里夾菜。她們一邊喋喋不休地向男人抱怨自己的命有多么多么的苦,自家男人應該向誰誰誰的男人學習,一邊和別的女人炫耀自己的男人對自己是如何的體貼,對家庭是如何如何的盡職。這些女人們戀著男人,就像土炕連著鍋臺,一切都是那么自然,那么樸素
山里的女人是最辛苦的,她們不僅要在農忙時和丈夫一起春種秋收,平日里的農活也離不開他們。在家里,又是縫縫補補生兒育女,又是喂羊喂豬洗衣做飯,女人們便在這緊張而又單調的生活中度過一個又一個白天。生在大山里,扎根鄉野間,山里女人聰明能干,心靈手巧,扎花剪紙,剁面攤饃,樣樣在行,尤其是那一個個繡著花的荷包、鞋墊,每一個針腳都留下女人們無盡的情絲。
晚上,男人們走出了家門,家里就剩下了女人,女人們收拾完家務,坐在炕上看電視,手里還閑不住地拿著針線活,一邊看著電視里那些浪漫家庭的浪漫生活,一邊想著自己的心事,山里女人的心思永遠也猜不透。
四
打虎店的人住在交界處,趕集的地方很多,可以在陜西趕,可以在寧夏趕,還可以繞個彎到甘肅去。后洼村的集市是每個農歷逢“八”的日子。這一天,山里人早早地起床收拾好要賣的,想好要買的東西,騎上摩托車,三五成群,翻幾座山, 拐幾道彎,把自家的羊羔、羊皮捎了出來,換回一些日用物品。山里人趕集的目的更多的是出去散散心,男人們找幾個朋友喝上幾口,扯扯閑話。女人們想出去看看世道,看看新潮的服裝。
也還有一些或男人或女人們想走出去看看人,山里的男人、女人的面孔他們已經太熟悉了,想出去瞧瞧新的面孔,也不為別的,解個心癮罷了。回去后,把見到的、聽到的加工加工,當作一個新的故事演繹了出去。那種渴望,那種嫉妒,那種無奈全部通過故事宣泄出去。
世事在悄然中起著變化。如今山里人聽故事的渠道多了,電視機里講的都是山里人很少接觸的新鮮事,可新鮮事聽得多了也就不新鮮了。最重要的是山里人和城里的距離越拉越近了,哪家山里人沒有幾個在城里工作的親戚,哪家山里人沒有幾個在城里上學、打工、上班的人?尤其是那些年輕人一個一個地往外奔,孩子長到十六七,能考上高中、大學的自不必說,他們有自己的理想,那些連初中都念不好的,也是一離開校門就飛出了大山。還有那些結婚生子后的年輕人,等到孩子剛學會舉步的時候,也是急猴猴地領著老婆孩子走了出去,他們在山里窩了半輩子,想給孩子尋找一個讀書上學的良好環境,翻下山租間房子,先不管怎么吃喝,就學著城里人的樣子,過起了城里人的日子。
留下的山里人依舊過著艱辛而樸實的日子。
直到有一天,大山突然被一輛輛各式各樣的汽車震醒,山村的梁坡溝底都豎起了一座座鉆探的井架時,山村的寧靜被打破了,山村的羊腸小路被修成了寬闊的車道,山村一天一個變化,山里人也一天一個變化。山里人才知道千百年來,他們就睡在錢堆子上面,只不過厚厚的黃土擋住了他們的眼睛。石油大開發,山里人種慣了蕎麥、山芋的黃土地里冒出了黑乎乎的石油。過去年產值百十來元的貧瘠地,天天不間斷地噴出黑色的金子。山里人的地被占了,山里人的路修寬了,山里人在村邊建起了小食堂,開起了小賣部,不出村就有了打工的地方,山里的褲兜里漸漸地鼓脹了起來。那些急猴猴領著老婆孩子出山的人,又回轉了回來,那些說不上婆姨夜里瞅著窯頂睡不著的光棍們,從山外領來了一個又一個俊俏的媳婦。山里人的生活發生了徹底的變化,唯一不變的是山里人待人還是那么實誠、厚道,還是會把心窩子的話亮開嗓子告訴你。
春天的樹枝上抽出了嫩芽,夏天的胡麻綻開了藍花,秋天的山坡被季節染黃、染紅,冬天的落雪迎來了春風,山里人的四季變化明顯,山里人的日子多姿多彩。在正月二十三的晚上,多年來燒柴困難的山里人終于能奢侈地點起一大團柴火,幾聲爆竹炸去了去年的不快和晦氣,一團烈火燃起了新的希望。山里人,把火花揚到了夜空,那繽紛的色彩包含著山里人新的期盼,新的夢想。這期盼、這夢想,讓山里人度過了一個又一個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