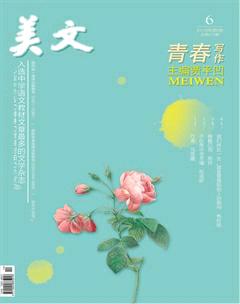文學是一臺探照燈
安黎
在某種程度上,文學和繪畫有其共通的一面,那就是皆執著于為人畫像。畫家用的是畫筆,而作家用的是鋼筆或鍵盤;繪畫用畫面說話,文學用文字表達。然而,繪畫和文學,畢竟萌發于不同的藝術根系,決定了兩者之間必然既有交織,又有分叉。畫面比起文字,更直觀,更具象;也更狹小,更局促,受限于尺寸之間,止步于表皮之淺,難免顯得過于以點帶面了。文學沒有繪畫那么一目了然,卻更委婉,更含蓄,更深邃,更博大。繪畫是一盞聚光燈,而文學則是一臺探照燈,能洞穿人目力無法抵達的角落,能發現潛伏與隱匿的“敵情”,并將人與物事的里里外外,像發掘古墓那般,壇壇罐罐地掏挖出來。也就是說,文學不但要展示西瓜之皮,還要展示西瓜之瓤;不但要給人畫像,還要給人畫魂。
文學反映的主體是人,事件也好,物件也罷,都不過是用以陪襯人烘托人的道具。然而,世間的人,無一是從石縫里蹦出來的,皆為父母所蘊育生養。人的生物學來源,決定了人與生俱來不可能是孤立的。哪怕一個自閉患者,整天閉門不出,不與外界產生任何關聯;但他與父母及其兄弟姐妹的血親關系,卻無論如何都無法斬斷和根除。站在這個角度審視,就會發現每個人其實都生活在枝枝蔓蔓里,相互牽掛著,糾纏著,難以金雞獨立。于是要書寫某一個人,就不能對縈繞其身勾連錯織的旁支,置若罔聞。這些旁支,構成了人生存網絡的背景圖案,是人所依賴,所倚重,又所煩厭的。人的選擇余地常常都是有限的,于是選擇就多為被動型的。基于此,才生發出了這樣或那樣的矛盾沖突:人與環境的抵觸,人與他人的沖突,人與自己的博弈——人最難的,恐怕就是克服自己的心理障礙,從而戰勝自己——集聚的矛盾若無法消解,很有可能演化為一幕幕帶有悲劇色彩的連續劇。生活中的精彩劇目,如果被悉數采擷,并得以呈現,就會轉化為文學中跌宕起伏的故事情節。在相當意義上,正是現實土壤里的劇烈沖突,才成就了敘事文本的豐饒與飽滿,也才使得文學世界由單調變得斑斕,由平面化變得立體化,由筆直平坦變得千折百回,由寡淡無味變得五味雜陳。有一句話叫“社會不幸詩人幸”,講的就是這個道理。社會的動亂,引來社會成員驚弓之鳥般地擔驚受怕,乃至于流離失所,家破人亡,但卻成批量地繁殖出層疊堆積的寫作素材。法國大革命是血腥的,暴力的,導致多少頭顱落地,多少鮮花凋零,但它促成了《悲慘世界》這部巨著的巍然高聳,也奠定了作者雨果的泰山屹立。
人是泥坯,環境是模具。泥塑的樣態,取決于模具,而不是泥坯。環境塑造著人,人也在抵抗著環境。人與環境博弈到末梢,大多是以人的敗北而收場。雞蛋身體脆弱,力量微小,一旦與石頭相遇,保全自己的辦法,就是節節退讓,繞道而行,不和石頭直接磕碰。同一片枝頭的樹葉,夏天翠綠,秋天枯黃,冬天飄落。人也一樣,遇到好的時代算是走運,遇到不好的時代算是倒霉。氣候的冷暖無常,催生出生命形態的千差萬別:有人開花結果,有人踩雷陣亡;有人生機盎然,有人自生自滅……文學的使命,就是將社會的潮起潮落與人生的花開花謝,予以吸食與消化,并以其獨特的方式吞吐出來。不要漠視與忽視那些微不足道的物事,因為任何一粒石子,都是地球的一部分;任何一個人,都是人類的一分子;任何一片云彩,都在孕育著雨水;任何一股微風,都在傳遞著風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