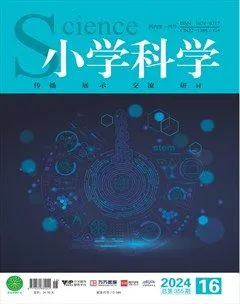培養科學思維的邏輯與創新
鐘文婉
〔摘? ? 要〕? 新課程改革背景下,核心素養被確立為課程修訂的基石及終極追求。面對新挑戰,教師迫切需要調整教學理念,改進教學策略,以期系統地培養學生的綜合素養與實踐創新力。基于此,本文圍繞核心素養下小學5~6年級科學教學的意義,對具體的教學策略進行剖析與研究,旨在為優化教學方式以及提升教學質量提供有意義的參考,進而助力學生全面發展。
〔關鍵詞〕? 核心素養;科學思維;邏輯與創新;教學策略
〔中圖分類號〕? G424? ? ? ? ? ? ? ? 〔文獻標識碼〕? A? ? ? ? ?〔文章編號〕? 1674-6317? ? (2024)? 16? ? 013-015
隨著教育教學理念的與時俱進,提升學生的科學核心素養已成為小學科學教學的重要使命之一。2022年版《義務教育科學課程標準》(以下簡稱“新課標”)對小學科學教學提出新的更高要求,強調在教授學科核心知識的同時,將科學觀念、科學思維、探究實踐及態度責任等核心素養的培養無縫融入教學過程,倡導策劃能引發學生興趣的科學活動,呵護并點燃他們對科學的好奇心,以驅動其內在科學學習動力。
一、核心素養下科學教學意義
(一)塑造面向未來的科學素養人才
科學素養不僅關乎個體的知識積累,更關乎其是否具備科學思維方式、探究實踐能力、態度責任意識等綜合素質。這些都是未來社會公民適應科技發展、參與科技創新、做出科學決策的必備素養。小學5~6年級正是學生科學素養形成的關鍵時期,通過核心素養導向的科學教學,能夠系統地培養學生的科學觀念、科學思維、探究實踐和態度責任,使其具備應對未來挑戰所需的科學素養,為國家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提供人才儲備。
(二)促進學生全面發展與個性化成長
核心素養下的科學教學不再是單純的知識灌輸,而是強調關注學生的核心素養、情感態度、三觀等多方面的培養。同時,教學模式還注重培養學生的創新精神、批判性思維、問題解決能力、團隊協作和溝通技巧等綜合素質。這些能力不僅在科學學習中至關重要,也是個人全面發展、終身學習的基礎,有利于強化學生的社會適應能力和競爭力。
(三)提升科學教學質量與教育公平
核心素養教學摒棄傳統的應試教育模式,強調知識的深度理解、遷移應用和問題解決,一定程度上能夠提升科學教學的質量與效果。所以,在科學課堂上,教師不再只是知識的傳遞者,而是學生學習的引導者、促進者和支持者。他們通過創設真實情境、設計探究任務、引導反思討論等方式,引導學生在實際操作和互動交流中深入理解和掌握科學知識,提高學習的積極性和主動性,進而提高學習效率。同時,核心素養教學關注教育公平,強調通過優質教育資源的均衡配置、教學方法的創新、評價方式的改革等手段,縮小城鄉、校際科學教育的差距,讓所有學生都能接受高質量的科學教育,享有公平的科學學習機會,從而促進教育公平和社會公正。
(四)培養科學公民與社會責任感
小學科學課堂在核心素養的指引下,往往更加注重科學與社會、環境、倫理等領域的關聯,引導學生關注科學的社會影響,培養他們尊重科學精神、遵守科研道德、關心社會熱點問題、具備科學決策能力,成長為具有社會責任感的科學公民。在科學課堂上,教師會引導學生探討科學與社會的關系,包括科技對環境的影響、科技倫理問題、科學與社會公正等,使學生認識到科學不僅是客觀的知識體系,更是與社會生活密切相關的力量。同時,教師還會引導學生參與社區服務、環保行動、科學普及等社會實踐,使他們能夠在實踐中體驗科學的價值,培養其社會責任感和公民意識。通過這樣的教學,學生將學會用科學的眼光看待世界,用科學的方法解決問題,用科學的態度對待生活,成為具有科學素養、社會責任感的現代公民。
二、核心素養下科學教學策略
小學科學核心素養包括科學觀念、科學思維、探究實踐及態度責任四個部分,以此為依據,結合教學內容,有序開展教學。
(一)深化科學觀念的理解與運用
所謂科學觀念,具體是指小學生對科學本質、科學知識體系以及科學與自然、社會、生活之間關系的基本認知與理解,通常涵蓋對科學基本概念、原理、規律的認識,以及對科學知識的結構化、系統化把握。具體包括:科學事實與概念理解、科學原理與規律認知、科學世界觀建構等。以“什么是能量”教學為例。第一,科學基本概念的理解。小學生應能理解能量是使物體運動或發生狀態變化的“能力”,是自然界中普遍存在的一個基本屬性,同時,能認識并列舉常見的能量形式,例如,動能(與物體運動有關)、勢能(與物體位置或形態有關)、聲能、光能、電能、磁能、熱能等,理解這些能量形式是能量的不同表現形態。第二,關于科學原理與規律認知。需要引導學生初步理解能量不能憑空產生或消失,只能從一種形式轉化為另一種形式,或者從一個物體轉移到另一個物體,但總量保持不變。這是能量領域的一個核心原理,有助于學生構建對能量轉化現象的科學認知框架。在教學過程匯總,通過具體事例(如燃燒產生熱能、水力發電、太陽能熱水器等),理解能量在不同形式間的轉化過程,體會能量守恒定律的實際應用。第三,科學知識的結構化、系統化把握。教師需要將各種能量形式組織成一個有序的知識網絡,明確不同能量形式之間的聯系與區別,理解能量在自然界中是作為一個整體存在和運作的。第四,引導學生理解能量轉化不是孤立發生的,而是通過一系列連續的過程實現的,如太陽能→植物光合作用→生物質能→燃燒產生熱能和光能等,幫助學生看到能量流動的全景。第五,科學與自然、社會、生活的關聯。幫助學生加深印象,認識到能量是驅動自然現象(包括風的吹動、水的流動、生物生長發育等)的重要因素,從而理解能量循環在生態系統中的重要作用。還可以了解能量的實際應用,包括煤、石油、天然氣、核能、可再生能源等,進而樹立節約能源、提高能源效率的意識,以此為基礎,進一步理解合理利用和開發能源對于實現社會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性。
(二)培養科學思維的邏輯與創新
關于科學思維的培養,主要是在教學中引導小學生運用科學方法和邏輯推理解決科學問題、解釋科學現象的能力,以及在面對新情境時進行批判性思考、創造性思考的傾向。結合小學5~6年級學生特征,科學思維應該包含邏輯推理、批判性思考、創造性思考等。在小學5~6年級小學科學“太陽系大家族”教學中,培養學生的科學思維應貫穿于整個教學過程。具體可以通過以下方面開展:第一,邏輯推理能力培養。引導學生從已知的地球知識出發,逐步構建太陽系的概念模型,明確太陽系的核心——太陽,以及圍繞太陽運動的八大行星、矮行星、小天體等組成部分。通過比較分析,讓學生理解各行星在大小、距離、運動軌道等方面的差異與相似性,以及這些差異與行星特性的關聯,例如,行星與太陽距離與表面溫度的關系。同時,通過實例或模擬演示,讓學生觀察并理解行星沿橢圓軌道繞太陽公轉、行星公轉周期與軌道半長軸的立方成比例等規律,歸納總結行星運動的共性特征,從而培養他們從現象到規律的邏輯推理能力。第二,批判性思考能力培養。要鼓勵學生對教材或教師提供的信息提出疑問,如為什么行星軌道呈橢圓形而非圓形?為什么冥王星被重新定義為矮行星?引導學生查找資料、觀看科普視頻或進行小實驗,對比不同來源的信息,學會鑒別信息的可靠性,培養對科學知識的批判態度。此外,可以嘗試設定一些關于太陽系的爭議性話題,比如,是否存在第九大行星、外星生命的可能性等,組織學生進行小組辯論或討論。通過聆聽不同觀點、分析證據、反駁論證,鍛煉學生的批判性思維,學會理性、公正地評估科學主張。第三,對創造性思考能力進行培養。教師可以布置開放式探究任務,如設計一個理想的太陽系模型,或者設想如果太陽系中某個參數發生變化(如地球離太陽更近或更遠),會對地球生命產生何種影響。鼓勵學生大膽設想、提出假設,培養他們發現問題、提出問題的能力。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可以嘗試開展模擬太陽系運動的實踐活動,如制作簡易太陽系模型、利用軟件模擬行星軌跡等。鼓勵學生在遵循科學原理的前提下,創新實驗方法、改進模型設計,甚至設計全新的探究方案,以展現他們的創造性思維。
(三)加強探究實踐的能力與操作
探究實踐是小學生親身參與科學研究的重要過程。通過觀察測量、實驗設計與實施以及科學交流與報告等環節,他們不僅能夠獲得科學知識和技能,還能培養科學探究精神和合作能力,為未來的科學學習奠定堅實基礎。例如,在教學“有趣的食物鏈”相關知識時,可以設計一系列探究實踐活動。第一,通過播放生態紀錄片片段、展示生態系統的圖片或講述生動的生物故事,引發學生對生物之間食物關系的好奇心。介紹食物鏈的概念,即生物間通過捕食與被捕食而形成的能量與物質傳遞鏈條。強調食物鏈的單向性(箭頭指向)和逐級遞減的特性。同時,解釋食物網是多個食物鏈相互交錯形成的復雜網絡,體現生態系統中生物間多樣且復雜的營養關系。第二,講解植物作為生態系統中的能量源頭,通過光合作用制造有機物。區分一級消費者(食草動物)、二級消費者(食肉動物)和三級消費者(頂級掠食者),以及它們在食物鏈中的位置。還可以闡述細菌、真菌等微生物及部分無脊椎動物如何分解有機殘體,將物質回歸環境。第三,開展探究實踐活動。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可以進行一次實地考察,組織學生到校園、公園或附近的自然環境中,觀察不同生物及其生存狀態,記錄可能的食物關系線索。在實踐過程中,指導學生查閱書籍、網絡資源,收集特定生態系統中生物間食物關系的實例。第四,引導學生嘗試構建食物鏈,以小組合作的形式開展。學生分組選擇一個生態系統(如森林、草原、濕地等),依據所收集的資料,繪制食物鏈圖,標明生產者、各級消費者及能量流動方向。各組展示并解釋自己繪制的食物鏈,討論其中的邏輯合理性,教師適時點撥、糾正。第五,鼓勵各組制作科學海報,清晰呈現所研究生態系統的食物鏈/網、生物角色、失誤率分析等內容。同時,教師還要鼓勵學生以小組形式進行口頭報告,詳細介紹探究過程、重要發現以及對自然界事物相互聯系的認識。
(四)強化態度責任的塑造與落實
對于小學生而言,態度責任主要是他們在科學學習過程中表現出的對科學的積極態度、對科學倫理的尊重以及對科學在社會、環境中的責任意識。具體包括:第一,科學態度。對科學保持好奇、求真、嚴謹、開放的態度,尊重科學證據,欣賞科學美感,對科學進步持有樂觀態度。第二,科學倫理。理解并遵守科學研究中的道德規范,如尊重生命、保護環境、誠實記錄數據、正確引用他人成果等。第三,社會責任。要求學生意識到科學知識與技術對社會、環境的影響,關注科學熱點問題,參與科學傳播、環保行動等,具備科學決策意識。同樣圍繞“有趣的食物鏈”相關知識,針對5~6年級學生的認知特點,可以進一步加強科學自然觀教育,使其擁有責任感。例如,引導學生反思食物鏈/網探究過程,討論生物間如何通過食物關系相互依賴、影響,以及這種聯系對生態系統穩定性的重要性。同時,討論人類活動(如過度捕撈、破壞棲息地等)如何改變食物鏈/網結構,導致失誤率變化,進而影響生態平衡,引導學生樹立保護生態環境的意識。
三、結語
綜上,小學科學核心素養涵蓋了科學知識的認知、科學思維的鍛煉、科學實踐的操作以及科學態度與責任的培養。在教學過程中,教師需要結合教學內容,通過合理的教學策略,塑造具有科學素養的小公民,為其終身學習和適應未來社會奠定基礎。
參考文獻
[1]張竹林.核心素養視域下小學科學學習活動設計思路及模型搭建[J].創新人才教育,2023(4):68-74.
[2]楊曉夢.新課標視域下中小學科學教育的發展方向與推進路徑[J].中小學管理,2023(6):30-33.
[3]鄭榕.新課改背景下小學科學課堂情境創設策略[J].亞太教育,2022(24):166-168.
[4]鐔淑芳.核心素養下農村小學科學趣味課堂的探究[J].農家參謀,2022(20):144-146.
[5]魏秀華.聚焦小學核心素養?優化小學科學課堂教學[J].大學,2021(S2):13-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