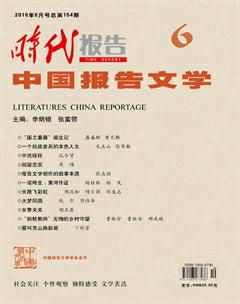凝眸陳忠實
4月29日早餐8時,我在韓城采風,餐桌上突然間就問閻安,陳忠實先生病情怎么樣了?他表情凝重地說,唉,不太好。接著,省作協(xié)的電話就來了通知:陳老,剛剛走了。
心是一緊。以后就是酸楚。幾次眼淚漲潮……
晚上,全國各地的作家電話短信微信奔騰而來。魯一班全體同學就發(fā)起送個花圈的建議。柳建偉說,先生生前喜愛鮮活,要送就送鮮花!班黨支委書記關仁山說,班長李西岳一定要把敬獻的挽幛辭聯(lián)寫好。經(jīng)白描常務副院長精心修改:“七旬早逝巨著一部雄筆擎日月,萬古不朽忠實二字鐵血映山河——魯迅文學院首屆高研班全體同學敬挽陳忠實先生”。推舉在西安的我和紅柯代表全體同學去靈堂敬獻花籃。4月30日上午9時,我倆莊重送上。
記得前年王蒙來西安講樓夢,他提出想看一個人。省委宣傳部副部長陳彥就讓我請。那時他已經(jīng)不去赴宴了。我很猶豫老人家的身體和意愿,但是一說,他即刻出發(fā)來了。兩位文壇老人交談甚歡,我也很欣慰。那時,他只是吃一點兒燒餅。這是我與先生最后的聚餐。沒想到這頓晚餐,就成為了與先生人生最后道別的豪宴。
以后,陸續(xù)聽到先生不希望別人看見他病了狀態(tài),我?guī)状渭s人想去看望,還是下不了見面會痛心讓先生無顏的決心。尊重,有時就是訣別。
記得那年,我們陜西省體育局召開新年茶話會,請專家們座談提高體育創(chuàng)造力的專題。要我去邀請陳忠實先生。那些頭銜——中國作協(xié)副主席,《延河》主編,小說《白鹿原》的作者,都是明亮撼人的。陳先生推辭。他說我可不懂體育啊。聽聽別人講那倒可以。我堅持著單位的邀請,陳忠實先生就到了位,也講了幾點與體育貼切的觀點,大家聽后都說他講得很好。作家一旦成名,就有許多邀請,最離譜的邀請就是吃飯。吃著吃著,老板就說了,您能給我這道菜做首詩歌,寫個散文嗎?那時感覺離譜,可是今年我去北京在大董烤鴨店,一切都已經(jīng)成為現(xiàn)實。每一道菜里都有優(yōu)美的名字和詩詞作伴,客人等待的杯杯異樣的雞尾酒……讓餐飲與藝術(shù)融為一體。
那年西安的六月已經(jīng)很熱。陳忠實先生滿面核桃紋暴露著滄桑,鶴發(fā)趨后,獨立在體育專家們中間。他專注的目光漫漫在薄霧狀的陽光里,抽著自帶粗壯濃烈的雪茄,右手一根食指點點戳戳在空中,向天也向前,吞云煙,噴吐霧,語氣秦腔濃重,語氣緩緩注注地說: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即使長壽也不過百年。所以,人,都要珍惜生命。珍惜生命的途徑有兩條。一是讓有限生命中的創(chuàng)造力充分表現(xiàn)出來;二是要保證生理肌能生命的健康活力,使具有創(chuàng)造意義的生命在肌能健康正常運轉(zhuǎn)的基礎上,把生命的可創(chuàng)造性發(fā)揮到最好……”
你看,陳忠實先生是不是講得很貼切,很好?
我認識陳忠實先生算很有緣分的事。一九九七年,西安出版社出了一本我的散文集《丈夫的名字叫西安》,西安市文聯(lián)作協(xié)創(chuàng)研室的朱文杰老師就對我說,有了專著,你就可以加入陜西省作協(xié)吧?去不去?
西安市文聯(lián)在城里西北方向蓮花寺的巷子里,陜西省作家協(xié)會在和平門城里東南方向的建國路上,我工作居住在和平門城外建西街,能到陜西省作協(xié)那真是臺階高了,距離又更近了,還是組織推薦。我很高興地答應道,好啊,我去!
朱文杰老師為我開了介紹信,并囑咐著讓我去找一位叫李秀娥的大姐。說她是省作協(xié)負責創(chuàng)聯(lián)工作的老同志,一個很好很開朗的人。
那是十二月一個飄著雪粒的早上。我?guī)е话鼤热挝徽埣伲屴k公室領導在介紹信上簽了字,蓋好章。八點半,我就騎自行車去了省作協(xié)。
作協(xié)沒人。小院子很安靜,各個房間都鎖著。在一個立了碑像古殿大堂樣的屋子臺階下,我支撐好自行車,站在一株小樹下搓手哈氣,等待李大姐。
“啊哈!嗯——唉,哎!你找誰呢?”忽然就有一個洪鐘般的聲音在我的頭頂上嗡嗡喝響,震動了整個由黃土、枯樹、小瓦房、青磚墻、干水池組合的寧靜小院兒。這是一個主人的聲音。
我剛才就這么進來了,并沒有給誰打過招呼。可我也沒看見人哪。我抱歉地回頭朝上一看,古殿大堂臺階花磚女兒墻后立著個半老漢,一手提著鐵壺,一手拎著根捅火條,很像我們家屬院的看門人。我就連忙回話說,嗷,我在等李秀娥呢。
外邊冷得很,她還得一會兒才能到呢,你先上屋里來等。喝些水,咋樣?
那好得很。我鎖了自行車,上臺階,進到廊廳東頭一間掛著脫線竹門簾的屋里。老漢已將大鐵爐的炭火捅得火苗紅紅藍藍白白的,感覺暖和多了。我感激地沖著好心的老漢笑笑。他說,來,你坐。我說,好。然后他就開始埋頭拆開許多堆在案桌上的雜志和信件,很多很多很多。
在《體育世界》雜志社,我曾負責通聯(lián)工作,每天也和這位老漢一樣,要拆許多的信件,分發(fā),回信,寄刊物……那時,我還很年輕,又好奇又努力,神速快捷,好像有鬼在催你。現(xiàn)在看老漢把年紀還要干這樣的繁瑣的活兒,就充滿同情地說,我來幫幫你吧?
“你幫不了。”他把一直很嚴肅的臉抬向我卻不看我只瞇眼看他自己手里的活兒,回答著我的話。邊看還邊問我:“你找秀娥,啥事么?”
“加入陜西省作協(xié)。”
他這才抬頭看我問,你叫啥?
“夏堅德。”
哦——他仿佛想起來了什么,說,那一天我還在晚報上看見介紹你了。還有篇文章,很有藝術(shù)性的。俄以為是個男人,沒想到是你呀。出咧個啥集子?啥?啥《丈夫是西安》的個集子,得是的?呀,那你厲害得很呀!全西安市都是你丈夫,你奏太歪咧么!啥時給俄也帶一本來看看。
我說,今天我?guī)砹耸尽R粫何宜湍阋槐尽?/p>
你,見過我嗎?我搖頭。他又指指一個信封的名字說,你認識他嗎?我看見“陳忠實收”幾個字。說,嗷,這人寫的《白鹿原》小說我讀過。可我不認識他,書里又沒有照片,封面就是畫了個穿棉襖的駝背老漢嘛。
老漢笑了。笑得很開心。他說,是這樣!啊,那你加入省作協(xié)是要先回去準備這么幾樣東西的。然后再來找秀娥。咋樣?老漢立時拿起一支粗筆在一張紙上用大大的柳體寫道:一、申請書;二、寫作簡歷;三、作品目錄和著作八九本。是供省作協(xié)討論研究的。
我看看他遞給我紙說,這好辦,我就在這兒寫。老漢說,你回去寫。我說我不回去,就在這里寫。他又說,你還是回單位去寫,還要蓋章子,還有著作呢。
我沒再理他。開始認真按那三點要求寫了三頁紙。然后,要膠水,要剪刀,要釘書機,在三頁上面貼上西安市作協(xié)推薦的介紹信,上面已經(jīng)有我們單位領導“同意!支持加入”的簽字及公章,然后,出門下臺階取書十本,送給老漢。我叮囑他說,剛好,你好人做到底。你幫我看看寫的這些行不行,別讓李秀娥大姐看了通不過。老漢笑笑搖搖頭說,我還沒見過這樣不聽人勸說的女子,你回吧,讓我好好看看。
他又說,你真不認識我?
我說現(xiàn)在咱們不就認識咧嗎。老漢低腦搖頭,然后嘿嘿嘿地笑起來,一會兒還哈哈哈地仰頭朗朗地大笑起來了。我一驚,再小心謹慎地問老漢,咦,你憑啥笑成這樣嘛?
“我就是陳忠實。”老漢洪鐘般的聲音很高。就像秦腔戲中小邊鼓噠噠、噠噠、噠噠噠地剛剛細碎著,突然“咣”地一聲鑼。一個英雄亮相,靜場,叫道:“陳,忠,實!”
我頓時愣住了。嚇住了。在我的印象中,這是一個很大很大的名字。
白色,一片白色。空白……我好像是沒魂似的一溜煙飛奔出陜西省作協(xié)的。因為以后什么也記不得了。許多次我回憶起這一段初遇的往事,每回憶到這里,腦子就是一片空白。一片糊涂云。遇見陳忠實老師在場時說道起來,他會補充,會敘述完整,但我還是記著這個空白的版本。
我那一怵溜飛也似的逃奔出陜西省作協(xié)后,就再也不敢妄想加入陜西省作協(xié)的事情了。不久,李秀娥老師電話里和風細雨地通知我去陜西省作協(xié)填表了。她說,你的申請已初步通過了。你得找兩個省作協(xié)的成員當介紹人。我說我不認識誰呀,那就您和陳忠實先生吧行不行?她說她可以,我很愿意。但陳忠實主席那里你要自己去說。我想想說,那好。
我去了。陳忠實老師在醫(yī)院剛做完胃切除,才一周,正靠躺在西安第四軍醫(yī)大學的高干單間病床上。看見我來,他就堅持要下床坐在小凳子上和我說話。我很猶豫。他連連問有啥事?我說沒事沒事。他又緊問一句,到底啥事?我就說我想請他當我的加入省作協(xié)介紹人。他說,這是件好事情嘛,我愿意!我就這樣有了在文學殿堂再上一個臺階的平臺。這是我的文學生命,我一直很珍視它。
二〇〇二年,經(jīng)陜西省作協(xié)黨組推薦,我到北京參加魯迅文學院全國中青年作家首期高研班學習。開學那天,常務副院長、《小草在歌唱》的作者雷抒雁老師堅持要點全體同學的名,四十九位同學,一一站起來答應。后來雷院長告訴我說,當時點名也很想看看陳忠實和賈平凹同時都極力推薦的夏堅德是個什么樣的人。之后,我又申請加入了中國作家協(xié)會,介紹人就是雷抒雁和陳忠實。朋友李芳泓女士曾千辛萬苦為我的表格在西安到處尋找到陳忠實先生,他欣然簽字。
記得曾有人請教詩人雷抒雁先生如何寫詩歌。雷抒雁說:“寫詩,如嬰兒的第一聲啼哭。是人最初那種很自然的呼吸。”我認為與人相識,也如呼吸一樣,自然最好。任何生命,都有在自然中生長的第一聲啼哭。自那美麗的第一聲“啊哈!嗯——唉,哎!你找誰呢?”這是一個關于文學的美麗開頭。之后,我們關于足球,關于朋友,關于書法,關于奧運會,關于寫作,關于誰扮演白嘉軒家的地主婆田小娥她媽,還有“蕎麥園”里關于白骨精和狐貍精……就有了太多的趣味、趣事。關于我的散文小說,評論家暢廣元曾在一次開會時問及陳忠實老師,他用了很簡潔的兩個字評論了我的作品:“別致!”
張山飛碟奪冠奧運時,我們曾一起去射擊場打過飛碟。在射擊場,陳忠實老師為陜西省著名的國家級優(yōu)秀射擊冠軍的教練芮青也寫下兩個大字:凝眸。人的生命非常短促,我們的人生態(tài)度就應當是這兩個最簡單又最有力量的字:凝眸。
我們曾一共走進公安為西安干警們講文學;
他曾推薦我去給省雜技團的劇目編寫詩意的故事、分場簡介;
在我不自信的時候,他總是用巨掌推我,用洪鐘般的聲音告訴我——你能行!
有人曾經(jīng)問我,什么樣的相逢最難忘。我想,那就是他她認識了你的文字。我因文學于先生相識,就是最好最難忘的緣分。
陳忠實先生一生忠誠文學。我相信:文字不會消亡,文學青春萬歲!
先生,歸去,依如他活著。
責任編輯/魏建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