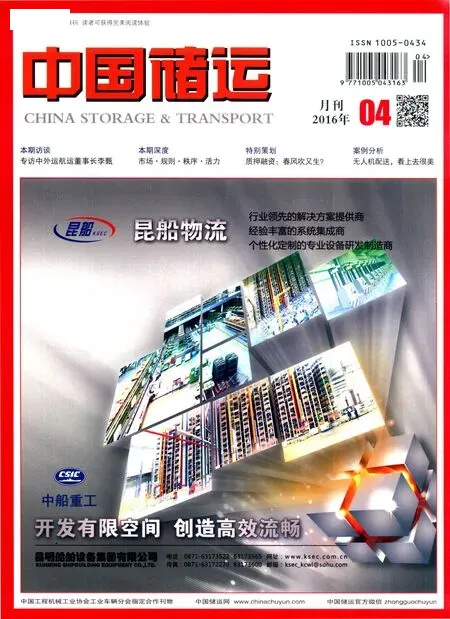把脈問診質押融資
——專訪中倉倉單服務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楊沁河
文/本刊記者 李靜宇
?
把脈問診質押融資
——專訪中倉倉單服務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楊沁河
文/本刊記者李靜宇

以動產融資監管為主要形式的物流金融,經歷20年的歷程,盛極一時。曾被譽為20世紀以來金融市場最重要、最有生命力的金融創新之一,很多大型國有物流企業紛紛搶灘該領域。但在上海鋼貿、青島港等融資風險事件出現以后,物流金融陷入了低谷,銀行業“談鋼色變”,國有物流企業逐漸退出了這個領域,業界驚呼:“質押”融資怎么了?
隨之而來的是質押融資業務的大幅縮減,更有這個行業對此業務的深刻反思,質押融資業務作為服務于所有中小企業、直接受益于物流業、制造業、銀行、現貨或期貨交易所、供應鏈企業和電商等眾多方面的一項服務產品,更是一個普惠實體商品經濟的基礎服務產品。那么,如何醫治質押融資這個疑難雜癥使其再現輝煌呢?為此,記者采訪了中倉倉單服務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楊沁河。
病癥:質押騙貸
近幾年來,物流金融始終處于跌宕起伏的狀態,物流企業在這個過程當中承受了非常大的風險和困難。楊總在接受采訪時指出,我國物流市場相比歐美市場在技術和信用體系上有較大的差別,同時,我國的司法實踐相比經濟運行還較落后,所以我國的“質押”融資業務一度出現了大的震蕩,這些事件險些將“質押”融資業務顛覆于泥潭之中。
中資銀行業前十幾年“流行”的動產質押監管模式在華外資銀行始終不接受,外資銀行僅接受法律結構清晰的合格品牌物流企業(外資為主)的倉單質押。而事實是,危害甚大的上海鋼貿融資事件和重復質押案例絕大多數采用的是動產質押監管模式,由于以鋼貿市場和比較低端的基地作為保管方,中遠中外運等大牌企業作為監管方一起“組合”運作,“從國際和產業發展長期視野來看,這是種過渡模式,本身就存在著根深蒂固的實物操作障礙和法律與技術障礙”。銀行為了開展具有重大市場價值的融資貿易,不得不接受這種現狀,而一旦經濟出現嚴重下滑,類似鋼貿事件等違約失信事件就會不可避免地發生,最終,物流和金融無疑成為最大的受損主體。
與之不同的是,青島港事件引發的有色金融虛假質押和重復質押連環案例絕大多數糾紛發生在提單轉換“質押清單”環節,物流企業用“入庫單”“質押清單”這些沒有中國合同法和物權法支持的習慣單據在低層次運行。

“對于這兩個轟動一時的事件,前者是動產質押監管出現了問題,后者是倉單質押出現了問題。”楊沁河介紹說,這兩種截然不同的操作模式產生的問題,暴露出倉儲能力、管理水平雙重能力的不足,更顯示交易所和中外銀行使用倉單、辨別倉單、處置倉單能力的不足。
而這一現象很大原因在于物流企業自身服務能力的不足。在楊總看來,中國物流市場的一大特點便是其分散性,作為一個分散的市場呈現出的是不足萬平方米的倉庫占據了大部分市場份額。
據初步統計,中國目前沒有任何一家大型倉儲企業或是物流企業倉庫的市場占有率超過2%,這種情況下出現兩個不足,一是銀行業最認可、倉儲業最基礎的倉單業務必須在第三方倉儲企業自管庫內開展,十幾年前中國市場獨立的第三方倉庫不足,導致銀行和貨主不得不使用一些比較低端的倉庫(主要是貨主倉庫),通過品牌物流企業的輸出監管來開展此項業務,“這些倉庫往往不是中儲或中外運這些大牌的物流企業的,更多的是一些以鋼貿市場作為倉庫,中儲或是中外運等品牌企業派出少量人員前去辦理‘輸出監管’業務。”楊沁河說,二是責任結構復雜且控制能力不足、質權效力有缺陷。這種模式在歐美市場是不存在的,而在我國卻是風靡一時,當市場發生變化后搶貨“強行出質”、拉攏監管員放水等違法行為便“常態化”了。貨主“主導場地”+低端倉儲商+品牌監管商的畸形模式,無奈配套復雜且個性化的“三方監管合同”,保管責任、信息服務責任、回購責任、擔保責任、場地權利、抵押關系、質押關系、善意第三人利益、權屬核定義務、價格變動核定義務、浮動質押效力、登記與否效力等交織,各方都在謀求推責別人、擺脫自己甚至渾水摸魚!
病因:信用體系缺失
十幾年前中國內資銀行業接受動產質押監管的模式,倉儲行業“勇于開展”這項業務的背景,從客觀條件看是當時第三方專業物流企業倉儲空間不足、技術能力和法律管理能力薄弱,屬于內資銀行和內資倉儲企業“無知者無畏”,“摸著石頭過河”的探索之舉。但經過十幾年中國物流和科技發展,目前第三方物流擁有的倉儲空間已經顯示過剩跡象,還有沒有必要在存在先天缺陷的老路上修補前行了呢?
事實是,相對于動產質押監管業務,倉單是一個比較穩妥、法律關系清晰、管理現場單純的業務,中國內地倉儲企業前十幾年倒是較少開展倉單質押這一業務,即使中儲這些大公司內部也只有上海、天津幾家子公司做過期貨交割倉,涉足過倉單的業務。
“在物流金融事件集中暴發過程中顯現出的物流企業和銀行雙重能力不足,規則與標準相對落后也是倉單業務發展的障礙。期貨交易所在十年前就用了‘標準倉單’”,但是那個‘標準倉單’僅僅覆蓋少數幾個產品,而且倉單要素非常少,只包含10個以內的要素。所以導致社會上‘非標倉單’嘗試做了很長時間。直到2014年7月1日,倉單格式規范的國家標準才出臺生效。所以說倉單標準建設這個過程長期是滯后的。”楊沁河介紹說。
據了解,倉單的具體業務流程,是在主合同包括銀行、倉儲企業、貨主企業簽署倉儲合同下開展,其中的條款明確規范貨物交付后開具的倉單以及倉單的用途、見倉單才能提貨等等要求。下面是預約交貨、安排入庫流程,其中包括清點貨品數量、稱重以及清點貨物的品牌和規格、確定貨位等內容。
在楊沁河看來,“倉單的技術難點是確定存貨的質量和規格,只要貨物的質量檢驗技術和朔源技術能夠支撐,專業倉儲企業能有效管理,那么它就可以提供倉單服務”。
對此,楊沁河介紹說:“過去大多數交易所自己在做倉單,而不是倉庫在做倉單,物流企業更沒有自身的倉單服務等系統。很多倉庫離開了交易所的系統支持,自己是不會做倉單的,因為大多數中國倉儲企業自己沒有技術做倉單。這種畸形狀況實際上導致了倉單責任集中承擔于少數幾家期貨交易所上。”
在“質押”融資一系列的事件爆發之后,業內人士指出,我國企業信用意識薄弱,而楊總卻表達了另外一種看法:“我并不認為中國市場的經營者本身在信用意識方面與歐美的企業存在多少先天性的差距,差距在于整個社會的信用體系、服務體系的支撐能力、健全程度;結果表現在較高信用的機構是否能受到較好的市場待遇,是否可以取得較好的經濟收益。”在楊總看來,目前我國信用體系建設方面差距明顯,倉儲企業自身信用的評價沒有社會化服務支持,出了監管質押案后,倉儲行業整體信用受損,以致我國的市場出現了一種“銀行不敢貸、企業的擔保不足”的狀況。
醫治:創新新模式
中國高信用國標倉單綜合服務是現階段物流企業與供應鏈金融相互結合的全新價值的模式,正如楊總所闡釋的:“中國高信用國標倉單綜合服務是以維護倉單交易、融資市場的便捷與安全為目標,為倉單業務的供需雙方提供認證、征信、保險等一攬子倉單基礎配套服務,它屬于高端專業公共服務。”
具備哪些要素和能力才能提供這樣既高端、專業又綜合性強的一攬子服務產品?在現有的倉單水平之下,已經做了哪些方面的創新升級呢?
“第一個重要的升級,就是我們將整體的這個倉單模式回歸到簡單倉儲保管模式,逐漸替代或降低動產質押監管這一過渡模式,逐漸替代或降低商品交易雙方直接頻繁實物交收的傳統模式,用公共交割倉單的模式來普惠所有現貨交易和電商市場。”楊沁河指出,中倉倉單這一項業務,就相當于把期貨倉單電子化標準化后推廣到現貨交易所,推廣到供應鏈公司和電商公司。
與此同時,中倉倉單對原有安全模式進行升級。“經過詳細地探索比較,我們決定徹底放棄紙質倉單,因為紙質的單據安全性差。目前我們就是采用電子匯票的技術體系來系統地做電子倉單的運行,用這種方式來保障倉單真實、可靠地在倉庫、持單機構、金融機構高效流動。”楊沁河介紹說。
金融產品各方最關心的是風險的管理,據調查,目前,中國即使最大的交易所其風險準備金也不過十幾億元,難以支撐現階段較大的交易量和風險。所以,長效的機制應該是使全行業升級為公共倉單,獨立的倉單認證體系、現代化的保險分散機制可以讓貨主和倉庫通過平常支付低成本保險金的方式,將風險轉移和分散到整個商品經營行業。
中倉倉單聯合中國人民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陽光保險集團等大型保險公司研發的專業國標倉單險,將保險實務中逐單實施的風險評估、風險定價、風險統計、投保操作等環節全部標準化、智能化、線上化,并提供了財產底層驗證和遠程視頻核保等技術支持,有效滿足了大量倉單快速生成、頻繁贖單的供應鏈融資交易需求和保險保障需求。
在一系列升級創新的背后,這個創新型服務的真正意義何在?對此,楊沁河介紹說:“通過倉單認證、倉單征信以及倉單保險等這些基礎性事務工作的逐一打磨,最終才體現出這項服務產品對整體物流和金融行業的基礎意義。”
楊沁河表示,“中倉的一個重要定位是發揮基礎作用,輔導一些真正講信用的倉儲企業會做倉單,而中倉、人保整個公共倉單服務機構獨立地評價它,給它承保,讓這家企業的倉單有技術和風險分散的支持,能夠為各家金融機構提供商品質押和交易服務。”“哪個企業具備條件做這種高信用國標倉單,我們就會把大量的銀行資源、保險資源和客戶資源推到這些倉庫里面去。”楊沁河說,結果就是,第一,是它有大量的客戶進來;第二,使它們省下了一系列的技術和法務研發投入;第三,中國頂級的第三方技術支持,能解決倉儲企業外部客戶物權憑證利益沖突和內部人作弊例如監守自盜的問題。
在采訪中記者了解到,這項業務已經開始在武漢、上海、深圳等地物流節點城市部署試點工作,有多家銀行和大型倉儲企業參與試點,楊沁河代表整個綜合服務團隊表示,將奉行“甘做中國物流信用服務基石”的信念,專注成為電子倉單領域的基礎服務機構,與社會各界共創、共建、共享順應行業發展的倉單新基礎、新規則、新機制。
之所以稱之為基礎性的綜合服務,一如楊沁河所講,“這不是哪一家貨主或是物流企業或是銀行所能承受的,而是需要一個公共的服務體系來支撐它,而中倉倉單協同中國金融認證中心、中國人保、中國檢驗認證等六家倉單基礎服務機構組建的“國家隊”正是實現了這樣幾種服務功能,一是技術上的集中研發,二是風險的長效識別和分散,三是對有利益沖突的部分引入獨立第三方的專業機制,四是全國性金融和物流節點的基礎服務支撐能力。
恰逢中國社會對供給側改革的共識,高信用國標倉單綜合服務的誕生,正是給中國物流和金融行業一個新的選擇,不是對原有動產質押監管模式的修補,而是呼應互聯網金融和電商交易的需求,將物流服務的供給升級到高信用國標電子倉單服務的模式,靠模式升級重樹中國物流行業信用,高標準支撐中國金融和流通升級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