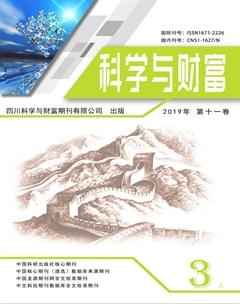新能源汽車維護與保養一體化教學形式探究
孔寧
摘 要:隨著環境污染與能源危機的日益嚴重,新能源汽車已經日益普及,新能源汽車和傳統燃油汽車專業在構造、原理和維修上都有著極大的不同,為了適應汽車行業發展需求,各職業院校汽修專業也逐步開設關于新能源汽車技術等順應行業發展、緊跟技術前沿的新課程。就此,本文分析了新能源汽車專業人才培養現狀,探究了職業院校新能源汽車維護與保養一體化教學形式,希望能為相關人員提供一些幫助。
關鍵詞:新能源汽車;維護與保養;一體化教學;教學探究
1新能源汽車專業人才培養現狀
1.1新能源汽車專業特點分析
現代化社會車行與汽車本身都是耗能較大的,然而在我國社會資源日益緊缺的情勢下,耗能較大的汽車行業與汽車本身需要面臨著重大的改革創新,因此,新能源汽車橫空出世。與傳統的汽車相比較,新時代下新型新能源汽車行業有著傳統汽車無法比擬的優勢,尤其體現在汽車的設計,新能源利用方面,盡管在汽車的基本構造和基礎知識方面與傳統汽車不想上下,但是單憑新能源汽車現狀優勢,對社會資源的利用就產生了較大的變化。在此環境下,眾職業院校應發揮企業教育優勢,制定完善的新能源汽車專業模塊化人才培養模式與計劃,基于市場需求前提下開展教育,為汽車行業改革建設培養專業的汽車人才。
1.2培育模式
從現代化職業院校汽車專業學院教學目標來說,培養傳統的汽車行業專業人才是汽車專業目標,要求學生具備傳統汽車相關理論知識;而從現代化需要的汽車專業人才來看,更看重的是汽車專業人才在實際崗位上的實踐能力。而如何提高學生實踐能力與相關的專業理論知識主要取決于職業院校對學生專業化與模塊化的人才培養,然而當前教師主要采用的教學方式是將理論基礎為主要教學內容,忽略了實際能力培養使得學生在社會崗位中無法盡快的順應崗位,與此同時,基于這種培養模式下,學生通常對實際企業的最新資訊不夠了解,對于新能源汽車相關知識,也不能真正接觸到,主要包括汽車配件和構造的了解。
1.3現階段職業院校新能源汽車專業培養模式問題分析
缺乏實踐教學的人才培養模式帶給學生的是對市場的迎合度不足現象,無法提高學生新能源汽車專業能力,并在學習層面也有相關的限制因素,導致社會相關行業的認可,不能及時獲取,因此在之后的就業階段問題層出不窮也是常見的事。其次,由于新能源汽車在當今時代下還處于發展階段,因此需要大量的相關研究促進其發展,所以職業院校新能源汽車專業學生需要不斷的與社會相交流,進而實現現代化新能源汽車資源情況了解。除此之外充分結合實際崗位,將書本上的知識靈活運用于實際崗位中有助于提高學生的創新能力,進而推動汽車行業建設,然而傳統的汽車專業教育模式忽略了實踐教育,對學生的就業率是一種降低的教育表現。
2新能源汽車維護與保養一體化教學形式
2.1一體化實訓室建設
新能源汽車在實踐運用中對電控,電池裝置的要求非常高,需要培養的學生具有非常好的團隊協作能力和綜合實踐運用能力。因此,通過對接企業,引進校企合作,在校內建成校企合作培訓機構,來完善新能源汽車專業實訓基地建設的同時,可以邀請企業優秀技術人員為學生和教師做專業的培訓和技術指導,提升學生的實踐應用能力。教師可以通過企業真實的維修、維護案例和項目開展任務式教學,充分調動學生的學習積極性,學生也可以去企業實習鍛煉,讓學生在進入社會之前已經有了充足的社會實踐經歷,對企業工作流程、管理制度更早的接軌,滿足企業對人才的需求。
2.2一體化教材編寫
《新能源汽車維護與保養》課程涉及新能源汽車高壓安全防護、如何操作新能源汽車、處理新能源汽車故障以及對純電動汽車和混合動力汽車的維護等。與傳統的內燃機汽車在維護與保養的作業相比,內容存在很大差異,尤其涉及高壓電路安全操作方面,傳統汽車的維護與保養的教材的內容并不能滿足該課程的要求,故很有必要針對《新能源汽車維護與保養》的課程進行教材編制、建設。在編寫教材時,須將實際工作項目引入到教材中,并在課堂教學的過程中實施,能夠嚴格的按照4S店以及維修廠的作業過程標準來訓練學生,從而實現課堂教學“教、學、做”的一體化。在進行教學工作時,可以運用多媒體技術,在網上查找與課程相關的視頻、圖片,操作教學設備,播放直觀立體的動畫,有利于喚起學生學習興趣,促使學生主動探究視頻中的理論知識和操作方法,進而調動起主動性,提升學生的安全意識,使學生以最佳的狀態探究學習專業知識,不再被動接受知識,學習中更積極更主動。
2.3一體化實訓課程設置
職業院校應該開展如下的實訓課,培養學生動手能力、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理論聯系實踐,其中包含純電動汽車構造與維修實訓、新能源汽車使用與維護、高壓防護以及電動汽車動力系統實訓。純電動汽車構造與維修實訓:其中電池實訓工作任務有電池的拆裝、更換;電池技術參數的測量和電池故障診斷。電機實訓工作任務包含電機的拆裝、更換;電機調速控制;電機技術參數測量;電機故障診斷與排除。電控系統實訓包含大三電、小三電及其它電控系統的結構認識、控制器的檢修、波形測量以及分析等。新能源汽車使用與維護:包含五個大的模塊,分別是新能源汽車駕駛與操作驅動系統維護、充電系統維護、輔助系統維護、直流充電樁使用和維護、交流流充電樁使用和維護。高壓防護:包含高壓安全的認識、檢測工具的使用、操作流程以及事故急救模擬等重要內容。電動汽車動力系統實訓:認識新能源電驅動傳動系統控制原理和驅動傳動系統主要零部件功能。熟悉新能源電驅動傳動系統各種狀態下邏輯控制關系,掌握電流,電壓,電機轉速,負載等參數變化規律;熟悉負載變化對驅動電機轉速影響;明確新能源高壓系統操作安全注意事項,學會高壓連接器插拔方法;熟悉新能源電驅動傳動系統故障現象,并根據邏輯控制關系,學會查找故障原因。
2.4一體化教師培養
隨著高職院校新能源汽車人才培養目標和培養方案的改革與創新,教師隊伍結構也需要相應的調整。因此,有必要建立一支專業的師資隊伍作為新能源汽車專業人才培養的堅實后盾。新能源汽車的發展歷程短、現實應用性強,要獲取最專業的教學資源,職業院校需要深入相關企業進行人才尋找,建立合作企業,聘請企業專業人才進行教學和教師培訓,并且遣教師進入企業進行學習進修,從而提升教師的能力、豐富其知識面,穩固知識結構。在現在師資隊伍進行培訓、學習、提高的同時,通過引進切實具有新能源汽車實際工作經驗的人員進入教師隊伍,從而達到改變教師結構、提高師資隊伍。這樣才能建立屬于自己的專業團隊,提升整個專業的師資水平。
結語:
總之,新能源汽車將會在今后逐漸普及開來,對相關技術人才的要求也就越來越高。基于維護與保養一體化的新能源汽車技術專業人才的培養是促進新能源汽車可持續發展的重要舉措,在實際的人才培養過程中,要健全課程體系,加強教師隊伍建設,完善新能源汽車專業理實一體化教材編寫,對接企業利用校企合作完善實訓基地建設,注重學生綜合實踐運用能力培養,進而培養出高技能、復合型新能源汽車技術專業人才。
參考文獻:
[1]吳凱.中職學校開設新能源汽車專業課程的教學研究[J].汽車與駕駛維修(維修版),2018(S1):58+60.
[2]周大翠,高東璇,王競.淺談高職院校新能源汽車專業課程與教學改革[J].課程教育研究,2018(24):19-20.
[3]馬劍.淺析新能源汽車人才培養[J].汽車維護與修理,2017(14):2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