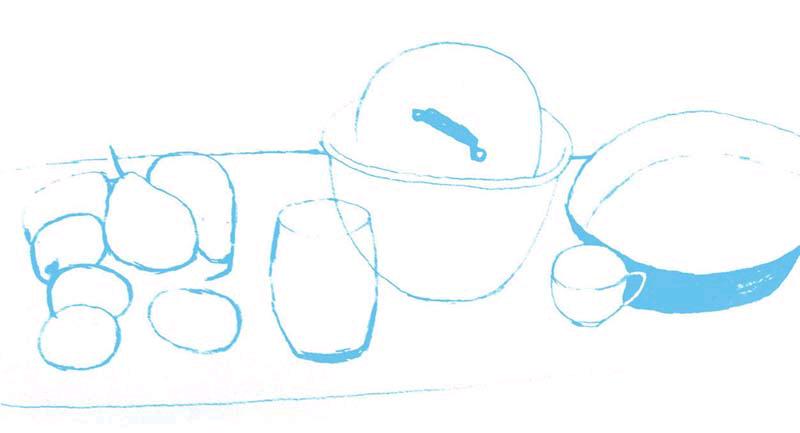浪漫的鬼魂
蔣子丹
我相信每一個懂得生活的人都會找到一種聲音與你的生命同在。那個聲音可能是蟬嘶或者鳥鳴,可能是高山流水或者空谷回聲,可能是雨打殘荷是雪落荒郊,可能是深巷里蒼涼的叫賣,是夜窗外孤寂的足音,我不能一一例舉,但我知道它們一定如同把把形狀各異的鑰匙,可以開啟我們各自塵封盈尺蛛網(wǎng)密布的記憶之門,讓往事幽深的溫泉沿著歲月的九曲長渠涓涓滲淌而出,如靄如煙如訴如泣如血如髓。當我們找到了它,就找回了童年之歡青春之夢,找回了故鄉(xiāng)之戀故人之情, 找到了自己,找到了生命里一切最值得珍愛的時光,于是我們說,我們懂得了生活。 現(xiàn)在我想告訴你,在一個風的夜里,我找到了那一個屬于我的聲音。
那夜我在燈下讀著這篇題為《腳印》的散文,讀到了一個有關(guān)鬼魂的浪漫傳說:人死了,他的鬼魂要把生前留下的腳印一個一個都揀起來。為此鬼魂要把生平走過的路再走一遍,車中船中, 橋上路上,縱然橋已坍,船已沉,路已翻修鋪上柏油,河岸已變成水壩,一旦鬼魂重到,他的腳 印自會一個一個浮上來。 這時候,風來了,海的風,帶著我曾經(jīng)陌生的氣息,從我不知該如何標志方向的遠方吹過來, 在窗前椰子樹寬大飄逸的樹葉上走過,留下陣陣綿長回應,一如旅人疲憊的嘆息。這是一個辛勞 的鬼魂,我毫不猶豫地想。它也許來自北極光照耀的寒冷地帶,穿越中原密實的青紗帳和江南水泊桅帆織出的網(wǎng),從都市的霓虹燈影里奪路而來,走過了太多的路,揀回了太多的腳印,也負載了太多的眷戀和愁思。在天涯海角的椰樹梢上,它躊躕不前了,生前的路或許已經(jīng)到了盡頭,末日之旅也到了盡頭。這是一個富有的鬼魂,它的路也長,腳印也多,所以眷戀多多愁也多多。我又想。它將要離去了,去喝孟婆的茶,用這滿筐滿簍的腳印作茶錢,買來忘卻的輕松。風更大了,椰子樹的回應更加綿長更像嘆息。
在我中年的一個夜里,我讀《腳印》,伴著這樣的風聲。 于是有風的聲響,從我童年的時光里吹來。那是一種細碎的輕響,當夏天的晚風吹臨古都北京林蔭道上的楊樹,滿樹心形的葉子一齊晃動起來。我們在樹下邊聽大孩子胡謅鬼的故事,又怕又興奮地擠成一堆。我在風的聲響里想象著鬼魂們穿著寬大的黑袍到處溜達,袍子邊蹭著樹葉子, 弄出這一陣聲響。在童年夏夜的風里,我與鬼魂在幻想中首次相遇,接受有關(guān)前生來世最初的啟蒙。楊樹的葉子響得歡實,鬼魂在我們的童年也好象無憂無慮,那時候,講鬼的聽鬼的誰也不知道,有朝一日你們自己的鬼魂還要回到這楊樹下邊,從黃葉底下拾回各自的腳印。 你們是一些都市里長大的孩子,你們過于貪戀父母的懷抱,過于習慣靜態(tài)的舒適,過于依賴生你長你的環(huán)境。你們只能在想象中體驗顛沛流離的經(jīng)歷,而你們的腳步卻一年年被束縛在稔熟的道路上,重復同一種頻率和節(jié)奏。你們害怕變化,害怕風吹草動,害怕失去已經(jīng)擁有的一切,害怕置身前景莫測的曲徑。你們尚可讀萬卷書卻無法行萬里路,當你們有一兩次心血來潮,想到外邊的世界去走一走的時候,總是被親切的輿論規(guī)勸阻止,進而被惡意的輿論指責為輕舉妄動異想天開。所以你們總是走不開行不動,當你們在爛熟于心的街市上往返,從不曾想到日后替你們拾揀腳印的鬼魂,路線怎么重復工作多么單調(diào)。 或許應該抱憾,你們這樣遲才知道了自己身后還負有如此令人激動的使命,否則你們肯定會將每一次腳步都邁得更加審慎更具美感更有深意。王鼎鈞先生可以對他的愛人宣告:在你家門外窗外后院的墻外,你的燈影所及你家梧桐的陰影所及,我的腳印一層鋪上一層,春夏秋冬千層萬層, 一旦全部涌出,恐怕高過我家的房頂。可是你們,你們不能。你們對身后令人激動的使命知之太晚,晚到只能袖手看王先生的鬼魂獨自收拾他的浪漫。你們的腳印夾雜在眾人的鞋轍中,匆匆, 淺淺,當你們果真要將來路再走上一遍的時候,甚至已經(jīng)無法辨認它們。你們說是春街席地的風沙已經(jīng)將它們吹去漫天飄散,如同吹散你們的笑聲,你們甚至從不曾在冬夜守候某個燈窗之下, 望著那團燈影瑟瑟發(fā)抖地抱緊雙肩,用一趟趟徘徊將路基墊高。你們生不如王先生活得率真和細膩,死后的鬼魂也就不必拾取那千層萬層腳印,載不動,許多愁。
我在有風的夜里讀王先生的《腳印》,聽到一個鬼魂在椰樹葉梢上嘆息,我想這肯定是一個浪漫的鬼魂,它的肉身曾經(jīng)在塵世上忙碌不休,以至累它到如此疲憊的程度。我在鬼魂的嘆息里輕而易舉地找回了童年少年青年,找到了屬于我的聲音,那是一陣風的響動,它從京都童年的楊樹吹來,吹過湘楚少年的泡桐與青年的銀杏,吹過蜿蜒千里的南遷之路,停在我窗外中年的樹上。 它看著讀《腳印》的我,對我說,多留下一些腳印吧,別怕累著將來為你拾腳印的鬼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