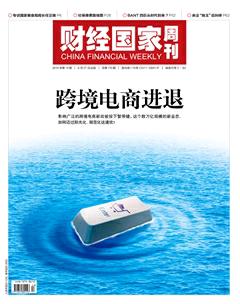洞悉國際貨幣權力
黃薇
成為國際主導貨幣通常需要有能力提供三類激勵:貿易激勵、金融激勵和安全激勵。
本書的諸多作者均是長期從事貨幣權力研究的政治經濟學家,他們的研究范式與我習慣的經濟學思維方式有著很大的不同。單純從經濟學角度進行研究是一回事,考慮政治之后的實際政策選擇往往是另一回事。這并不是簡單的陰謀論所能解釋的。對于從事國際經濟事務的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而言,這本書是理解當今世界的一個有益工具。
首先,該書有助于理解當代英美對外政策的基本思路。
2010年底開始,我所在的研究機構與中國有關部委建立了國際經濟合作領域的長期工作機制。工作的主要內容是協助中國參與國際經濟協調,如二十國集團(以下簡稱G20)合作、金磚國家合作等。接觸政府間的經濟協調活動初期,我十分不解為何西方,特別是美國,在各類國家間經濟政策協調對話(無論是G20會議還是中美經濟與戰略對話)中,一直將失衡問題視為國際經濟協調中的核心問題,并且從未停息過對中國人民幣匯率的種種指責。
按照經濟學常識,不可持續的國際收支失衡雖是一個國際問題,但也同樣是一個國內問題。對于那些國內經濟結構扭曲所導致的國際收支失衡,更加長效的治理方式是改善本國的經濟環境和經濟結構。為何美國一直揪著中國不放,而對真正亟待解決的涉及世界經濟中長期經濟發展環境的根本性問題熱情不大?畢竟類似G20這種重要的國際經濟政策協調論壇應該更多地關注那些全球層面的、新興領域的重大經濟治理合作問題,各國共商發展之道,而不應成為一個相互指責、推諉責任的平臺。這個問題困擾了我將近4年的時間,不過現在手里的這本書能夠很好地回答以上疑惑。
在處理經濟發展與國際合作的關系問題上,中美大致遵循兩種不同的路線。中國路線偏向于向內探尋提升的可能,通過不斷地加強自身建設來實現經濟與社會的發展。在這種視角下,國際合作的主要目的一方面在于營造適宜于經濟發展的開放穩定的外部環境,另一方面在于助推國內的經濟制度改革,使之更加適應當代經濟社會的需求。例如2013年成立的上海自貿區和2015年成立的深圳前海自貿區都是中國探索新型對外經濟制度改革的前沿試驗區;2013年中國提出并引導建設的“一帶一路”戰略構想是為了歐亞大陸經濟體的進一步融合和提升資源配置效率;2015年8月中國人民銀行發布《關于完善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中間價報價的聲明》進一步深化了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宣布人民幣中間價開始遵循隨行就市的市場化原則。
美國路線則偏向于將經濟發展的主要問題歸因于國外,并從外部尋找替罪羔羊。這種路線集中體現為其對外策略往往側重于通過樹立對立方的方式來暫時安撫民心。其國際合作的主要目的是實現和維護有助于實現內部問題外部化的國際權力。本書第二章和第五章詳細地剖析了國際貨幣權力的宏觀基礎及貨幣政策協調的實質。用作者的語言來說,1999年創建G20財長與央行行長會議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中國等新興市場國家的發展使得在七國集團內部已經不足以完成美國轉嫁調整成本或延續調整時間的政策目標。但是,由于G20國家差異巨大,再加上美國的國際貨幣權力已經有所減弱,因此美國在G20舞臺上施展貨幣權術的能力受到極大約束。難怪美國對于G20的合作越來越缺乏耐心和興趣。
其次,閱讀本書時需要注意作者的立論基礎。
以第二章為例,所涉及的兩個基本假設體現了經濟學研究邏輯與政治學研究邏輯的根本區別。第一個基本假設是在應對外部收支失衡時,一國已經實現了內部的收支平衡,因此,國內經濟政策目標并不需要調整。從經濟學角度而言,這顯然不是全部的事實。國外失衡與國內失衡之間本身互為鏡像,即過度的國際收支失衡實際也在表達國內經濟的失衡。這些失衡有些是由于資源稟賦所致,如石油輸出國等;有些則是其他扭曲性因素所造成的,例如鼓勵消費的經濟金融環境等。
本書的第二個基本假設是一國國內經濟政策目標的獨立性高于一切,因為它是自治權的唯一體現。因此,任何形式的受到外部影響的政策妥協(或偏離)都應被視為一種犧牲。眾所周知,由于經濟治理中常常需要考慮多種因素,因此政策目標最后需要經由政治程序決定,并非純粹由經濟評估來決定。這也意味著,本書所提及的國內經濟政策的自治權并不能完全等同于經濟理性。在這一假設下,所謂的國際經濟協調僅僅是大國借以對其他國家經濟政策安排實施影響的一個途徑。
最后,本書提出了國際主導貨幣形成的關鍵因素。
隨著中國經濟的崛起,作為經濟發展的必要工具,貨幣的國際化發展也越來越受到重視。根據本書作者的研究,如果希望真正成為一個國際主導貨幣通常需要有能力提供三類激勵:貿易激勵、金融激勵和安全激勵。貿易激勵是指具有相對于其他國家更好的經濟基本面特征以及緊密的貿易聯系。上海國際能源交易中心(INE)即將推出以人民幣計價的原油期貨合約正是基于貿易激勵實現的中國金融市場建設步驟。此舉意味著中國在全球金融、能源以及大宗商品領域中的影響力可以被實現。考慮到中國市場對于原油的強大需求,此舉將逐步侵蝕布倫特原油和美國西德克薩斯輕質原油對于能源市場定價的重要性。
金融激勵則是指提供保守型貨幣政策承諾以保障貨幣幣值的穩定,同時具備適應金融市場發展的制度環境以為貨幣交易的方便提供保障。中國在2015年上線的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CIPS)即是與此相關的一個典型例子。該系統將統一人民幣離岸與在岸匯率,減少中國的人民幣結算銀行的轉手牟利機會,極大提升國際金融機構進行人民幣在岸結算的效率。因而會吸引更多的海外金融機構開展人民幣業務。另一個例子來自美國,美國紐約聯邦儲備銀行的金庫中存放了全球官方黃金儲備的四分之一,約有60多個國家將黃金儲備存在美國,其中包括中國。不過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已經陸續有國家開始從美國提出黃金儲備,這反映出外界對美國金融穩定性的不信任。
此外,國際貨幣主導國通常還會給追隨國家提供經濟以外的安全激勵,這一點在貨幣區安排中更為常見。貨幣區的成員國資格通常與追隨國獲得的其他利益相關聯,如經濟援助、軍事保護、優先獲得貨幣區內國家的資本和商品市場的權力。例如在曾經的盧布區,俄羅斯不僅賦予成員國商品進入俄羅斯市場及獲得能源資源補貼的好處,而且還提供軍事保護。按照這一邏輯,單純地依賴貨幣建設與市場培育無法成為完全意義上的國際主導貨幣。需要指出的是,這里提及的三種激勵并非一成不變,例如美國降低對追隨國的安全保護將可能削弱追隨國的追隨動機,而如果美國股市、債市面臨重大動蕩則可能會引發對于美元霸權的嚴重負面拖曳效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