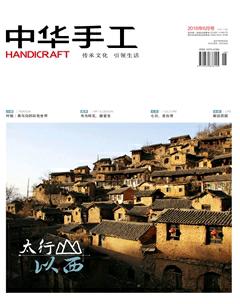新舊蘇園
陳麗萍



Eames設計的椅子、Jean Prouve設計的壁燈、巨大的玻璃窗、蘋果電腦;
嵌了蘇州老城磚的床頭柜、兩個斗拱改成的吊燈、有兩扇花窗的椅子、老木匠用過的紅木刨子門把手……
推開新舊間,“新”與“舊”對比明顯,卻又舒適得理所當然,好似過去和未來在這里交織。“這緣于我對當代設計和傳統文化的雙重喜愛。”王斌笑。所以去設計,去嘗試,讓新舊融合。
新 在于活力
無疑,新舊間是現代的。
白色的墻面沒有一絲多余的設計,地上鋪的灰瓷磚是流行款式。如此,整個空間明亮、簡潔,為老舊的公寓帶來無限生氣與活力。
當然,新舊間最多的,還是實木。吊柜、邊柜、書桌、椅子、床……或許因為屋主是建筑師的原因,使得這些木家具很有整體感。“其實我更喜歡硬朗的材料,比如混凝土、水磨石、樹脂,不過家裝要考慮家人的感受,所以用了許多木材,比較溫暖。”
所有家具都是他設計,請木工做出來的。只是,能夠現場制作出復雜木作的木工不多,如何顯得不廉價?成為一個挑戰。舊物的加入,很大程度上解決了這個問題。譬如床頭柜,原木上一塊黑色老城磚,氣質瞬間提升了好幾個檔次。
城磚是1958年王斌的父親和叔叔搬回來的。前兩年蘇州政府鼓勵大家把城磚捐出來恢復城墻,但這些城磚早流落在了四處,有些被砌成古街的道路、有些被當成建材成為了老民居中的一部分。“城墻并沒有消失,只是分散到了我們生活的各個角落。”他把城磚嵌入床頭柜,讓城磚獲得新的生命。
上閣樓的樓梯,根據落差做了一排書架。如此,書架的每一層都隨著樓梯起伏。抬起頭,天花板上也根據樓梯的高度做了4個書柜,保證不會碰頭。但站在上一級階梯上,伸手就可拿到柜子里的物件。趣味十足。
閣樓的舊物最多,一眼望去,卻沒有絲毫陳舊感。或許是因為明亮?棕色皮沙發后面,是一個小小的窗戶,頭上,還有兩個天窗。或許是因為布置?巨大的谷倉門,滑軌藏在吊頂下,更像一面裝飾墻。
推開谷倉門,背后別有洞天,這里還藏著一個書房,兩張書桌各占一方,地上一排小小的綠植。拉開書房的窗簾,外面還有一個小陽臺,粉墻黛瓦、綠意盎然,好似穿越,以為走進百年前的蘇州園林。
舊 源自沉淀
“我不會刻意追求所謂極簡的風格,更有興趣的是在空間和所有物品之間建立一種更豐富的關系,喚起一種有人情味的生命力。”
王斌喜歡收藏舊物,去外地旅行總會帶回來一些當地的舊物,譬如斯里蘭卡的老懷表、吉爾吉斯斯坦的大花瓶等。還未搬入新舊間,舊物已經差不多填滿了這里。
最令人稱道的,自然是谷倉門上那個門把手。沒有了徒弟的老木匠,退休的時候把全部老工具以500元的價格賣給了王斌。感覺到老木匠有許多不舍,他便想著要用這些工具來做點什么。待做好了谷倉門,要安裝門把手的時候,他突然想到了這些工具,搜尋一番,發現紅木刨子非常適合。果然,去掉刀片的刨子,配上谷倉門,無論配色還是樣式均令人叫絕。更關鍵的是,刨子的兩個“耳朵”都可以用來借力推門。
“舊物使得新家充滿故事和回憶,容納時代的變遷和個人的情感。”充分利用舊物,融于新的家具設計中,如此。它們就不僅僅是擺設,而是作為功能性元素獲得新的生命。
“新與舊不僅在家里上演。”新舊間是一個原地回遷的老小區,王斌為了把尺寸超過樓梯寬度的沙發運上閣樓,找來了一輛吊車,小區鄰居紛紛聚集到樓下“共襄盛舉”,紛紛出謀劃策。搬進來后,他發現老小區故事多:樓道里永遠堆放著很多等待變賣的舊貨;二樓老爺爺家的陽臺上像熱帶雨林般種滿了各式植物,還把綠化帶當成自家花園,種上了月季、山茶;對面的老奶奶家里則堆滿了陳年報紙,甚至可以把報紙堆當成沙發坐在上面看電視……
這種熟絡的鄰里關系讓他想起從前,帶來許多靈感,也很安心,可以享受寧靜,“更重要的是,在這里,我似乎找到了過去和未來相交的坐標點,找到了心靈的歸宿。”
王斌教你舊物改新
花窗椅
老家拆遷剩下的兩扇花窗,配在木工做的椅子上。木椅尺寸根據花窗大小來定,留下凹槽,嵌入花窗即可。如此,既風雅、又結實。
斗拱吊燈
兩個斗拱是舊建筑的材料,發現它們的時候正和梁柱一起當廢柴一樣變賣。把它們朝內扣在一起,組成一個四方空間,裝上電源,就是一盞古老而別致的吊燈。
木雕桌飾
把從山東收回來的木雕小件,裝在餐桌的4個內角。北方木雕粗獷大氣,配上簡潔的餐桌,既是重要的結構,也讓吃飯的地方更有古意。同樣方式改造的還有邊桌。
樓梯穿衣鏡
收回來的舊式樓梯,鋸掉中間幾級腳踏。然后根據樓梯上窄下寬的尺寸,鋸一塊鏡片裝上,相信再也找不出比這更有特色的穿衣鏡了,既洋氣又古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