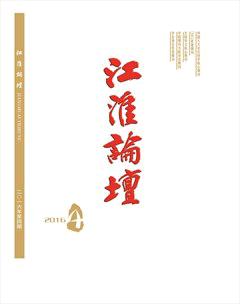凌一葉孤舟,渡生命之洋
——論理查德·耶茨《十一種孤獨》所秉持的三種情懷
姚月萍
(合肥工業大學外國語學院,合肥 230009)
?
凌一葉孤舟,渡生命之洋
——論理查德·耶茨《十一種孤獨》所秉持的三種情懷
姚月萍
(合肥工業大學外國語學院,合肥230009)
摘要:理查德·耶茨是美國“焦慮時代的偉大作家”,他用簡約、平實的文字記錄了二十世紀中葉美國社會的主流生活,影響了之后的眾多作家。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說集《十一種孤獨》用十一個故事代言了美國20世紀30年代至60年代的焦慮,描繪了整個現實世界的殘酷。帶著個體生命的印記,耶茨生發出對現實世界的三種情懷:孤獨、失敗與絕望。
關鍵詞:《十一種孤獨》;情懷;孤獨;失敗;絕望
本刊網址·在線雜志:www.jhlt.net.cn
《十一種孤獨》是理查德·耶茨的第一部短篇小說集,于1962年在美國出版,被譽為“紐約的《都柏林人》”。從主題意蘊和現實境遇上來看,兩部小說集委實很相似。詹姆斯·喬伊斯的《都柏林人》由十五個故事匯集而成,以愛爾蘭首都都柏林為背景,強調了一個共同的主題,即19世紀末20世紀初彌漫于整個愛爾蘭社會的麻木不仁、死氣沉沉的精神狀態。這種精神狀態被喬伊斯定義為“癱瘓”(Paralysis)。同樣,《十一種孤獨》用十一個故事代言了美國20世紀30年代至60年代的焦慮,描寫了社會的蕭條、虛偽,行文直指普通人的孤獨、失敗與絕望。而在現實境遇上,兩部小說在出版之初都鮮有人問津,《都柏林人》曾被22家出版社退稿,前后歷經9年挫折;《十一種孤獨》出版多年之后,才讓人們意識到它的魅力所在。
20世紀30年代至60年代,美國從經濟大蕭條走向二戰后的繁榮發展期,其間,文學創作潮流也隨之變遷。從30年代左翼文學與現代派文學并駕齊驅,到50年代“垮掉的一代”文學產生深遠影響,再到60年代“黑色幽默”的大行其道,敏感、好奇、富于個性解放精神的美國作家不停地探索和實驗,試圖把歷史演變過程中人受到的擠壓和社會轉型所帶來的陣痛一一表現出來。戰后的世界讓耶茨陷入巨大的迷茫,他懷疑人性是否還有善良的一面,懷疑人的命運是否會在孤獨中無窮無盡的穿行。在他眼里,美國的社會變得十分復雜,價值觀念混亂,于是便通過夸張、荒誕的方式,再現生活中底層民眾支離破碎的故事。在這些故事里,沒有希望與光明,只有耶茨對世界的悲觀以及他用來展現真實世界的孤獨、失敗與絕望。這三種情緒不斷在耶茨的手中重復與生發,遂形成了他對世界不滿的三種情懷。
一、唯其孤獨,方可映射世界
孤獨既是心理學層面上的定義,也包含了人類學和社會學的內容,而在耶茨這里,孤獨更應該被稱作為一種社會性格。“任何巨大的社會形態,為了保持自身的多元化發展,總要孕育出各式各樣的社會性格。”[1]耶茨在描寫社會性格上是一位大師,他沒有借助任何宏大的社會事件,而僅僅截取了一個個普通人的生活片段,就描摹出“焦慮時代”下美國社會的整體性格,獲得了整整一代讀者的贊同與共鳴。
耶茨也屬于孤獨人群中的一員。他出生在大蕭條時代,酗酒、容易歇斯底里的母親帶著他和姐姐在曼哈頓艱難度日。中學畢業之后,耶茨受到海明威的影響,認為作家應該融入生活的洪流中,通過斗爭在生活中占有一席之地。于是,他參軍去了法國,像許多上世紀五十年代的作家一樣,他經歷過戰爭,但不幸在軍隊中染上肺炎,治療康復后,從德國退役,回到紐約,在此結婚。1951年,他帶著軍隊發給他的肺炎補償金舉家遷到歐洲,當他沉浸在自己孤獨的寫作中之時,妻子與他關系破裂,帶著女兒從倫敦回到美國,幾年后正式離婚,兩個女兒的撫養權也歸了妻子。此后的許多年,耶茨從歐洲輾轉到美國孤單一人生活,在煙草和酒精的刺激下不停地寫作,直至1992年11月,他透支完了自己的身體,孤獨地離開了令其不滿的世界。現實的生活給了耶茨孤獨的世界,除了用筆去描摹孤獨世界的形狀,他還把自己的孤獨演化成一種情懷,傾其所有般地投注了自己的靈魂,打通了內心與外部世界的聯系。
《十一種孤獨》寫了十一種孤獨的人生,主人公都是生活在社會底層不如意的普通人:新轉學的小學生、即將結婚卻十分迷茫的男女、郁郁不得志的軍官、老病號的妻子、曼哈頓辦公樓里被炒的白領、干巴巴的老教師、退役軍人、遭羞辱的爵士鋼琴手、肺結核病人、有著杰出想象力的出租車司機、屢屢遭挫卻一心想成為作家的年輕人等。這些普通人經受著來自現實和精神上的雙重擠壓,與人相處總是不如意的,只好退縮到無人窺視的一隅,任孤獨包圍自己。
最能體現耶茨這種孤獨情懷的小說是《一點也不痛》和《與陌生人同樂》。前者是一篇關于孤獨與背叛的小說,女主人公麥拉的出軌雖然有違道德,但卻是在孤獨籠罩下的無奈選擇。丈夫哈利常年患病的身體早已萎縮變形,百無聊賴的醫院生活更讓他失去了對妻子的關懷,他像一盞即將燃盡的油燈,已然無法再承擔照亮他人的責任。麥拉每周一次的例行探望多數都在沉默中打發過去,寥寥幾句交談,也無非是對以往瑣碎話語的重復。這樣可有可無的見面讓麥拉每經歷一次就加深一些對丈夫的逃離感,更加無所畏懼地與姘夫杰克廝混。小說的細節反應出麥拉的這種微妙心理,在前去探望丈夫的路上,她十分厭惡杰克的毛手毛腳,但在從醫院回來的路上,她卻完全放開自己,任由杰克擺布。只有通過男女之愛,麥拉才能擺脫孱弱丈夫帶給自己的孤獨感,去體驗鮮活的肉體與生命。但麥拉又終究是無法逃離孤獨的,每周一次的探望只能把她拉進無限循環的孤獨旋渦里,一遍遍地體味自己的孤獨,直至越陷越深,無法自拔。《與陌生人同樂》這篇小說從題名上就定下了書寫孤獨的基調,表面上它寫了一個古怪老教師的孤獨,實際上卻以一群三年級小學生的孤獨為中心。六十多歲的斯耐爾小姐毛孔里都散發著古板、嚴厲的味道,她對學生無所謂好與壞,只是不習慣或者說不愿意付出情感。學校里所有的學生都不喜歡她,老師們也不接近她,她的孤獨顯而易見。但與她的孤獨相比,學生們的孤獨更值得反思。無法與其他老師的學生去攀比關愛,能讓斯耐爾小姐的學生亢奮的只有逃避了,他們既要逃離斯耐爾小姐又要逃離周遭朋友的幸福。對于學生們來說,干巴巴的斯耐爾小姐更像是一個陌生人,她本身就是一種孤獨的象征。學生們為了逃離這種孤獨,只能以孤獨為代價,把自己同外界隔離開來。
耶茨窮盡一生與孤獨為伴,他的孤獨不是空虛與寂寞,也不是單純的心理壓抑,而是在內心的平靜中獨行。正如他自己所說,“如果我的作品有什么主題的話,我想只有簡單一個:人都是孤獨的,沒有人逃脫得了,這就是他們的悲劇所在。”由此,耶茨的孤獨情懷可概括為:在個人的生命歷程中對孤獨毅然持守并由此生發出具有出色價值理想的精神狀態。
耶茨用孤獨去認知世界,也用孤獨去構建世界,這一點與其他擅長書寫孤獨的作家不甚相同。海明威可以被稱為耶茨創作的領路人,他的人生軌跡深刻地影響了耶茨。18歲中學畢業,耶茨沒有選擇讀大學,而立志像海明威一樣通過斗爭而在生活的洪流中占有一席之地。在小說《建筑工人》里,耶茨多次把“我”與海明威放到一起進行比較:相同的從軍經歷,類似的婚姻狀況等等,但海明威的影響并沒有讓耶茨的小說在對孤獨意蘊的表達上成為復制品。海明威對孤獨的探索總是帶著超越與反抗的,他在否定傳統精神價值的同時,還苦心孤詣的尋覓陷入孤獨絕境的現代人的出路。同樣冷峻的筆調下,海明威呼喚著人性尊嚴的回歸,贊美著“非英雄”的堅毅與隱忍,而耶茨卻很無情,他不給主人公任何出路,也很少留給讀者安慰。[2]簡而言之,孤獨在海明威那里是一種激發反抗的情結,而在耶茨心中卻彌漫成一種平淡的情懷。
二、坦言失敗,還原真實世界
在耶茨筆下,失敗與孤獨總是相伴相生,更多時候,失敗甚至比孤獨更加永恒。在《十一種孤獨》里,每一篇小說都充斥著大量失敗,有的關乎工作生活,有的涉及親情婚姻。如此執著于對失敗的描寫,離不開耶茨真實的失敗人生。參軍去法國后,他沒能在軍隊里建立功勛,卻因染上肺炎從德國退役。回國后帶著并不幸福的婚姻舉家移居歐洲,在租來的房間里,伴著煙草和肺疾,他不停地寫作,但都不成功,《紐約客》拒絕了他的每一篇投稿。(1)婚姻破裂后,耶茨回到美國,輾轉多個公司謀求生計,甚至為付賬單,代人寫作。不管是政府部門還是大學,耶茨都沒能獲得成功,只是一遍遍地品嘗失敗,直至離開人世。耶茨的人生充斥著失敗,帶著習以為常的處世態度,他又把失敗填充進自己的孤獨世界并且拒絕質疑與抗爭,因為在他的意識里,失敗才是真實世界的代名詞。
《泰晤士報》贊譽耶茨為“20世紀最具洞察力的作家”,誠然如此,《十一種孤獨》里的作品并非依仗著華麗的修辭和驚心動魄的故事情節,而是憑借作者對于日常生活的敏銳的洞察力和對于人物形象、背景環境等文學要素的把握,用簡約、樸實的文字構筑起了貼近社會現實的文學世界。當然,耶茨杰出的洞察力還體現在對現實世界的把握上,他用自己的一生洞察了真實世界的本質——無盡失敗的結合體。和孤獨一樣,耶茨選擇把失敗放進自己的文學世界里溫養,他要告訴讀者:生活之路有時會意外地轉個彎,但給我們的并非驚喜,仍舊是無奈。
《十一種孤獨》里描述了太多失敗,又幾乎全是命中注定的。《喬迪撞大運》里優秀的軍官瑞斯,正直嚴厲、不近人情,他希望通過訓練把新兵們變成合格的軍人,卻受到上級的擺布與他人的排擠,被調到野外營地工作。他害怕失敗,安全感的缺乏使他不斷加強自我保護,刻意保持和士兵的距離,試圖以自己的正直去對抗整個軍隊的散漫與墮落。事與愿違,當訓練結束后,新兵們都變成了兵油子。耶茨讓瑞斯眼睜睜地看著失敗降臨在自己身上而毫無躲避之力。和瑞斯相同的另一個失敗者是《自討苦吃》中的沃爾特·亨德森,他對抗失敗的方法是通過表演去掩飾自己的無助與痛苦。在中國文學里,這種病態的心理叫做“阿Q精神勝利法”。與阿Q不同的是,沃爾特沒有去虛構自身的強大,而僅僅是在人前維持了自己短暫的體面,但這又何嘗不是自欺欺人。沃爾特兒時善于表演死亡,這讓他收獲了玩伴們的贊美,也讓他得到成人社會虛偽的尊重。被公司解雇,他第一時間就偽裝好自己,在同事面前淋漓盡致地表演了自己的瀟灑。沃爾特最終無法維持自己的表演,在妻子面前,用“向后頹然倒進椅子里”[3]93真正體面的宣告了自己的失敗。沃爾特為了遮掩失敗而選擇了孤獨應對,卻無法承受來自孤獨的煎熬,他的失敗在于既無力扭轉現實也無法控制自己。耶茨對失敗者的嘲弄不僅于此,在《與鯊魚搏斗》中,他并不像慣常的那樣,一開始就把人物設定為失敗的樣板,利昂·索貝爾用自己的行事方式表現得像一個敢于同鯊魚搏斗的人。他放棄高薪而選擇在《勞工領袖》做一名報社編輯,希望成為一名可以 “洞察人性本質之謎”[2]109的專欄作家,但結果卻夢想破滅,飯碗也不保。原本這種失敗還帶有著反抗者的光環,但耶茨卻在小說結尾撕下了索貝爾的反抗者面具,將他重新歸入失敗者一類。實際上看似柔弱的妻子才真正地左右著索貝爾的生活,甚至可以禁止他向朋友表示感謝。一個敢于同鯊魚搏斗的人,卻在妻子的授意下茍活,這實在是一個極好的諷刺。
在海明威那里,老漁夫圣地亞哥不斷地對抗失敗,雖然最終仍以失敗告終,但他是真正敢于同鯊魚搏斗的勇士,這樣一個“硬漢”式的人物代表了一種可以被毀滅但不可以被打敗的精神力量。海明威借此建立起充滿人類力量的世界,賦予反抗失敗的勇士圣徒般的贊美。而耶茨卻用“與鯊魚搏斗”這樣一個篇名,帶著自己對世界的獨特認知,去解構與反叛海明威所建立的世界。在耶茨的世界里,失敗是永恒的,不管人如何反抗,終究逃脫不了失敗的窠臼。耶茨的一生都在經歷失敗,他沒有激發出圣地亞哥般堅毅的斗志,但同樣也沒有被失敗徹底毀滅。他對待生命如蘇珊·朗格所說,“把生命視為一個整體,視為一種他凌駕于失敗之上的成功”[4]。同時,他也意識到現實世界遠比海明威所料想的殘酷,人幾乎無法掌握反抗失敗的力量。在這樣的世界里,耶茨用自己面對失敗坦然超脫的情懷向讀者訴說了一個個失敗的故事;他不奢望讀者能從失敗里學會反抗,更不愿看到讀者因為失敗的綿長而陷入絕望,他只是把真實世界里的失敗呈現在那里,不提供任何啟示和幫助。
三、絕望與生命相守
希臘悲劇善于展現人物致命的缺陷,當厄運來臨,俄狄浦斯們不免要仰天長嘆,控訴命運的無常與弄人。而耶茨不會這樣,他無情地刻畫出一幅幅人物白描,沒有讓自己的主人公故作姿態地去抱怨宿命。從耶茨的作品與人物里,我們能夠認出他的影子。《與鯊魚搏斗》中寫了九本書卻無一出版的利昂·索貝爾影射了他寫作上的失敗,《勃朗寧自動步槍手》里退伍軍人費隆的遭遇也與他的現實境遇相符,《建筑工人》里最終失去妻子和子女的鮑勃甚至就是他的真實寫照。但耶茨無意用自己的遭遇去博取憐憫,困擾世人。在早期的作品《革命之路》里,耶茨暗示自己不想屈服,讓弗蘭克與愛波想盡辦法拯救婚姻;而到了《十一種孤獨》,耶茨卻讓主人公們放棄了面對絕望的努力,他不愿用喜劇色彩來羞辱自己,更不齒于從文字中找尋安慰。實際上,耶茨深知屈辱的可怕,但更無奈的知道生活還要這樣繼續。當耶茨孤單一人凄苦寫作時已然醒悟:孤獨與失敗鑄就的絕望枷鎖將與自己終生相守。
《萬事如意》驗證了耶茨對婚姻的絕望。在迷茫中作出結婚決定的格蕾絲不敢幻想未來,僅能用自己的妥協換取暫時滿意的結果,但她最終卻把自己一步步地逼到懸崖邊,等待粉身碎骨。耶茨在訴說這樣一種絕望:人拋棄一切作出選擇,但卻讓自己失去所有,連同自己幻想的美好一起,生活全部歸于崩塌。繼而他又用《舊的不去》來展現疾病帶給自己的絕望。封閉的結核病大樓遭到一切外部世界的排斥,它像一個孤島,承載著一百多個被人遺忘的病人。在大樓之外,每個病人都有自己的家庭,卻因長年的分隔早已形同陌路。結核病摧殘了人的身體,孤獨與絕望更讓人在精神上無依無靠,只有在圣誕節來臨之時,一群人才能借歡樂之名暫時忘掉孤獨;當借口失效后,孤獨還是會重新襲來,絕望就像反復發作的結核病一樣,越來越難以抵抗。《南瓜燈博士》則表達了耶茨想進入世俗世界而不得的絕望,他借用轉學男孩文森特·薩貝拉不知道如何融入新集體這樣一個隱喻,來暗示自己融入現實世界的艱難。老師普賴斯小姐試圖幫助文森特卻適得其反,遭到他惡意的攻擊。究其原因,是因為普賴斯小姐的善意違拗了男孩自己進入集體的意愿。如英國小說家安東尼·特羅洛普對自己童年的描述那樣:“我非常孤單,必須自己想一些游戲。我一直都需要某種游戲,當時也是一樣。讀書并非我之所好,無所事事又不會使我快樂。因此,我就在心里牢牢地建立某種空中的樓閣。”[5]123男孩文森特的空中樓閣就是自己精心編造的謊言世界,普賴斯小姐動搖了它,文森特因為屈辱展開了攻擊。最能體現耶茨絕望情懷的是《建筑工人》,這篇小說可以看作耶茨對自己真實經歷的演繹,而小說人物鮑勃和伯尼則是耶茨一生失敗經歷在藝術上的折射。耶茨給這篇小說冠以“建筑工人”之名,他不愿意認同一個失敗的代人捉刀者可以像海明威那樣被稱為作家,寧肯以諷刺的“建筑工人”代稱。在小說開頭,耶茨俏皮的嘲笑自己:“您最好還是把他想的笨拙、魯莽一點,因為不論是在小說還是現實生活中,幾乎所有作家都如此。”[3]191在小說結尾,耶茨的替身——鮑勃仍舊找不到寫作的啟示,只能用“上帝知道,伯尼,上帝知道這里當然在哪兒會有窗戶,一扇我們大家的窗戶”[3]253來掩蓋絕望。
耶茨將對待絕望的態度隱藏在自己的寫作中,他的寫作從未真正成功,但他的寫作也從未停止。[6]生命中的最后一年,他的健康狀況極度惡化,仍舊在抽煙與酗酒中寫作,寫作本是他的生命力,但終究抵擋不住煙草與酒精的侵蝕。耶茨漠視絕望,正如他從不思考寫作帶給自己何物一樣,既然絕望已經如影隨形,又何必費力去打破它與生命之間的平衡。
英國小說家格雷厄姆·格林對待寫作的態度與耶茨相似,他把寫作當成一種治療的形式,“我有時候會驚嘆,那些不寫作、不作曲或不繪畫的人,他們怎么能不發瘋,不患憂郁癥,又怎么能避免人類固有的恐慌心態”[5]141。我想,這里的恐慌心態就包含著絕望。但耶茨寫作不是為了逃避絕望,因為他明白命運從不曾改變,它只會沿著必然之軌跡帶你到絕路,把你留在那里。于是,耶茨只是如實地描寫,他不粉飾絕望,也不嘲諷絕望,更不會將作品浸泡在感傷的眼淚里。[7]坦言絕望是一種情懷,耶茨用一生的經歷與智慧告訴讀者:絕望就像空氣,你總要一口口的去呼吸。
值得注意的是,耶茨認定個體生命的生存就是必然的孤獨、失敗與絕望,但死亡并不在他的情懷之列。在《十一種孤獨》里,無論耶茨讓自己的人物恒久地活著,不是為了抵抗宿命,而是對個體生存思考的超越,正如他認為孤獨、失敗與絕望是永恒的一樣,生命的存活也是永恒的,當這兩種永恒交織在一起,才是真實世界的原樣。
艾略特曾形象地把現代西方世界比作 “荒原”,其表現有靈肉分離、人格分裂、神性喪失、集體迷失等。[9]我認為,耶茨是描繪這個荒原最優秀的作者。卡夫卡沉迷于荒誕的隱喻,海明威寄希望于人的力量,卡佛用幽默給不幸世界增添一絲希望,而耶茨做的只是真實的呈現。在他的小說里,孤獨、失敗與絕望是一個無休止的循環,主人公們試圖打破無所依附的孤獨,但努力總是失敗的,最終只能走向絕望。[8]面對“荒原”上的孤獨、失敗與絕望,耶茨清醒地看破了個體生命無法改變的生命圖式,用最樸實的文字勾勒出“荒原”原貌及居于其中的殘酷。這是耶茨對自己的認知,也是他對現實世界所秉持的三種情懷。
注釋:
(1)直到2001年耶茨逝世八周年后,《紐約客》才在1月15日發表了他的短篇小說《運河》。
參考文獻:
[1][美]大衛·理斯曼,等.孤獨的人群[M].王?,朱虹,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10.
[2]宋智鵬.耶茨筆下孤獨者形象解讀[J].短篇小說(原創版),2015,(12):7-8.
[3][美]理查德·耶茨.十一種孤獨[M].陳新宇,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0.
[4][美]蘇珊·朗格.情感與形式[M].劉大基,傅志強,周發祥,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6:52.
[5][英]安東尼·斯托爾.孤獨[M].張嚶嚶,譯.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7.
[6]劉媛.耶茨《十一種孤獨》的寫作特色探析[J].短篇小說(原創作品版),2014,(36).
[7]張穎.理查德·耶茨作品中的現代性悖論探析[D].蘭州:西北師范大學,2014.
[8]張玉東.理查德·耶茨的孤獨文學淺析[J].芒種,2013,(24):149-150.
[9]崔雅萍.《夕陽》下美國黑人的人格分裂與現代精神荒原 [J].西北大學學報 (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3).
(責任編輯黃勝江)
中圖分類號:I712.074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1-862X(2016)04-0163-005
作者簡介:姚月萍(1970—),女,安徽青陽人,合肥工業大學外國語學院講師,主要研究方向:外國語言與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