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是知識分子的“權利”嗎
徐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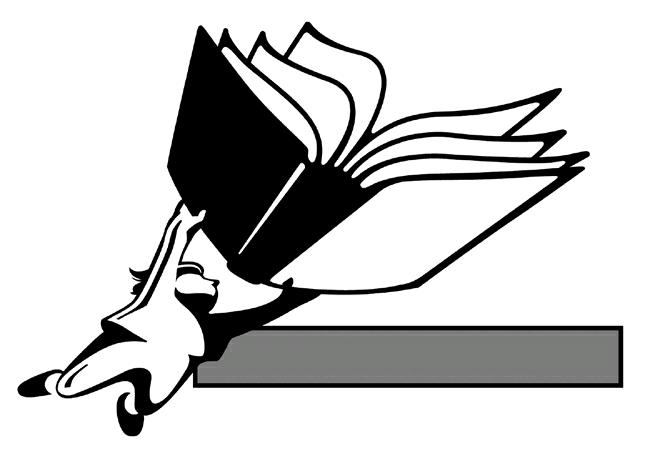
“大家”閱讀
互聯網時代,讀者并不缺乏信息,但一些真正具有傳播價值的內容,卻往往淹沒于信息洪流之中。力求將最有價值的信息,最有銳度、溫度、深度和多維度的思考與表達,最值得閱讀的網絡優質原創內容,快速呈現給讀者,是《世界文化》與騰訊《大家》建立合作的初衷與共同努力的方向。【“大家”閱讀】每期將臻選《大家》所匯聚的中文圈知名學者、專欄作家的最新文章,與讀者分享“大家”眼中的“世界文化”。
讀到一篇《為錢楊伉儷的“不公共”辯護》的文章,文章反駁有些人批評錢鐘書和楊絳對社會不公不義之事的冷淡,認為,知識分子“沒有義務為遭受不公者說話”,主要的理由是“公民行為,法無禁止,即為許可”。文章解釋道,“作為一種政治自由的言論自由,……是任何人的權利,而不是義務。如果法治條件正常,你可以在正常良法范圍內任意使用處理這項自由,沒有任何人有權干涉你是否使用它,包括你徹底拋棄這項自由的權利”。文章顯然是從錢楊的“個人權利”來看問題的,而批判者則是從知識分子的公共責任來看問題,意見不同的雙方所辯論的其實并不是同一個問題。
在一個知識分子能夠起到批判作用的正常社會里,他們對公共事務保持沉默,并不證明是他們是在行使自己的正當公民權利,而是顯示他們未盡自己的社會道德責任。盡管不盡責并不違法,但卻仍然是一種失德行為。這就像日常生活中普通人見死不救、袖手旁觀一樣,雖然法律并不禁止,但卻并不被普遍接受為道德上應該許可之事。

知識分子的社會道德責任也被視為他們的“義務”或“良心”。康德把人的義務分成完全的和不完全的兩種。如果一件事大家都去做——普遍行使——會在邏輯上或實行中引發沖突,那么,這件事就不能去做。不做這樣的事是人的完全義務(perfect duties)。完全義務禁止人有違反普遍法則的行為。例如,我們有不偷盜、不殺人的完全義務,因為可以偷盜或殺人不能作為普遍法則施行于群體之中。但是,如果我們僅僅盡完全義務,不偷盜、不殺人、不強奸等等,那還不能真正算是有良心。
如果一個人做一件事,奉行的是一個他希望能普遍化的道德原則(雖然他不強迫別人也這么做,但他希望有盡量多的人也這么做),那么他所盡的便是不完全義務(imperfect duties)。例如,雖然別人不助人,他卻可以助人;雖然別人明哲保身,他卻可以見義勇為。普通人的道德高下主要是在能否盡不完全義務和盡哪些不完全義務中比較和區別出來的。知識分子也是一樣。
人的不完全義務感越強,也就越可能有所道德擔當,知識分子尤其如此。身為一個知識分子,如果你認為實事求是、揭示真實、說真話、公正待人應該是普遍善行的原則,那么,當你看到同事或熟人被羅織罪名,打成“右派”或“反革命”,受盡屈辱,甚至家破人亡的時候,你就會為他們鳴不平。你能夠站出來為他們喊冤,以行動證明你是一個有良心的人。即使你生活在一個大多數人都對 “右派”漠不關心、甚至落井下石的社會里,你也可以把說公道話當做你的義務。這是你自己選擇的義務,這個義務對大多數人沒有約束力,所以是不完全義務。但這個義務對你有約束力,這就是良心的作用。你的良心是你個人的,但也是你在一個小范圍里聯系他人的方式,其他有良心的人會認同你,尊重你。
從過去幾十年的歷史經驗來看,能夠這樣堅持良心和道德義務的知識分子越來越不多見,但始終沒有絕跡。由于社會的環境險惡,正義和良心行為經常招致禍端,大多數人不能堅持良心,選擇了沉默。正因為如此,環境也就變得更加險惡,這是一種惡性循環。在這種情況下,提出知識分子的沉默問題——逃避道德責任,游離于公共事務和社會正義之外(無論是因為什么原因),是一件有意義的事情。這并不是在干涉知識分子的“個人權利”,或強迫他們去盡理應無須擔當的義務。
為知識分子的道德沉默辯護,就像為公民的政治冷漠辯護一樣,不能以個人權利來泛泛而論,因為不同情況下的“沉默”和“冷漠”看似為相同的行為,實質上是有不同內涵的。就拿公民冷漠來說,它指的是沒有或缺乏公民參與行為——冷漠的公民不投票,不關心公共事務。然而,這只是表象。有的公民本來就是利己主義者,只關心自家的事情,公共的事情全然拋到腦后。一百多年前,梁啟超倡導“公德”的社會啟蒙,在很大程度上針對的就是這種公民冷漠。這是一種公德缺失的公民冷漠。但是,還有另外一種制度結構性的公民冷漠,許多人本來說有公共參與意愿的,但卻被制度性的權力剝奪了參與的權利。這種剝奪可以是顯性的(如根本沒有投票的機會),也可以說隱性的(如不滿美國兩黨競選的選民沒有第三種選擇,因此事實上并沒有實行自己政治選擇的機會)。
公德缺失的冷漠比制度結構的冷漠更容易導致犬儒主義。有些人明明是因為自私自利不關心也不參與公共事務,但卻善于找出一些堂而皇之的理由,用制度結構的限制來為自己的不參與制造借口。他們不但自己不參與,而且還自視優越,覺得在見識上高人一等,看不起積極參與的他人。他們嘲笑參與者天真幼稚,預言任何公民參與必定只能是徒勞無功的愚蠢行為。這樣的犬儒主義對公民社會是一種極大的毒害。
和公民冷漠一樣,知識分子對公共事務和重大事件保持沉默,同樣也包含了不同的情況,也可能隱藏著自視優越的犬儒主義。知識分子沉默,有的是因為從來就不關心別人的事情,早已養成了一種利己主義的處世方式。有的是想發聲但被噤聲。還有的則是想發聲但懼怕發聲帶來的麻煩和懲罰,因此不得不閉上嘴巴,明哲保身。后面兩種是制度性的沉默。知識分子的利己主義沉默也很容易變化成為犬儒主義,它經常會把自己打扮成迫不得已的制度性沉默,但更經常的是把自己標榜為一種“獨善其身”的生活哲學,自命清高,孤芳自賞,明明不敢發聲,但卻偏偏還裝作高人一等,不屑多管閑事的樣子。相比之下,敢于發聲的或確實發聲的人們反倒顯得像是一些不入清流的庸俗之輩。

把知識分子的沉默簡單歸結為純粹個人性質的說話或不說話的選擇權利,其先在假設是,他們對自己的行為能有充分的選擇自由,而且,他們是可以為自己的選擇充分負責的自由主體。就中國知識分子(包括錢楊)的現狀而言,這樣的假設是不確實的,其中的原因有的是可以明說的,有的還不能明說,因此不得不對此保持沉默。楊絳的去世引發對知識分子責任和知識分子沉默的討論,不僅涉及她個人,也涉及知識分子的普遍生存狀況。這在當今中國是一件很及時的事情,其意義遠遠超過了對錢楊個人的評價,不應該局限于對他們兩人的褒貶。
討論沉默,而不是對沉默保持沉默,這本身就是一種公共意識的覺醒和公民覺悟的進步。美國社會學家伊維塔·澤魯巴維爾(Eviatar Zerubavel)在《房間里的大象:生活中的沉默和否認》一書里把對公共事務的沉默稱為“政治性沉默”,這是一種與社交禮儀中寡言少語不同的沉默。政治沉默中有世故與禁忌之別,但這二者間的界限并不像看起來那么涇渭分明。這樣的沉默中經常包含著對沉默的沉默,形成一種 “超極沉默”(meta-silence)。對超級沉默保持警惕,并有意識地打破這種沉默,這應該成為知識分子的一項重要社會責任,也是今天討論錢楊兩位學人政治行為缺失的普遍意義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