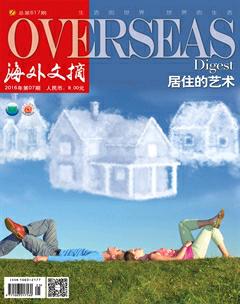幽靈伴侶
西里爾·德方坦++薄荷
恩佐離開瑪麗已經4個月了,他離開時沒留下任何解釋。“我們是在一個片場認識的,當時我們都在那里做群演。后來每個周末,我都會去他家或者我們一起外出。我認識他的父母和朋友們。我們在一起看電視劇或展覽。我對于這段感情是認真的。”瑪麗說。瑪麗20歲,恩佐19歲。但是,我最后一次和他共度周末后,他就不再回復我的短信了,這和他的個性截然相反。“周三,我給他發了個短信,他沒回。周末到了,我問他去哪玩,他也沒回。那時,我就意識到出問題了。”瑪麗以為恩佐出事了,于是她去看恩佐的Facebook上有沒有更新。“我發現他把我拉黑了。他應該過得不錯,因為我看見他在相冊中更新照片了。這時我才知道自己被拋棄了。”沒有任何預兆和爭吵,甚至沒有令人心碎的分手短信,一切就中止了。
索尼亞也有過相似的遭遇,她后來再也沒見過她之前最好的朋友露。“我給她打過電話,但每次都只響了一聲,就收到自動回復的短信。”索尼亞說,她現在在巴黎就讀傳播學專業。“我知道這意味著她拉黑了我的號碼。她還在Instagram上把我拉黑了。我知道我們的友誼走到了盡頭,但卻不知道原因。”
瑪麗和索尼亞都莫名其妙地被戀人、朋友“ghosting”了。這個新詞已經出現數月,它來自于英語的“鬼魂”一詞,最早被美國人使用,指通過約會軟件網戀的情侶,或是相處過較長時間的朋友,在不做任何解釋的情況下離開,并拉黑你的電話號碼和各種社交網絡帳號。通過失蹤達到分手的目的,已經不稀奇了。上個世紀70年代的一部電影敘述了一個男人在約會過程中,提出“去買煙”,然后一去不返。這種一去不返的橋段在過去很少見,而且多出現在小說中,但現在,卻變得稀松平常。
英國《財富》雜志3月進行了一項調查,結果顯示,78%的20-30歲人群都曾有過被“ghosting”的經歷。《赫芬頓郵報》輿觀調查網做的另一項調查稱,2014年,11%的被調查者“網絡自殺”,以達到分手的目的。在社交網絡上拉黑某人被視作最不禮貌的行為之一,但是“網絡自殺”卻讓“失蹤者”從容不迫。悄悄地退出一段關系似乎在人際關系虛擬化的社交網絡時代變得更容易了。“不少人在網絡上建立過較為親密的關系。決定離開的人因為害怕對方不愉快,所以不會明確地和對方解釋原因。或許,當另一半迷人的神秘感破滅時,就是他們要離開的時候了。”心理分析專家米歇爾·斯多拉解釋道。另一種情況就是在離開前撂下狠話,然后“落上大錘”:斷絕聯系。被拋棄的人總是有點失落。
“我開了個失敗的玩笑,然后我們的聊天就戛然終止了。”41歲的小學教師科琳回憶道。怎樣才能了解對方,并接受對方復雜的一面?在晚會上,人們互相產生好感,并成為Facebook好友。如果這個“準朋友”不再讓我們感興趣,只要不理會就可以了。脆弱的聯系很容易被切斷。“他的手機通訊錄里有成百上千人,他可以輕易地找到比你更有趣更漂亮的女孩。”索尼亞嘆息道,她在約會軟件上認識了一個男孩,又被莫名其妙地切斷了聯系。對,他們已經在網絡上“自殺”了。年輕的計算機工程師阿布戴拉坦陳:“我在網上認識過很多人。我決定不再和一個人說話的時候,并不會感到愧疚。同樣,如果一個和我認識半年的朋友以同樣的態度對待我,我也覺得無所謂。”
約會網站和軟件想要重新定義“愛情”,就要重新定義“分手”。“這些網站不再討論‘愛情中的付出,而是告訴用戶如何‘愉快的見面。”Misere-sexuelle.com的網站創始人斯蒂芙妮·羅斯解釋道。“短暫的關系變得可以讓人接受了,尤其是以性為基礎的關系。同樣,不加解釋地結束一段關系也不再讓人像以前那樣愧疚了。”31歲的塞里姆說,他曾是花花公子,也曾是一個“幽靈黨”,但他現在有些后悔了,“面對女人的眼淚實在太難了。接著,你厭倦了。你不再和她說話,只是因為你不想再和她見面,或者你又遇見了一個比她更有趣的女孩,這時候你又該怎么解釋呢?然而,在等待的人看來,問題就不一樣了。90%的關系中,被拋棄的那一方依然想聯系上對方。當你和一個和你同床共枕半年的女孩玩失蹤的時候,你可以很輕松,但對方可能以為你想與她發展感情關系,所以她會不停地問你,為什么要結束這段關系。”尤其是在城市中,“網絡自殺”就更容易了,因為兩個人偶遇的機會很小。
艾瑪認為,她像幽靈一樣消失,是有正當理由的。“上中學的時候,我們5個人關系非常好,不過她們和我個性并不相像。參加畢業會考后,我在大學城里住了下來,我在那里不認識任何人。剛剛搬到那里第3天,她們就不理我了。”艾瑪切斷了和她們所有的聯系,換了手機號碼,并在Facebook上屏蔽了她們。“那一刻,就像重生一般。”她們之間已經隔開了一道無形的墻。“后來,我再也沒見過她們。有一天,我父母在我家花園里找到了一幅畫,那幅畫是我們上中學的時候一起畫的。我們之間沒有發生什么足以摧毀友誼的事,但我們的友情就這樣結束了。現在,她們對我來說已經算是陌生人了。”
還有個女孩選擇了離開,遠遠的離開。她25歲時去了拉丁美洲教法語,后來生活得很幸福。“歐洲人的生活方式不適合我。我想要重建自己的人生,過更適合自己的生活,”娜塔莉·吉羅·德福爾熱離開了原來生活的地方,“這或許是唯一的辦法。在一個人的生活中消失意味著你不再聯系他,你把內心深處的憤怒掩藏起來,出于自我保護,你拋棄了他。”
“幽靈黨”消失時,總有他們的理由,這樣的行為在如今也司空見慣,但是對于那些被拋棄的人來說,滋味依然不好受。“我有個朋友和她喜歡的男孩約會,他們是在約會軟件上認識的,”索尼亞講述道,“像很多情侶那樣,他們一起散步、吃飯、看電影,然后一起睡覺。但后來,那男孩突然消失了。她給他打電話,但沒人接。她已經把那個男孩當作男朋友了。她感覺很糟糕。后來,她也遇到過其他讓她心動的人,但那次戀愛的陰影卻一直籠罩著她。她一直沉浸在疑問中:‘他為什么離開我?她一直在給他打電話,甚至在他消失3年后,她依然沒有放棄。她并不想挽回這段感情,只是需要一個解釋。”
無法理解,就無從得到解脫。“這是一種冷暴力,”娜塔莉說,“被拋棄的一方無法理解‘幽靈黨的行為,他們無法得到一個合理的解釋,于是陷入一種深深的糾結:‘我不應該說那句話。因為結束得悄無聲息,所以愛情的祭奠也無從談起,就像一場沒有結局的電影。”幽靈的鬼影時不時地出來游蕩一下,很久以后才會消失。“他消失后,每當我乘坐他曾經經常乘坐的地鐵時,我都會四處找尋他的身影,希望他能出現并給我一個解釋,即使我知道他再也不會出現。”雖然那個人已經從她的生活中消失了,但之后的幾年中,他依然能讓原本正常的氣氛變得令人顫抖。
“我10年的老朋友尤里安,突然離開了我,沒有任何解釋,讓我再也聯系不到她。我只好默默承受,我想盡辦法去理解她,”32歲的梅蘭妮說,“我感覺自己遭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即便是離婚,我都可以坦然面對,因為我知道原因,那就是我丈夫愛上了另一個人。”
30歲的比利時電影編導馬克西姆無奈地接受了朋友毫無征兆的失聯。他15年的老朋友住在布魯塞爾,他們約好在那里見面。見面的前一天,他們還重新確定了一次,從那個年輕女人的聲音中,聽不出任何的異樣。但是第二天,朋友卻沒來,從此他們失去了聯系。“我一直試圖與她取得聯系,”馬克西姆說,“每當我想她的時候,都會給她發信息,只是想知道她過得好不好。我覺得這不算是侵犯她的個人空間,我并不想強迫她敞開心扉,我尊重她的選擇。但是就我個人而言,我努力維持著這段關系,即使我知道這只是我一廂情愿。如果她來找我,我依然在這里,可我的努力似乎是徒勞的。”
[譯自法國《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