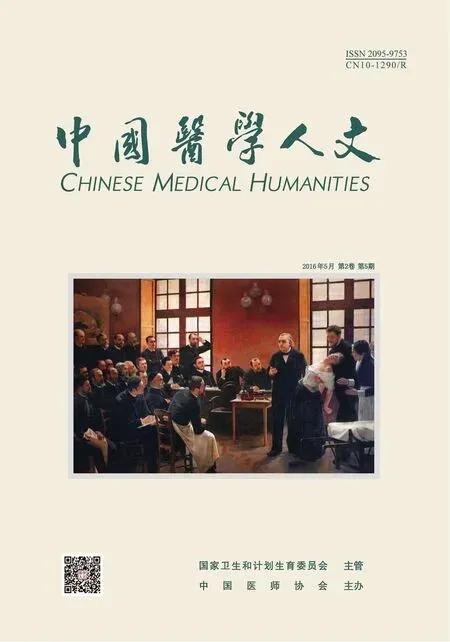一次病 贏得幾多情
文/洪云鋼
?
一次病 贏得幾多情
文/洪云鋼
“金錢草、海金沙、車前子、雞內金……”美麗草藥的名字,親切動聽,時而滑出記憶,列隊而來。我暗自慶幸,自己有生以來的一場大病,得到了醫者的真誠關照與悉心呵護。
時間是上世紀八十年代。初診為尿路結石,在家鄉的地區醫院。當泌尿科醫生聽說我在醫療條件差的山區工作時,十分同情,建議“在城里確診,回廠里治療。”“兩步走”戰略確實是為我著想。那時B超、CT很遙遠,連名詞都沒聽說。采用拍平片、做“造影”的笨辦法。拍片簡單,做造影人就遭罪了,醫生用特大號好像注射畜生時的特大針管,往體內注進滿滿一管顯影劑。我被綁在墊了黑色橡皮的床上,腰部位塞進圓形的硬物壓迫,難受萬端大汗淋漓幾乎脫虛。我把保存了30年的病歷找出來復習,平片報告:16K紙復寫,滿滿一頁,共計309個字,一氣呵成,無增刪修改。腎圖報告:坐標圖上紅藍鉛筆逐點勾勒出來的曲線。術語專業,一絲不茍,令我動容。
漫長的療程,開始奔西醫,繼而中西結合,最后死心塌地投靠了中醫。而家鄉鄰居陳大爺,地區醫院資深藥劑師,給我送來金錢草,黑色的干枯的葉莖,蓬蓬松松一大竹籃,關照道:“熬水當茶喝,使勁喝,喝完我再搞。”
草藥的名字俏麗動聽,可它們的汁水卻苦澀逼人。近百副中藥下肚,頑石仍在尿道虎踞龍盤。偶爾暴動,大痛,痛得床上打滾、劇烈嘔吐、膽汁噴涌。病急亂投醫,輾轉打聽到地區治療結石的名醫,中醫院副院長史先生。慕名前往,老先生年過七旬,衣衫素凈,儒雅親和。靜靜為我把脈,慢慢旋開帶帽的老式鋼筆,用老派的字在病歷上書寫。接過處方,一看竟與年輕的廠醫如出一轍,唉。希望中有些失望,徒有虛名?效果不言而喻,過了一周,我又來到他的面前。趁著年輕助手替他抄寫處方的當兒,老先生和聲細語,殷殷切切:在哪單位工作?家住哪里?父母多大?孩子好小?然后看看周圍,悄悄地“晚上到我家來,給你偏方‘氣氣’。”先生南方人,把“吃”念成了“氣”。不得不謹慎,當年誰敢私下行醫?
如約趕到先生家,昏黃的燈下老人正在“氣”飯,放下碗,從里屋拿出一小包東西,挺神秘。“多少錢?”我忙問,老人擺擺手:“不要錢!”我還是掏出了10元錢。見狀,老人手一縮,欲將我的期盼收回。“一天一次,用加飯酒送服,記住!不能用茶水。”“加飯酒,紹興黃酒。”怕我不懂,先生特地解釋。我暗暗驚嘆,盡管不是魯迅痛恨的藥引“冬天的蘆根,經霜三年的甘蔗,蟋蟀要原對的,結子的平地木”,何處買到加飯酒?逛大街走小巷,終于在一家煙酒商店的柜臺底層,如獲至寶般地發現了“紹興黃酒”。一看產地:黑龍江省某某縣。媽呀,“南轅北轍”。
一小撮灰白的粉劑抖進口里,舌頭“嗞”地產生灼熱反應,仰頭一小盅黃酒,將石灰般硌牙的勞什子沖進喉嚨,黃酒草木灰濃烈的古怪糊味,經久不息,“繞口三日”。吞下12包“石灰”12盅黃酒,石頭依然偏于一隅。向老先生匯報詳情,目的暗示名醫加大力度,或是提供更高級的秘方。史先生十分淡定,依然如故地開出了“金錢草、海金沙、雞內金……”讓我再去他家拿偏方,再一個療程。拿第一次偏方時,我像“抱了十世單傳的嬰兒”,這一次時就猶疑了,到底吃不吃呢?患者到底是“小學生”,對醫生的話總是言聽計從。第二個療程剛進入第三天,奇跡發生!隨著劇烈的疼痛和血尿,“當”的清脆的金屬聲,一粒固狀物擊中了潔白的痰盂。霎時間,我清晰地看見了黃豆瓣似的赭色石子。興奮得蹦了起來,“山高月小,水落石出”!第二天拍了平片,結論“未見明顯致密結石影”。
懷著一顆感恩的心,買了一斤雞蛋糕、一斤羊角酥,去謝老先生。還是昏黃的燈下,老先生正“氣”晚飯。見我手里的東西不高興,我臉紅,連忙說“下不為例,下不為例”。老先生嘆了嘆氣,“怎么都是這樣呢?救死扶傷是我們醫生的天職,病治好了,你沒忘記告訴我一聲,不就是最好的回報么?別的都是多余的!”
那時節的醫患關系很真誠,溝通、理解,唇齒相依,相互體恤,泌尿科醫生、廠醫、藥劑師陳大爺、史先生以及我,都是贏家。時光,一塊臟兮兮的橡皮擦,史老先生的眉目已被擦得模糊不清了,但他那悅耳、充滿仁愛的“給你偏方‘氣氣’”的吳儂軟語,卻時常縈繞耳畔,溫暖。

ICU護士精心呵護患者 武安市第一人民醫院
作者單位/ 安徽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