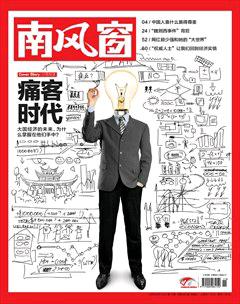“教輔江湖”灰色鏈
覃愛玲+鮑紅
教輔是學(xué)生除教材之外的輔助學(xué)習(xí)資料,常見的有課后練習(xí)冊、考試總復(fù)習(xí),以及作文、閱讀等等。比起家教、培訓(xùn)、學(xué)習(xí)機(jī)等,教輔是比較廉價(jià)實(shí)惠的助學(xué)產(chǎn)品,因而學(xué)生使用最為廣泛。中國近兩億中小學(xué)生,絕大多數(shù)使用教輔。
多年以來,中國的教輔一直處于爭議之中,不僅作為使用者的學(xué)生、家人和教師意見很大,在教輔出版的行業(yè)之內(nèi),多部委出臺無數(shù)文件治理,而成效有限。最新一輪國家關(guān)于教輔的政策起源于2010年,至今仍處于廣泛爭議之中。
緣起
2010年,中國的教輔出版市場開放度較高,隨著在校學(xué)生人數(shù)的持續(xù)減少,教輔市場的競爭非常激烈。教輔的采購方式多樣,各級教育主管、各級學(xué)校領(lǐng)導(dǎo)、學(xué)科組或任課老師“推薦”,以及學(xué)生與家長自由購買等并行。
與此同時(shí),社會上出現(xiàn)了因?yàn)榻梯o市場的品種過多過濫、質(zhì)量良莠不齊,高定價(jià)低折扣,誘使學(xué)校過量采購,加大學(xué)生課業(yè)負(fù)擔(dān)等情況,包括一個(gè)小學(xué)生因36元的教輔費(fèi)自殺等,媒體和政府內(nèi)部的上報(bào)材料中也多次出現(xiàn)相關(guān)信息。
國家相關(guān)領(lǐng)導(dǎo)人于是責(zé)成有關(guān)部門進(jìn)行治理。由此,相關(guān)部門進(jìn)行了一輪近年來最嚴(yán)厲的教輔治理。治理的思路認(rèn)為由學(xué)校推薦的教輔存在的高碼低折等問題,是市場失靈的表現(xiàn),需要更高層次的行政干預(yù)來解決。
教輔跨教育與出版兩界,出版和發(fā)行在出版界,編寫、評議和選用則在教育界,雙方關(guān)系復(fù)雜,因?yàn)榭缃纾哟罅巳藗冋J(rèn)識問題的難度。
作為專業(yè)人士,2011年6月,筆者參與起草了原國家新聞出版總署關(guān)于教輔管理文件的初稿(非最后發(fā)布稿),并為此進(jìn)行多方調(diào)研。8月,原新聞出版總署正式發(fā)布了《關(guān)于加強(qiáng)中小學(xué)教輔出版物管理的通知》。
而對行業(yè)影響最大的,是2012年2月教育部為首出臺的四部委《關(guān)于加強(qiáng)中小學(xué)教輔材料使用管理工作的通知》(以下簡稱四部委通知),2015年的《中小學(xué)教輔材料管理辦法》便以此為藍(lán)本。其主要措施,是由省級教育部門成立一個(gè)教輔評議委員會,對市場上的教輔擇優(yōu)推薦,并進(jìn)行評議公告;各地市的教材選用委員會從省級評議公告中,選出一套教輔“推薦”給學(xué)校,由學(xué)生“自愿”購買。
四部委通知中還有一條規(guī)定是,根據(jù)他人享有著作權(quán)教科書編寫出版的同步練習(xí)冊,應(yīng)依法取得著作權(quán)人的授權(quán)。這一規(guī)定對行業(yè)影響巨大,引起了廣泛爭議。
以這兩條措施為核心的教輔管理政策沿繼至今,構(gòu)建了一個(gè)全新的中國教輔市場乃至出版市場利益格局。此后幾年中,這些政策的落地和實(shí)施,在出版界和教育界一直都有著廣泛的質(zhì)疑聲。
按照以上的規(guī)定,能夠進(jìn)入評議的同步教輔,數(shù)量極其有限,通常每省只有1-3套。到了各地市的“推薦”目錄上,就只剩下1套。
在這種情況下,雖然通知中也明確要求要堅(jiān)持學(xué)生的“自愿原則”,但在實(shí)際執(zhí)行中,由于許多地市下發(fā)的目錄上,只有1套同步教輔,也就是說,學(xué)校只有選擇這1套的“自愿”。
這樣,推薦成了強(qiáng)制,學(xué)校一級都已沒有了選擇權(quán),學(xué)生自愿購買更成一句空話。實(shí)際上是由省市一級教育機(jī)構(gòu)完全決定了下屬各地所有學(xué)校應(yīng)該使用的教輔材料內(nèi)容。
被教輔綁架的教學(xué)
遠(yuǎn)離教學(xué)一線的省、市教育主管部門決定了教輔選用的權(quán)力,而直接使用教輔、最了解教學(xué)需求的學(xué)生和老師卻無權(quán)自主選用。這初聽起來有點(diǎn)荒誕,卻是幾年來近兩億中小學(xué)生面臨的現(xiàn)實(shí)。
筆者隨機(jī)調(diào)查了全國各地不少中小學(xué)校老師和學(xué)生、家長后發(fā)現(xiàn),由于各城鄉(xiāng)之間、校際之間教育發(fā)展差異很大,加之近年國家倡導(dǎo)課堂教學(xué)改革,教學(xué)日益?zhèn)€性化,這種情況下,要求全市甚至全省選用同一套教輔,完全違背了教學(xué)規(guī)律,令教師在教學(xué)中無所適從。
更嚴(yán)重的是,許多通過省評議的教輔靠行政壟斷市場后,無心產(chǎn)品質(zhì)量,內(nèi)容陳舊,多年未變,與現(xiàn)實(shí)教學(xué)相差甚遠(yuǎn)。與一些緊跟教改變化、不斷更新的被市場所認(rèn)可的品牌教輔根本無法相提并論,嚴(yán)重影響教學(xué)質(zhì)量。
雖然沒有明文規(guī)定學(xué)校必須購買評議上的教輔,但由于負(fù)責(zé)評議事務(wù)的教育部門是學(xué)校的上級主管單位,不購買經(jīng)常會給學(xué)校引來麻煩,所以多數(shù)學(xué)校都會征訂評議中的教輔。一些地方教育主管部門甚至在完全不征求學(xué)校或者老師意見的情況下,自作主張選擇一套,直接隨教材發(fā)到學(xué)生手中。
在這種情況下,作為教學(xué)一線機(jī)構(gòu)的學(xué)校推薦雖然大受打擊,但不少學(xué)校為滿足自己教學(xué)需求通常會再推薦購買。老師往往只把被迫征訂的評議上的教輔作為課堂上的練習(xí),學(xué)生主要練習(xí)的還是在市場上重新購買的教輔。有的學(xué)校無奈訂購了評議中的教輔后,甚至不發(fā)給學(xué)生,堆在庫房內(nèi),成為一堆廢紙。
為了迫使學(xué)校只使用經(jīng)過自己評議的教輔,有的教育主管部門以紅頭文件規(guī)定,對于學(xué)生和家長自己購買的教輔,老師不得統(tǒng)一布置、評改和講解。例如,有的地方規(guī)定,如發(fā)現(xiàn)有2/3以上學(xué)生使用目錄以外的同一本教輔,即視為教師推薦,要追究教師責(zé)任。
有的學(xué)校因?yàn)閺?qiáng)烈抵制,受到上級部門的刁難,三天兩頭派人到學(xué)校檢查,甚至翻查學(xué)生的書包。很多地方都有類似的查檢教輔使用情況的“稽查隊(duì)”。這種對于自己并不了解的一線教學(xué)情況,查禁到具體的教室的現(xiàn)象,對基層教學(xué)形成了嚴(yán)重的干擾。
省里推薦不適用,又不允許學(xué)校購買其他教輔,否則就要受查處。一些地方的教師迫于無奈,進(jìn)行了令人感慨萬千的“創(chuàng)新”,即老師自己購買教輔,然后編題,再復(fù)印給學(xué)生使用,這樣,除加大了老師的工作量,并不便宜的復(fù)印費(fèi)和粗糙的復(fù)印資料,讓認(rèn)真教學(xué)的一線教師直接由數(shù)字時(shí)代,被打回去“復(fù)印”時(shí)代,一線的教學(xué)不勝其煩。
另一個(gè)情況是,由于許多重點(diǎn)學(xué)校比較強(qiáng)勢,很少征訂評議中的教輔,但一般的學(xué)校往往迫于壓力征訂。在現(xiàn)實(shí)中造成了更大的教育不公。
從治理教輔亂象出發(fā),主管部門的初衷是為學(xué)生推薦優(yōu)秀教輔。但在教輔征訂的實(shí)際操作中,出現(xiàn)的許多問題,已經(jīng)嚴(yán)重影響到教育發(fā)展。
各級利益鏈剖析
在這種近乎荒誕的教輔使用現(xiàn)實(shí)背后,是巨大的利益鏈條在支撐。
教輔除了關(guān)系到千家萬戶、每個(gè)孩子的教育、社會影響巨大外,還對整個(gè)中國出版界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
教育出版是中國出版業(yè)的支柱。據(jù)各上市出版企業(yè)顯示,教育出版收入占其圖書收入的70%以上。其中份額最大的是中小學(xué)教育出版。由于中小學(xué)教材出版有嚴(yán)格的限制,絕大多數(shù)出版機(jī)構(gòu)收入來自教輔,中小學(xué)教輔的規(guī)模約是教材的兩倍。教輔在當(dāng)前中國出版業(yè)的重要地位可見一斑。
由于目前約80%的中小學(xué)教輔是通過統(tǒng)一采購實(shí)現(xiàn)的,而按照前述以教育部為主的四部委通知的規(guī)定,在其評議目錄之外的教輔,學(xué)校不能統(tǒng)一征訂,這樣,評議目錄的教輔事實(shí)上壟斷了80%的統(tǒng)一采購市場。能上到這些評議目錄,便成了—本教輔成功銷售的關(guān)鍵。
一本能上到評議目錄教輔,通常是由各省或市教研室組織編寫,由具有出版資質(zhì)的國有出版社進(jìn)行出版,然后經(jīng)省教輔評議委員會評議進(jìn)目錄,由新華書店進(jìn)行發(fā)行,而地市教材選用委員會主導(dǎo)選用。在這其中的每一個(gè)鏈條中,都有不小的尋租空間。
教輔的策劃和出版機(jī)構(gòu)上千家,發(fā)行機(jī)構(gòu)有上萬家,而能夠有幸進(jìn)入教育廳目錄的同步教輔是極其有限的。教輔的評議權(quán)與選用權(quán)集中于省、市教育主管部門,眾多的出版發(fā)行機(jī)構(gòu)為公關(guān)他們,進(jìn)行著大量的隱性或顯性的利益輸送,例如,每年的版稅,各種項(xiàng)目或科研贊助費(fèi),培訓(xùn)、報(bào)銷、旅游,教育部門親屬的就業(yè),等等。
據(jù)筆者了解,某東部省份一家出古籍書為主的出版社,為社里創(chuàng)利最多的前三名,都是一些地級教育局領(lǐng)導(dǎo)的親屬。他們可能不會基本的編輯業(yè)務(wù),但憑這層關(guān)系就可以包下整個(gè)地級市轄區(qū)所有的教輔,從小學(xué)到高中,各個(gè)科目,人手一套,人均純利潤好幾百萬元。
教育部門官員因?yàn)榻滩慕梯o受賄而落馬的案件也屢見不鮮。四川省教育廳連續(xù)兩任分管領(lǐng)導(dǎo)(省教育廳原副廳長何紹勇和前任汪風(fēng)雄)都因在教輔領(lǐng)域?yàn)E用職權(quán)、受賄被查。今年4月,廣西新華書店原總經(jīng)理李小勇也因教輔目錄受賄675萬元受審。
因?yàn)橹挥袠O少數(shù)當(dāng)?shù)爻霭嫔绲慕梯o才有資格上目錄,不少具有評議優(yōu)勢的出版社原本已不做高中教輔,現(xiàn)在又開始出版。但高中教輔直接關(guān)系高考,對質(zhì)量要求較高,這些出版社就跟一些市場上知名的民營教輔企業(yè)合作,由民營策劃、組稿、推廣、銷售,自己坐收“牌照費(fèi)”。
另一大得利群體是出版教材的出版社。四部委通知中,要求根據(jù)教科書編寫出版的同步練習(xí)冊,應(yīng)“依法取得著作權(quán)人的授權(quán)”。根據(jù)原國家新聞出版總署和教育部官員的解釋,它的核心是“依法”。由于法律文件沒有直接的表述,多起法院判例的認(rèn)定是,教材的編排體系和結(jié)構(gòu)的設(shè)計(jì)并不具備著作權(quán)法意義上的原創(chuàng)性,侵權(quán)的判定是基于教材內(nèi)容的使用方式和使用數(shù)量。而同步教輔主要是編排結(jié)構(gòu)與教材相同,對教材內(nèi)容的使用并不多,據(jù)此并不能認(rèn)定為侵權(quán)。
雖然并不具有法律依據(jù),但在實(shí)際中,各地都把教材出版社的授權(quán)書當(dāng)作目錄送審的前提,這樣,造成了教材社惜權(quán)限授,只授權(quán)1套或不再授權(quán),使得能進(jìn)入評議目錄的教輔極少。
教育廳目錄的數(shù)量太少,且質(zhì)量難盡如人意,無法滿足基層需要,在巨大的利潤和現(xiàn)實(shí)的需要面前,一些在行業(yè)內(nèi)具有特別資源的機(jī)構(gòu)又開辟一些新的渠道。在發(fā)行方面具有一定壟斷地位的新華書店,就另設(shè)一個(gè)銷售目錄,吸引更多的教輔。
能上新華書店的目錄,也代價(jià)不菲,要出讓近半的折扣,要負(fù)責(zé)銷售,要保證上千萬的銷售量,還要提前交保證金。而新華書店則拿出這近半的利潤的一部分,再分給各地市、縣區(qū)教育局及鄉(xiāng)鎮(zhèn)學(xué)校三級教育部門,以換取他們的支持。
還有不少新華書店在下面營造一種氛圍,稱只有跟自己結(jié)賬才是合法的,不少地方要求學(xué)校只能統(tǒng)一買新華書店的產(chǎn)品。于是,當(dāng)?shù)孛駹I書店實(shí)現(xiàn)的銷售,也要通過新華書店來結(jié)賬。這對新華書店來說,不僅截留了利潤,也做大了規(guī)模,可以用這些業(yè)績來獲取更大的政策支持。
有時(shí)新華書店為保自己出版集團(tuán)的份額,并不愿意幫別人結(jié)賬。于是,一些新華書店負(fù)責(zé)與學(xué)校結(jié)賬的工作人員,就成為地方書店公關(guān)的對象。通常是給他們幾個(gè)點(diǎn)的回扣,由他們代為結(jié)賬。
種種亂象之下,經(jīng)年的實(shí)際調(diào)研和思考之下,筆者給出的解決思路是,教輔的推薦權(quán)交給該科的任課老師。
根據(jù)許多老師和學(xué)生的反映,教學(xué)中確實(shí)需要一套教輔統(tǒng)一練習(xí)和講解。而統(tǒng)一選購都可能出現(xiàn)問題。校領(lǐng)導(dǎo)與教育主管部門的推薦,由于遠(yuǎn)離教學(xué)一線,根本無法保證教輔質(zhì)量和適用性:同時(shí),由于越來越大的銷售量,腐敗問題也更為嚴(yán)重。
而從責(zé)任、利益、監(jiān)督和人性等各種角度分析,任課老師可能出現(xiàn)的問題都是最小的,是有最大利益選用好教輔的群體。作為教學(xué)的實(shí)施者和直接責(zé)任人,一個(gè)任課老師通常帶的班少,能夠形成的銷售不多,利潤空間有限。由任課老師推薦,教輔質(zhì)量和適用性是可以保證的。
同時(shí),為了防止任課老師可能產(chǎn)生的腐敗,強(qiáng)調(diào)任課老師只有推薦權(quán),不能指定渠道,采購由學(xué)生或家委會完成,徹底切斷采購的利益通道,而且一科只能推薦1本教輔。據(jù)調(diào)查,1套教輔基本能滿足80%學(xué)生的需要,個(gè)別學(xué)生需要可以自行購買。為了規(guī)避可能出現(xiàn)的“高碼低折”現(xiàn)象,還可以對所有教輔進(jìn)行最高限價(ji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