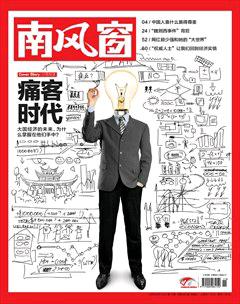痛客:我關注中國人需要什么
譚保羅
痛客,他們能夠從各種社會現象和問題中找到普適性的、亟待解決的關鍵需求,形成并提出痛點。中國痛客大賽的對應的痛客,來自全國各地,而痛點則涉及了當下備受關注的P2P監管、食品安全、新能源汽車、網絡信息安全等熱點。這些痛點的匯聚,很可能形成一個擴張力強大的創業點子和商業方案。
但是,發現需求的痛客并不是“嗅覺敏銳”的商人,某種意義上講,他們是對國家、社會和家庭有著擔當的社會中堅人群,發現痛點并非基于逐利,初衷更多的是來自于推己及人的人文關懷。
籍中蘇:為中藥提煉“科學化”疾呼
61歲的籍中蘇是國內頂尖的消化內科專家之一,也是貴州省消化內鏡學會副主任委員。他看起來比實際年齡年輕得多,健談、風趣,邏輯清晰。
他提出的痛點是新藥研發的“瓶頸”問題:—方面,在很多領域,新的致病因素不斷引發新的疾病,或原有疾病的發病率大幅增加。更嚴重的是,原有疾病抗藥性不斷增強,使得“藥效”不斷降低。
但另一方面,在人類面對艾滋、寨卡、SARS、埃博拉等疾病的時候,由于資金、技術和藥企的逐利傾向等因素,新藥研發效果并不佳。因此,形成一個疾病“版圖”不斷擴張,藥物研發卻嚴重滯后的“反差”。
在中國,新藥研發的“瓶頸”更明顯。由于地區分割的問題,中國的制藥企業呈現分散化和規模小的特點,多數藥廠都沒有足夠資金、意愿去研發新藥。現實情況是,仿制藥成為了醫藥企業藥品“研發”的主流模式。
籍中蘇對《南風窗》記者分析,新藥研發耗時長、花費大是一個客觀事實,但不妨換個角度想問題——我們并沒有充分利用中藥的寶貴資源。目前,中藥“研發”的方法存在兩個缺陷:一是品種選擇上相對盲目,范圍太廣、流程繁雜;二是流程傳統,費時費力,投資巨大。
目前,中國中藥的“提煉”只有兩個方法。一是“方劑照搬”,簡而言之,就是中藥大夫開出一副藥的方劑,醫藥企業按照藥方比例對中藥材進行混合,制成成藥。實際上,這種模式就是把“熬中藥”機械化而已。比如,便捷藥店到處有售的六味地黃丸,就是采取的這種模式。
另一種模式是“單藥提煉”,即只對某一味藥進行提煉,提煉其有用物質,進行大規模生產。“青蒿素”就屬于這種模式。此外,患者耳熟能詳的柴胡注射液、清開靈、炎琥靈、穿心蓮都屬于這種提煉類中藥。
這兩種模式中,真正的創新并不多,這些混合方劑和單藥是現成的“研發成果”,也不需要進行知識產權保護,因此很多時候都是藥企直接復制使用。這對藥企來說,不需要研發投入,是最省錢的制藥模式。
但這兩種基本上不需要研發投入,只對現有方劑進行處理的模式之下,中藥其他未被開發的寶貴資源卻被白白浪費。對此,籍中蘇深感痛心。
籍中蘇認為,要全面從我國中藥文化汲取資源——包括中草藥、苗藥、藏藥、單方、驗方等,必須徹底改善傳統的制藥方法。對此,籍中蘇還設計了一個優化后的研發流程:先是初篩,從初步選定的方劑或藥物中提取相關汁液,對特定的和相關的細菌、病毒、癌細胞等進行藥敏試驗。
第二次篩選:篩選掉無效或效果不好的,對有效的方劑或藥物進一步精制純化,進行動物模型試驗,進一步了解效果和安全性。
第三次篩選:再純化后,以醫院制劑和協定處方形式,先口服,再肌注,再靜注給藥,觀察療效和安全性,積累病例。在保證效果和安全后,申報新藥,批量生產。
籍中蘇坦言,要解決這個痛點,需要藥企、科研院所、政府的“合力”才可以完成,也需要一定的投入,因此需要國家政策的大力支持。
籍中蘇曾任六盤水市人民醫院黨委書記、院長,還擔任過六盤水市衛生局黨組書記、局長這樣的行政工作。他認為,中國醫療和藥品研發的創新,應該基于中國的國情而定。痛客大賽就是一個非常符合中國國情的平臺。
籍中蘇對《南風窗》記者講了一個故事:在上個世紀,中國鄉間的“赤腳醫生”給患者治療“拉肚子”時,會給患者吃“鋇餐”。久而久之,很多患者反映,吃了“鋇餐”之后,不光拉肚子好了,而且以前的胃疼也好了。
這是為什么?在當時的中國,沒有人對此深究。因為當時沒有胃鏡,無法判斷引發胃病的原因,所以中國的赤腳醫生索性將“鋇餐”作為了治療胃疼的常用藥物。但后來,澳大利亞人巴里·馬歇爾發現,原來是“鋇餐”可以殺滅消化系統的幽門螺桿菌。為此,他獲得了諾貝爾生理學獎。
籍中蘇不無遺憾地說,中國當時有數以十萬級的赤腳醫生,卻沒有一個人對此有過“深究”或者“較真”。如果當時有痛客平臺這樣鼓勵“深究”社會痛點的機制,獲得諾獎的可能會是中國人。
陳聽:讓農民工“血汗錢”拿得更踏實
陳聽是貴州雙龍航空港經濟區政法與社會工作局行政執法處負責人,他提出的痛點可以說是“社會之痛”——農民工被欠薪如何高效、妥善解決的問題。
據陳聽透露,根據貴陽市勞動監察部門近3年的統計數據,拖欠農民工工資占據全市所有欠薪事件的90%以上,每年涉及的金額在四五億元左右。2015年的金額最高,達到了6億多元,涉及的農民工多達4萬人。
碩士畢業的陳聽一直在政法系統工作,多年和這一類事件打交道的經驗讓他意識到了問題的重要性。為此,他一直在思考,是否可以給出一個有效的解決方案。
農民工欠薪的問題不光是貴州、貴陽的問題,而且是全國性的問題。目前,中國大約有2.5億農民工在各地從事各種各樣的工作,他們是國家建設的重要力量,保障他們的合法權益,這是政府部門的職能。與此同時,預防或者妥善解決這類事件能夠降低社會成本,也是維護社會穩定,推動改革深化的前提之一。
陳聽說,在討薪事件中,一個常見的“疑難雜癥”是薪資的數據不客觀、不準確。他對《南風窗》記者舉例說,一個建筑工程會層層轉包,到最下面的,帶著幾十個農民工的最低層級“包工頭”可能已經轉包了近十次。
由于工作量直接和薪資掛鉤,在每一個層級,都有人會虛報、瞞報,這樣最后到了最上級的施工單位,往往會因為數據對不上而扯皮。實際上,除了施工單位發不出工資來,或者分包商“跑路”等原因,數據“扯皮”也可能是欠薪事件的導火索。
陳聽還表示,在全國的一些討薪事件中可以看出,勞動監察部門對于這一類事件幾乎都是“事后解決”,而很少拿出“事前預防”的辦法。“事件集中爆發,監察部門人手有限,這時常讓監察部門很被動。”陳聽說。
善于觀察的陳聽還發現一個問題,即農民工欠薪的群體性事件一般多發生在三個時點。一是開學前后,二是春節之前,這兩個時點主要是因為農民工子女開學要繳納相關費用,和春節返鄉討薪。第三個時點則是“兩會”前后。某種意義上講,農民工在討薪問題上已經有了“經驗”,即懂得選擇“特殊時點”,從而吸引社會的關注。
因此,討薪問題其實是一個具有社會普遍意義的重大痛點,事關社會穩定的大局。“痛”在急需一套完整的數據系統,既能有利于薪資數據的準確,維護農民工的利益,又能提前對監察部門予以有效的“預警”。
目前,陳聽的這一痛點已有創客按手,一套基于虹膜識別技術的數據平臺成為了解決方案。
石木旺:發展中國人的無線充電技術
石木旺是鼎木清源(北京)科技有限公司的負責人,他提出的痛點是,中國發展電動汽車必須首先解決電動汽車“無線充電”配套的問題。他告訴《南風窗》記者,之所以提出這個痛點,來自于他對行業的三個判斷。
新能源汽車是一個世界性的潮流,主要分為純電動和油電混合兩個分支。在石木旺看來,中國未來的方向一定是純電動汽車,而不是油電混合。
因為,在油電混合領域,日本、美國的技術較為成熟。但在純電動領域,中國和發達國家幾乎處于同一起點,甚至領先于后者。在國內,中國已經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純電動汽車的產業鏈,從整車、零部件到充電配套裝置,中國都有很多成熟的規模化企業和具有競爭力的技術。中國基于壯大和扶持國內產業的目的,也必然會選擇走純電動汽車這一條路。
實際上,石木旺的這種看法是完全有道理的。一個簡單的例子是德國,該國之所以決定在未來全面廢棄核電,而改用其他清潔能源,其中重要的原因在于,由于歷史原因,德國在核電領域的技術水平遠不如鄰邦法國。因此,全面廢核,另起爐灶,這是一種國家層面的產業競爭策略。
石木旺的另一個判斷是,電動汽車領域民營資本的空間越來越大。2014年,國家電網向社會資本開放分布式電源并網工程和電動汽車充換電設施兩個市場領域,這意味著在2020年將可能撬動2000億元的一個市場規模,而分食蛋糕的主角是民營資本。
第三個判斷則是無線充電技術和設備會有巨大的成長空間。“舉個例子,在立體停車場內,樹立一個有線充電樁會影響空間的使用,無線充電技術就顯得很重要。”石木旺認為,某些特殊的“中國國情”也意味著無線充電的市場空間。
他對《南風窗》記者舉了一個真實案例,在西部某省,一項幾百個電動汽車無線充電樁的建設項目突然被領導否定。后來了解,被否定的重要原因之一,竟然是當地有人擔心充電樁設備價值昂貴,容易被偷盜,從而引發安全隱患和社會問題。
石木旺表示,自己之所以提出這一痛點,在于看到這一痛點后面的產業機遇,希望更多“有辦法”的技術人員、創業者—起解決這一電動汽車產業在“基礎設施”方面的瓶頸。純電動汽車,這是中國產業界難得的“彎道超車”機遇之一,需要痛客的“想法”,也需要創客的“辦法”。張巨鵬:食品安全的源頭之“痛”
今年3月,在收到“痛客大賽”即將舉行的消息的時候,張巨鵬認為是將自己多年的想法進行梳理的時候了。
張巨鵬在工商系統工作了20多年,目前是甘肅白銀市勝利路工商所的副所長。勝利路工商所的管轄區域屬于當地的城鄉結合部,“農耕文明”、“工業文明”和“商業文明”在這里交匯,這里是一道中國食品安全監管最富有代表性的截面。
在各處市場,新鮮的蔬菜、牛羊肉,禽類,還有飲食小攤的鮮炸食品,散發著各式各樣的味道,夾在空氣之中,展示了西北飲食樸實、原生態的一面。但在食品安全的監管上,張巨鵬和他的同事們絲毫不敢松懈。
作為一名流通領域的一線監管人員,張巨鵬對食品安全有著相當的“發言權”。他不無感慨地對《南風窗》記者說,數千年以來,只有新中國真正解決了老百姓能夠吃飽的問題,這是非常值得驕傲的偉大成就。但我們的食品安全領域存在不少隱患,這是一個無法否認的現實。
在銷售終端,比如超市食品專柜、路邊小攤,工商部門的抽檢,發現食品農藥超標的情況并不少見。“一些問題讓人揪心,光靠工商部門一家是沒有辦法解決的,需要形成社會的合力,最好從源頭上解決問題。”
張巨鵬從小在西北農村長大,言語中時常透露出了基層干部的責任心和西北漢子的豪爽以及質樸。他說,自己對食品的“源頭”非常關注。小時候,老家種菜很少打農藥,那個時候,真的是名副其實的“綠色食品”。但現在,全中國的農民超標、超劑量使用農藥的情況并不是新鮮事。
除了農藥使用之外,飼養行業還經常存在使用“催肥飼料”的情況。“只要雞鴨長得肥、長得快,什么都可以喂。”張巨鵬說,業內人士把這一類食品稱為“速成肉”,很讓監管人員頭疼。“一些物質在人體內無法分解,積累之后會引發病變。”張巨鵬說,工商部門對流通領域的食品只能是抽檢,而且局限于人力、物力,抽檢的面也有所局限。
食品問題無疑是真正的“時代痛點”。在最前端的生產環節,并不能完全苛責農民,害蟲的抗藥性越來越強,農民要維持自己基本的收入和生活,使用農藥的確是個無奈的選擇。張巨鵬認為,食品安全是一個社會性的問題,生產者、流通環節以及終端消費者,監管者都需要作出各自的努力。一個真正的解決方案,既要從嚴治理,也要考慮相關方面,比如農民的利益。
對于自己提出的痛點,張巨鵬坦言,解決的難度很大,但并非完全不可能。從縱向看,這是一個涉及各個環節的問題。從橫向看,也是一個全國性的問題。因為食品、飼料的流通是全國性流通,需要在整個國家的范圍內,形成社會的“合力”,共同找到這個痛點的解決方案,這也是他參加中國痛客大賽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