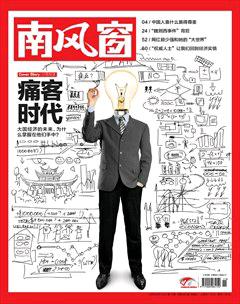“權威人士”讓我們回到經濟實情
譚保羅
5月9日,《人民日報》一篇對“權威人士”的專訪引得財經界紛紛刷頻。在這篇題為《開局首季問大勢——權威人士談當前中國經濟》的文章中,“權威人士”直指中國經濟領域的關鍵之處,語言風格更被網友稱為“通俗”、“霸氣”,還“接地氣”,以至于給人“似曾相識”的感覺。
從文章來看,這位“權威人士”對中國當前經濟形勢的把握,非常準確,對未來經濟形態的判斷,也極具前瞻性,是一篇深諳中國國情,為廣大投資者、企業家、政府官員以及普通國民的“解惑”之作。
更重要的是,“權威人士”盡管相當“權威”,體現了很強的政府意志,但其觀點充分體現了一種“市場導向”,即讓市場在要素資源的配置中發揮決定性的作用;同時,還對近期中國經濟的一些權力主導的提振之策進行了“反思”,這是一個耐人尋味的信號。
政策反思
“權威人士”對近期一些經濟策略的反思,甚至有些“不客氣”,這不尋常。
中國經濟真正的下行,可以說是從2014年開始的,這一年,我國GDP同比增長7.4%,這個增速是1990年以來的新低。在金融海嘯之前的2007年,這一數字是14.2%。也就是說,7年的時間,中國GDP增速幾乎滑落為原來的一半。
2015年,中國的GDP增速終于“破七”,國家統計局的數據也承認,中國經濟同比增速為6.9%。GDP僅僅是一個人為統計的數據,它并不能代表正在發生的危機。但在現實的經濟領域,一些“特殊行業”的消極信號則影響著國人的信心。
一線城市房價直線上升,二三線城市樓市去庫存緩慢,過剩產能和僵尸企業困擾著一些地方和行業。同時,銀行壞賬攀升,利潤下降,一些海外投資者紛紛清空中國的銀行股。股市更換了最高監管長官,托市政策紛紛出臺,甚至明確推遲了注冊制的施行,但上證綜指卻依然在3000點左右徘徊。
顯然,作為“經濟發動機”的房地產出了問題。房地產作為中國經濟名副其實的支柱產業,它是地方政府賴以生存的“財源”,也是銀行資產負債的主要配置行業。同時,它還是其他行業,比如鋼鐵、水泥等行業的“產能消化器”。
這個行業出問題,整個經濟會震動。因此,近期一些提振經濟的策略,本質上就是如何重振房地產,去除二三線城市的庫存,從而帶動其他產業的復蘇。這個依靠房地產提振經濟的“中國式邏輯”,從上世紀90年代末應對亞洲金融危機開始,一直屢試不爽,被一些官員奉若神明。但現在,事情正在發生變化。
前段時間,中國財經領域發生了一件耐人尋味的事,足以折射當前財經官員的“生態”、“心態”,以及中國經濟面臨的困境。今年2月,央行行長周小川在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相關記者會上,答記者問時說了一句:“個人住房加杠桿邏輯是對的。”
隨后,各種關于中國央行行長認為“加杠桿是對的”報道紛至沓來,認為這是新一輪貨幣“大放水”的明確信號。在一些報道中,可以明顯看到公眾對財經官員的質疑,貨幣當局的最高負責人怎么能如此輕率地說“加杠桿是對的”呢?
其后,兩位央行副行長對周小川的話專門進行了解釋。央行副行長易綱說,貨幣政策穩健的取向沒有改變。另一位副行長潘功勝則更直截了當地說,當時,周小川的回答是“你提問的邏輯是對的”,并沒有說“房地產加杠桿是對的”。
不過,周小川當時的回答并不是只有這句話。周小川當時還闡述了兩個關鍵點:其一,個人住房貸款在中國銀行系統總貸款的比重偏低,有的國家占40%~50%,中國只有百分之十幾,所以有很大發展機會。其二,中國個人房貸的首付比例原來是30%,現在降低是有空間的。今后,可能會考慮給銀行更多自主權,讓他們來制定首付比、利率。
顯然,任何稍有常識的人都能看出,貨幣當局負責人在公開場合闡述這兩個關鍵點,到底意味著什么?那么,中國到底要不要加杠桿,到底加多少,加到什么程度?這是所有人民幣使用者的擔憂。
“權威人士”對“加杠桿”問題給出了明確回答,其用語堅定、通俗,完全站在了普通中國人認知方式,以及利益立場的角度考慮問題。“樹不能長到天上,高杠桿必然帶來高風險,控制不好就會引發系統性金融危機,導致經濟負增長,甚至讓老百姓儲蓄泡湯,那就要命了。”
“權威人士”還形象地指出,中國不能也沒必要用加杠桿的辦法硬推經濟增長。“最危險的,是不切實際地追求‘兩全其美,盼著甘蔗兩頭甜,不敢果斷做抉擇。比如,一些國家曾長期實施刺激政策,積累了很大泡沫,結果在政策選擇上,要么維持銀根寬松任由物價飛漲,要么收緊銀根使泡沫破裂。”
“權威人士”的話已經很明確。有解讀認為,“權威人士”對加杠桿的論斷,是指出了中國未來經濟復蘇的“方法論”。不過,結合當前的經濟形勢、微觀金融生態和投資者心理,“權威人士”對加杠桿的解讀,意義更多在于穩定投資者的預期,重塑國民對中國經濟的信心。
因為,信心在現在比什么都重要。
信心之戰
如果用一句話形容當前的金融形勢,那么必然是“肉爛在鍋里”。
一方面,中國對資本外流采取了嚴格管制,老百姓多數的錢只能留在國內配置資產。另一方面,隨著國內經濟下行,國內資產(未上市公司股權、股票、銀行存款和房產等)的價值有著明顯的貶值趨勢。因此,資金必須要找到一種最可靠的資產進行配置,企業股權、股票越來越缺乏吸引力,而負利率又讓銀行存款每天都在貶值。那么,唯有一線城市的物業才能成為資金集聚之地。
于是,一個“反調控”的經濟現象出現了。中央希望二三線城市去庫存,但結果是部分一線城市的房價高到離譜,二三線卻去庫存緩慢。要知道,這種“反調控”的現象在以前很少出現。
可能有人要說,以前中央不斷調控樓市,房價卻不斷上漲,這不也是“反調控”嗎?這完全是兩回事。以前的樓市調控,很大程度只是某些部門和地方政府在“唱雙簧”,調控樓市最有用的信貸、稅收手段一直“溫溫吞吞”,投鼠忌器。
但這一次不一樣,政府在首付比例、信貸利率等方面大幅度放寬了二三線城市的買房要求,但依然效果不佳,而一線城市盡管拿出了調控樓市各種手段,但樓市依然從容地完成了新一輪“階梯式上漲”,并且把房價鎖定在了一個新的價位,看起來非常穩固。
“反調控”問題不光影響了國民對政府宏觀調控能力的信心,更嚴重的問題是,一線城市的房價暴漲,將危及中國實體經濟的根本。
一個不容否認的事實是,中國最好的實體企業都集中于中國房價最高的地帶,北上廣深,還有它們周圍的衛星城市。資金不斷“對調控說不”,蜂擁到這些城市和周圍地區,將對實體經濟產生嚴重的擠壓效應。
在深圳樓市結束新一輪狂飆之后,華為創始人任正非接受新華社采訪時,非常含蓄地指出,“深圳房地產太多了,沒有大塊的工業用地了。”“生活設施太貴了,企業就承載不起;生產成本太高了,工業就發展不起來。”
任正非的話說出了中國企業家的心聲。華為這樣的公司,目前尚未明確進入地產業,但其他實體巨頭早已在地產行業風生水起。比如,中國絕大多數家電企業旗下都有一家以自己名稱“打頭”的地產公司。
除了企業進入房地產逐利之外,個人投資者進入樓市進行資產保值的熱情并沒有改變。可以說,中國國民早已陷入了一種對貨幣“大放水”的習慣性恐懼之中,一線城市的房價高漲,購房者在賣房者臨時加價數十萬的情況下,依然果斷下單。如果不是出于恐懼,一個工薪族斷然不會如此“慷慨”。
因此,可以說,當前中國經濟最大的問題之一是信心問題。“權威人士”的這篇訪談中,多次提到“信心”二字。提振信心不是光靠口號,它必須通過兩個關鍵來具體化,其中之一是,破除國民對加杠桿、貨幣大放水的恐懼。另一個,則是對企業家的保護。
“權威人士”提到,現在最關鍵的是通過保護產權、知識產權,使企業家既有“恒產”又有“恒心”。要建立“親”和“清”的新型政商關系,把企業家當作自己人,讓他們充分體會到權利平等、機會平等、規則平等。在一些具體政策執行上,不要盲目翻舊賬,使創業者有安全感。
之前,在政府的各類官方文件中,可以看到各種各樣關于保護企業家積極性的“官話”,但像“權威人士”這樣用最簡單、最通俗的語言,直指企業家最關注的問題——產權保護和政商關系,極為少見。“權威人士”還指出,企業家是優化資源配置、提高供給體系適應能力的主導力量。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亟須發揮企業家的創新精神,包括面廣量大的民營企業家。
除了歐美遇到危機,外部需求下降的外部原因之外,中國實體經濟的下行,最重要的內部根源之一是企業家信心不足,不愿意投資,而是愿意把錢拿到房地產市場逐利。這背后的原因有兩個:一是,對貨幣“大放水”的恐懼,二是對產權保護的擔憂。在這個意義上講,“權威人士”可以說是看到了實體經濟真正的病根,對癥下藥,而提振信心是第一步。
現實主義
縱觀這篇“權威人士”的訪談,回歸現實,一切從實際出發是一個主導思想。
最簡單的問題是,中國要放棄對經濟增長、增速恢復不切實際的幻想。在中國經濟減速之后,不少人認為,中國經濟將面臨一個“U型”或者“V型”曲線。經濟在觸底之后,將很快反彈,重新進入快速增長通道。
但“權威人士”提出,中國未來的經濟增長將是一個“L形”。換言之,何時增速恢復并沒有明確預期。“權威人士”表示,“這個L型是一個階段,不是一兩年能過去的。今后幾年,總需求低迷和產能過剩并存的格局難以出現根本改變,經濟增長不可能像以前那樣,一旦回升就會持續上行并接連實現幾年高增長。”
另外,必須引起足夠重視的是,“權威人士”提到了“經濟分化”的問題。所謂“經濟分化”主要分為兩類,一類是行業、企業的分化,即經濟發展會讓中國涌現很多具有競爭力的行業、企業,而另一些行業則不具備競爭力,將被徹底淘汰和產能縮減。另一類分化是地區分化,一些地區經濟結構健康,產業強大,抗下行能力強,而另一些地區則完全是投資拉動,抗下行能力弱。
第一類分化幾乎是任何經濟體都存在的現象,但第二個分化則極具中國特色。改革開放后,中國一直通過“地方競爭”推動經濟發展,不同地區因自然稟賦、治理能力的不同,迅速拉開了經濟的差距。在中央層面,則不斷通過轉移支付、地區產業扶持等手段進行“調配”,從而維護地區平衡。
在經濟發展的初級階段,這種“調配”是合適的,但過度“調控”和“均貧富”,客觀上也對資源在全國范圍的自由流動起到了阻礙作用。隨著中國工業化進程不斷深化,越來越對要素資源的全國性流動提出了高要求。那么,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必須要開始重新考慮如何重構自己的“區域平衡”政策了。
在經濟轉型的關鍵節點,“權威人士”毫不回避,明確指出了經濟分化以及地區分化的問題。“權威人士”表示,“在新常態下,我們最需要優化資源配置,培育新動力、形成新結構,這意味著分化越快越好。無論是地區、行業還是企業,總有一部分在‘二八定律的分化中得到‘八的好處,脫穎而出,前景光明。”
有統計顯示,從2015年開始,《人民日報》每次刊發“權威人士”相關文章之后,都會出現股市下跌。比如,這次“權威人士”的專訪刊出后,上海綜合指數又下跌2.8%。這種“聯系”和“推論”,顯得有些牽強。因為,中國股市在2015年年中的大股災后,一直都處在密集的小幅度“上升、下跌”波動之中。
但換個角度看,“權威人士”的觀點顯然比中國股市更和實體經濟具有“相關性”,而且遠比后者更能體現實體經濟真正的困惑和問題。“權威人士”數次在黨報上對中國經濟的解讀,都可以看作是一次對中國當下經濟發展的“正本清源”。其指出問題關鍵所在,更重要的是,讓各方面回到中國的經濟現實。
當真正有分量的、客觀的“經濟解讀”打破了那些不切實際的預期,承載著不切實際預期的A股,顯然會做出應有的反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