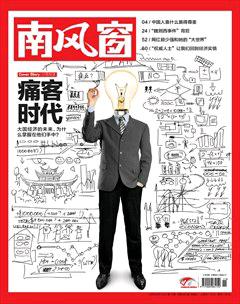青峰猶未見,舟上人已知
李木治
理論的價值,在于被實踐所呼應,對于理論工作者而言,最好的自我價值確認,無過于其研究建樹能夠獲得外部世界的積極回響。
從這個意義上講,顧澗清先生就是一個幸運的理論工作者。1988年,當中國社會對“海上絲綢之路”還沒有表現出多少研究興趣的時候,他便開始史海徜徉,在理論層面深求曲奧,28年從未懈怠。“青舟映霞千帆過”,時至今日,“21世紀海上絲路”已經成為國家戰略的一部分,回首他過往寫下的專著與論文,諸多預見性的理論便燭照當下。
在最近出版的廣東省政府文史研究館“館員文庫系列叢書”中,顧澗清先生所著《青舟集》備受矚目。《青舟集》收納了他30多年來研究和撰寫的大部分文章,細讀此書,可以從中發現他的理論洞見、責任擔當和個人情懷。
在歷史與現實之間
顧澗清現任廣州日報社社長,而數十年來,他的另一個一以貫之的身份是一名學者,他的自稱則是“理論工作者”。
他的研究涉及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傳媒等諸多領域,其中,對海上絲綢之路在現代化背景下的價值的探尋尤為執著。1988年,中國經濟活力已經初步顯現,大批體制內知識分子以“下海”為人生抉擇,整個社會熱情蓬勃又喧囂鬧騰,此時在江蘇連云港工作的顧澗清,卻一頭扎進了“海上絲綢之路”這一冷門的研究課題當中。
說起他與海上絲綢之路研究的結緣,還源自趙樸初先生的一首詩:海上絲綢路早開,闕文史實證摩崖。可能孔望山頭像,及見流沙白馬來。這首寫于1981年的詩歌,把位于連云港海州區的孔望山與古代絲綢之路進行了實體的意象連接,形成了一種穿越時空的文化想象,在當地被人們津津樂道,也一樣打動了顧澗清。
當時已經如火如荼的改革開放,放到中國近代以降的歷史大視野中,可稱為繼“洋務運動”之后中國人的第二次集體性的“開眼看世界”。與百年前的第一次“開眼看世界”不同的是,1980年代以來,在學習外部世界先進的科技與制度的同時,有識之士也開始探究如何在對外開放中堅持中國的主體性。而對更早以前中國仍是世界中心之一時與世界的關系的研究,有助于賦予當下的對外開放以主體性,具備主體性的開放發展,才更有對路徑進行理性設計的能力。
顧澗清對“海上絲路”的研究踏準了這一被忽視的需求,在重視其歷史文化價值的同時,更強調探尋它的時代價值
如何讓研究的課題對中國新時期向海而生的開放發展進行主動的介入,而不是故紙堆中的自娛自樂。到1990年顧澗清已經出版了多本著作,他與北京大學白化文教授主編了《論連云港與海上絲綢之路》,季羨林先生專門為此書題詞:“深入開展對海上絲綢之路研究,促進中外文化交流。”這一年他還出版了專著《沿海開發經濟簡論》,他在書中提出了“在沿海經濟特區和開放港口城市辟建自由港區”的設想,事實上就是今天的自由貿易區的理論呈現。
2013年習近平主席分別在出訪中亞和東盟時提出了“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構想,后被概括為“一帶一路”,并被寫入次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此時的中國,全方位的自信已經在過去35年的發展基礎上重新建構起來,“一帶一路”就是一種完全主動的開放。幾乎在一夜之間,顧澗清20余年青燈如豆的研究領域,成了國內的顯學,他在其期間的知識與理論積累,到了厚積薄發的時候。2013年,“海上絲路”涉及的廣東、福建、浙江、江蘇、廣西等省紛紛成立了研究機構。
基于對“海上絲路”的多年研究,2002年顧澗清就在《廣州日報》發表了《海上絲路應申報世界文化遺產》—文,當時由于課題依舊冷清,未獲得更大回應,而現在這一申遺計劃也早已啟動,顧澗清成為核心專家。
“一帶一路”的倫理思索
世上并無“先知”,但把握了正確的方向和方法的研究者,有可能借助邏輯推論,意外地組建出未來的事實架構。
順著“海上絲路”的研究軌跡,顧澗清在1992年出版了《中國陸橋經濟》專著,他在書中提出,陸橋經濟是在江河經濟、海岸經濟基礎上形成的以高速鐵路、高速公路為核心的一種新型的國際經濟類型,是世界經濟發展的第三里程碑。此時,中國離第一次鐵路提速還有5年時間。如今以“陸橋經濟”為關鍵詞在百度學術中搜索相關文獻,顧澗清有多篇文章發表于1995年,是所得文獻中時間最早的一批。
彼時的這位青年才俊,顯然無法預知今日中國高鐵技術的飛速進展以及高速鐵路的迅速普及,但卻在冥冥中透過歷史把握了未來。
《青舟集》中收入了一篇《南風窗》與顧澗清的對話文章,在其中可以看到他研究方法的吉光片羽。談及陸橋經濟時,他說:“一個新型經濟時代的出現總是與人類掌握科學技術的水平聯系在一起,如果說農業時代是鐵木工具的產物,工業時代是蒸汽機的產物,那么,我們現在的后工業時代就是高新科技的產物,與此相對應,從經濟發展的環球空間布局看,人類已經跨越了江河經濟時代和海岸經濟時代,那么在高新科技的推動下,就應該進入陸橋經濟時代、向大陸深處進軍了。”
顯然,他對大歷史的打量運用了社會學的方法,尤其重視工具對社會經濟、文化的建構作用。江河經濟、海岸經濟和陸橋經濟,在物質層面上都依托于工具的效率。
不過,作為一名社會科學研究者,顧澗清沒有陷入工具崇拜,反而處處強調價值理性。當他最為熟悉的“海上絲綢之路”帶上“21世紀”這一磅礴的前綴,從而變成一種人人都想要加入自身的解釋的時候,國內外經濟學圈子里開始流行中國的“一帶一路”戰略是為了消化過剩產能的說法。顧澗清對此表示明確反對,認為不應把“一帶一路”和產能過剩直接掛鉤,產能輸出只是一種單方意圖,與“一帶一路”所主張的合作共贏、區域經濟一體化不同。
“我的理解,‘一帶一路的發展主線是經貿合作、共定規則、人文交流和禮尚往來:發展重點是基礎設施的互聯互通、貿易投資的便利化和編織更加緊密的共同利益網絡:發展方式是廣交朋友、共同探討、平等協商、循序漸進:發展目的就是共同建設、共同受益,在合作共贏中打造命運共同體。”
這事實上包含一種對中國在新時代主動、自信地對外深度開放的倫理思索。自民族國家誕生以來,西方主導的國際關系理論事實奉行“利益至上”原則,任何國家在國際社會的互動行為都被認作隱含著單純自私的目的。在顧澗清的闡述中可以發現,他骨子里崇尚中國古代的“里仁”傳統,并力圖在國際社會的共處中尋求一種溫情體驗。而這一點,其實也可以在中國對外交往的歷史與現狀中得到事實證據。
“天下己任”的理想
在《青舟集》中顧澗清用一篇文章回顧了自己對“海上絲綢之路”的研究歷程,對于研究的指向,他總結說,人文社會科學就好比是智慧的“種子”,只有在進入決策、貼近群眾、浸潤社會中,才能生根發芽、開花結果。
這句話透露了他的人文情懷:他雖然有著現代化的知識結構和理論方法,但在對知識分子的社會價值的認知上,依然保持著傳統的“以天下為己任”的終極抱負。
盡管今天對“一帶一路”研究程度參差不齊的各領域人士都紛紛出來“分一杯羹”,但他對當前的研究熱樂見其成。究其原因,他在《青舟集》中也說得很明白:“一帶一路”使古老的絲綢之路升華蛻變到了全新的高度,將引領中國人重新發現世界文明,也將會使得世界重新發現中華文明。
“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我撰寫了《論海州灣的綜合開發》、《連云港與海上絲綢之路》、《沿海開發經濟簡論》、《中國陸橋經濟》并得到季羨林先生的題詞鼓勵,到本世紀初為促進廣州海上絲路史跡申遺建言獻策,完成《廣東海上絲綢之路研究》的課題和專著,直到今天創作、策劃大型紀錄片《海上絲路》,凡此種種,歷歷在目。近30年來,我看著海上絲路研究從某一學科分支而漸成顯學,自己的一些研究成果也對相關部門產生了積極推動作用,內心的興奮和欣慰自不待言。”
于他而言,在這一課題上也遠未到結束的時候。“責任擔當、使命使然、情結所系,在研究和傳播海上絲路文明的道路上,我將緊跟時代步伐,不因歲月而變。”
在這個過程中,顧澗清事實上用了將近30年時間扮演了一個潛心學術研究、服務國家戰略的智囊角色,而這一角色也與他的個人理想相吻合。2009年,時任廣州市社會科學界聯合會主席的顧澗清在新華網撰文,呼喚“智庫時代”的到來,提議廣泛聯合所有社科研究機構,使社科界真正成為推進科學發展的重要智庫,為國家民族的進一步發展提供智力支持。
今天,作為新聞傳媒界的領軍人物,顧澗清提出,新聞輿論工作者要擔“文以貫道、成風化人”之責,創“因時而變、隨事而制”之新。他常常對記者們提出的一個要求,就是要“成為一個學者型記者”,惟其如此,才能寫出更有社會價值的文字,創作出真正有思想、有溫度、有品質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