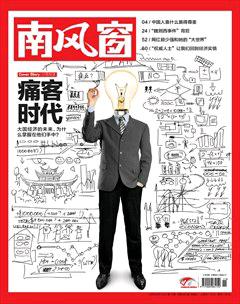市場經濟的“罪惡”與“美德”
林民旺
當下中國社會的道德下滑,問題的焦點經常落在“市場”身上:多少“罪惡”是市場經濟帶來的,又有多少“美德”是市場經濟培育出來?回想一下中國的改革開放史,就不得不讓人唏噓,為了確立或否定“市場經濟”的合理性而進行的辯護,曾經是如此的激烈。
然而,放在更長的歷史視角來看,中國內部對“市場經濟”的爭論,其實是無獨有偶。杰瑞·穆勒的《市場與大師》就展示了資本主義產生以來,那些“白人思想家們”如何言說市場經濟的“罪惡”與“美德”的思想歷程。
人類的行為總是需要給出道德理由,因此選擇一種生活方式或社會體制就需要價值上的判斷。雖然人類社會很早以來就存在商品交換,但是一種嶄新的普遍的社會形式——資本主義——是在18世紀的歐洲才開始站穩(wěn)腳跟。它和過去的差別在于,資本主義是“基于財產私有制度和法律上自由個體之間的交換,主要委托市場機制調配的商品生產和分配體系”。
在資本主義產生前及產生之初,歐洲的精神世界里都是反市場、反商業(yè)的。希臘時期的亞里士多德就認為,追逐財富在道德上是危險的,它會破壞人們對集體公共道德的追求。這種思想與后來的基督教道德是一脈相承的:商業(yè)對于追求美德而言是有毒害的,貿易滋長了欺騙和貪婪,消滅了美德和質樸,使人道德墮落。即便是宗教改革后,新教徒們對貿易的懷疑弱了些,如馬克斯·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甚至認為新教產生了資本主義,但是新教徒們仍舊認為對于財富的追求會威脅到靈魂的救贖。
對于為了獲得利潤而進行的“高利貸”行為(大致就是現在金融的本質),則更是受到嚴厲的批判。當時的歐洲文學作品中,存在大量對高利貸者的嘲諷,如但丁的《神曲》中說,地獄中有一層就是為高利貸者而準備。而莎士比亞的《威尼斯商人》中的夏洛克形象,更是著意塑造出“道德低下”的高利貸者。這種嘲諷和批評都源于資本主義之前的經濟思想中的一般性假設:人類的財富是一成不變的,“金錢不能產生金錢”,因此一人之所得就是另一人之所失。只有通過血汗的勞動才算是工作和生產,而貿易和放貸的利潤都是寄生性質的,不具有生產性。
在早期確立資本主義正當性的思想家中,亞當·斯密人們很熟悉,實際上伏爾泰大概才是歐洲知識分子中最早對資本主義予以肯定的。伏爾泰的時代,歐洲的宗教狂熱仍在繼續(xù),因此他所面對的問題是要實現宗教和解——這一點可以經由市場來實現,因為市場是“一個和平與自由的集會場所”,是一個出于自愿的社團形態(tài),商業(yè)活動為人們的和平共存提供了基礎。伏爾泰也挑戰(zhàn)了基督教和社會道德家們的核心觀點:社會秩序要建立在利他主義的基礎上。他認為,“利己主義的偏好才是社會秩序的基礎”,“要建成一個不追逐自我利益卻能持久的社會是不可能的”。這一思想啟發(fā)并且得到了后來的亞當·斯密、哈耶克的深入闡述。
物極必反。隨著資本主義的迅猛發(fā)展,對資本主義的批判也越來越多。保守主義者們擔心,與市場相適應的價值觀和趨向外溢到人類的其他組織形式中,會破壞國家、社區(qū)、家庭等組織。人們將自身與政府的關系簡單地看作是一種市場關系(契約關系),實質上是一種市場價值觀的過度蔓延。同樣,人們將市場的經濟理性帶到婚姻關系、家庭關系之中。不論是伯克、黑格爾、阿諾德,還是默瑟爾、哈貝馬斯,事實上都在擔憂市場經濟的思想滲透到所有的人類關系之中,進而瓦解人類社會的“溫情”。
歐洲曾經的這些思想爭論仍以其他形式在當下中國繼續(xù)。借用托克維爾之言,“有多少道德體系和政治體系經歷了被發(fā)現、被忘卻、被重新發(fā)現、被再次忘卻、過了不久又被發(fā)現這一連續(xù)過程,而每一次被發(fā)現都給世界帶來魄力和驚奇,好像它們是全新的,充滿了智慧。之所以會如此,并不是由于人類精神的多產,而是由于人類的無知,這種情況簡直令人難以置信”。
另外一個插曲,也許值得一提。中世紀被基督教會剝奪了土地所有權的猶太人,不得不轉向從事高利貸的金錢交易。加上他們不信仰基督教,由此背負上了難以擺脫的“污名”,被形容為貪婪、骯臟。在資本主義沒有得到“正名”前,對資本主義的批評實際上加在了猶太人身上。而隨著對市場的接受,反猶主義和其他排他性意識形態(tài)也幾乎同時衰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