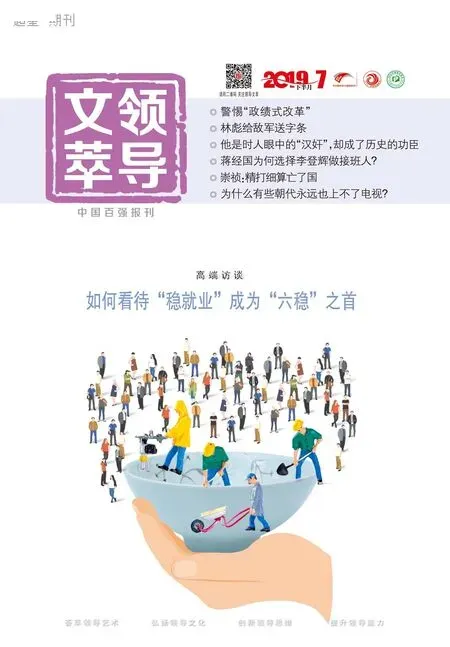十八世紀官場中的“結黨”行為
孔飛力
乾隆有著暴戾兇殘的另一面,這表現為他對于文人臣子們在種族問題上任何冒犯行為的高度敏感。清代文人們很快便發現,文字可以帶來殺身之禍。一位朝鮮使者在1780年發現,他所遇到的所有人都謹慎小心到了極點:“雖尋常酬答之事,語后即焚,不留片紙。此非但漢人如是,滿人尤甚。”
如果說,“文字獄”還不足以讓批評者三緘其口的話,那么,還有被指控為“結黨”的恐懼!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若是有人反對皇上寵臣的“結黨”行為,他們自己就會被扣上“結黨”的帽子。
整個18世紀90年代,乾隆對于和珅的寵信一直堅定不移,甚至壓倒了他對于朋黨派系活動的敵意。乾隆的政策搞得官員們明哲保身,但和珅的勢力卻靠著乾隆這道護身符,得以在官僚機構中大肆擴張。少數敢于對此提出挑戰的官員,自己都倒了大霉。一直到乾隆帝于1799年駕崩之后,和珅及其一黨才被推翻。
究竟是什么使得“結黨”的指控成為清代統治者手中如此有效的武器?這種指控的力量之所在,部分來自于精英階層自己對于結黨的不齒。清代精英層的大家都同意這樣的看法:17世紀上半夜,正是由于朝廷的朋黨爭斗而導致了明朝的瓦解。
“朋黨”本身便是惡名昭彰。孔子曰,君子“群而不黨”。這為所有執政者阻止部屬們拉幫結派提供了最好的理由。但實際上,在政府的各個層次,拉幫結派的活動卻仍在暗中進行。
18世紀官場中的結黨行為,一般來說并不以關于政策的共同看法為前提,而是建立在宗教、鄉誼和師生同門關系的基礎之上的。從朝廷的角度來看,這些關系中的最后一類是最傷腦筋的,是因為科舉考試是一座名副其實的生產朋黨的作坊。一方面,考官和考生之間的關系創造出了恩師與門生的網絡;另一方面,身居高位的考官們可以利用職權來操縱或“設定”考試結果,這又轉變為朋黨活動的催化劑。在官場之外,結黨活動在中國社會生活的土壤中自發地蔓延開來。宗教、同鄉和師生關系結合在一起,成為結黨的溫床。當朋黨勢力強大到足以制約皇家的權威和資源時,它便成為令統治者們極為頭痛的問題。然而,要鏟除朋黨活動卻是不可能辦到的。給朋黨活動貼上“謀求私利”的標簽,并不能使問題得到全面解決。可是,從權勢者的角度來看,這卻不失為沒有辦法時的一種辦法。只要同“謀叛”稍稍沾邊,人們便再不敢從事協調一致的政治行動了。朋黨活動依然存在,但要在從政時明目張膽地結黨,卻是有著很大風險的。
那么,文人們自己是否對“公共利益是單一的和排他的”這一點存在懷疑呢?從文人們反抗朝廷暴政的一樁命案——17世紀20年代的東林黨運動——來看,并非如此。東林黨事件所涉及的,是文人官員們拉幫結派,下決心要通過控制科舉考試來操縱對于官員的任命并安插私人,從而控制北京的朝政。東林黨人群起吶喊,對太監“閹黨”在朝廷的邪惡專權提出了挑戰。如果我們僅僅將視野局限于東林黨人對于“專權”的不屈不撓的抵制的話,那么,我們便有可能會忽略,他們采取行動的前提其實是自己所反對事物的一種翻版。當東林黨人轉而掌權時,他們反過來對處于自己對立面的官員們進行了無情的鎮壓。無論是權力的分享或對于利益的多元化考慮,在他們的眼里都是不可接受的。在他們看來,公共利益只能有一種,其界定,則是通過以個人德行為基礎的公正言辭而實現的,為了捍衛公共利益而獻身成仁的精神是可以接受的。東林黨運動及其命運所描繪的,是一幅派系斗爭中贏者全贏、輸者全輸的圖景。在這樣的黨政中,能夠使差異得到緩和或調節的機制是全然不存在的。到了清代,東林黨事件成為使黨爭視為損害公共利益和國家穩定的一種前車之鑒。
乾隆一生都對朋黨活動深惡痛絕。他在位初年,必須對付父皇留下來的兩位老臣和他們的親信隨從。到了晚年,盡管他可能認為自己已經鏟除了所有的舊朋黨,并通過恫嚇手段使得無人膽敢建立新朋黨,但實際上,當時他的銳氣已遠不復當年,而和珅之流所從事的朋黨活動又乘機卷土重來,這對帝國的傷害極大。
(摘自《中國現代國家的起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