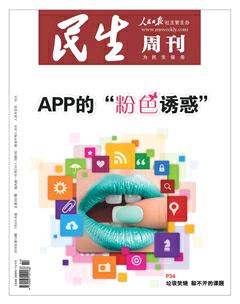賭不起的青春
2016-07-16 08:49:31
民生周刊 2016年13期
大概三個月前,我開始“潛伏”于多款婚戀交友APP中,靜等“粉色誘惑”制造者的出現。
根據預案,在完成對夏東的采訪后,我只要抓住制造者施以“誘惑”的證據,使其與夏東所述互為佐證,報道即為客觀的。但“果兒”敢于從幕后站至臺前,著實讓我有些吃驚。
當然,這也與我的一個失誤操作有關。在做“潛伏”準備時,我分別申請了新的微信和QQ。按照預案,我應該在“果兒”提出加我的微信時,告訴她新申請的微信號。然而那一刻,我卻習慣性地將自己使用了好久且載有自己職業信息的微信號告訴了她。
“你是記者?怎么,你是想采訪我嗎?”事已至此,那就將計就計吧。我記得,“你為什么干這一行”是我向她提出的第一個問題。沉默了大概一刻鐘,“果兒”提出第二天在房山區(北京)見面聊。
我預估了所有可能發生的風險后,要求見面必須在公共場所且地點由我來定。她沒有反對。
兩個小時的面對面采訪進行得沒有障礙。
最后,她告訴我,之所以自愿接受我的采訪,是因為她覺得自己已身心疲憊,沒有了自我。她每日都在惶恐中度過,見到穿制服的,哪怕是明知道對方只是一名保安,她都會額頭出汗。而最讓她擔心的是,她不知道未來的路在哪里。
在回主城區的路上,我思索著該如何展現這不太平凡的人和事。寫人性?“果兒”性本善良。寫社會?社會對她不公平嗎?
最終,我決定還是記錄她的青春成長史。畢竟,生存也好,創富也罷,每個人的青春都只有一次,賭不起,更輸不起。我想要做的,就是通過我的記錄,給像“果兒”一樣迷惘的人以警示。
猜你喜歡
鴨綠江(2021年35期)2021-04-19 12:24:18
考試與評價·高一版(2020年6期)2020-11-02 02:45:24
電子制作(2018年11期)2018-08-04 03:25:42
Coco薇(2017年10期)2017-10-12 19:26:55
中國信息化周報(2016年47期)2017-03-25 17:33:41
時代青年·視點(2016年11期)2017-01-14 19:34:24
Coco薇(2016年8期)2016-10-09 16:46:39
鑿巖機械氣動工具(2016年3期)2016-03-01 04:00:25
中國信息化周報(2015年27期)2015-08-12 22:09:31
中國信息化周報(2015年28期)2015-08-06 22:08: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