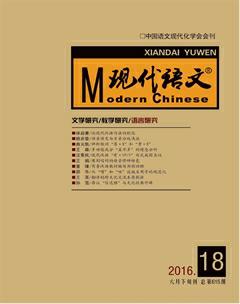國內二語語塊的心理加工機制研究:回顧與展望
摘 要:近年來,語塊的在線加工研究成為一大熱點。研究者運用不同的心理語言學范式考察語塊的加工機制,并取得了豐碩成果。目前的研究主要圍繞語塊的心理現實性展開。本文結合相關理論,回顧了國內外一些重要的實證研究,分析了該領域亟待解決的問題,并對國內未來二語語塊的發展進行了展望,以進一步豐富該領域內的研究,更好地揭示語塊的心理表征及加工機制。
關鍵詞:語塊 二語語塊 加工機制 回顧與展望
一、引言
語塊作為一種常見的語言現象,備受研究者的關注。國內的語塊研究從2000年開始起步,主要集中在語料庫語言學層面,探討其與外語學習的關系(丁言仁、戚焱,2005;繆海燕、孫藍,2005;李太志,2006;王立非、張巖,2006;衛乃興,2007等)。研究表明,語塊的運用可以提高二語水平(廉潔,2001),如提高口語流暢性和準確性(姚寶梁,2004;原萍、郭粉絨,2010)、提高寫作產出質量(陳偉平,2008;陳東嵐,2015)等。然而,隨著認知語言學研究的日益完善,語塊的研究視角也在發生轉型,正從語料庫驅動的內省、離線研究轉向心理語言學實證、在線加工研究,即向更微觀、更精細的方向轉移。對于語塊的在線加工,研究者主要從心理現實性角度展開。
二、相關理論
語塊的心理現實性是指其享有一定的心理表征,而不是按語法規則臨時生成的(Tremblay et al,2011)。該觀點認為,在心理詞庫中,語塊以整體形式表征,又以整體為單位提取,即語塊具有加工優勢,這為“基于使用的語言觀”提供了間接的證據。然而,這與“普遍語法(UG)”的觀點相悖。Chomsky(1957)認為,心理詞庫最基本單位(詞素)以最高效的方式,通過規則而存儲和組合。也就是說,語塊不能進入心理詞庫,必須在詞素的基礎上根據語法規則才能生成。以上兩種截然相反的觀點剛好反映在Van Lancker Sidtis(2012)提出的“語塊的雙加工模型”(Dual-process Model)上。“雙加工模型”包括語塊模式和語法模式。在語塊模式下,是以整體形式表征,無需經過任何語法規則的約束。而語法模式認為,語塊是以單個詞組成,并以精細的語法規則對其進行加工處理。兩者相互作用,相互影響,處于交互狀態。
簡單來說,這兩種觀點的分歧在于,語塊是否可以作為一個整體使用,從而只需經過字詞識別階段,省去中間的句法分析,大大降低認知負荷、提高信息加工的速度。顯然,整體加工的模式更符合經濟性原則。大量的心理語言學實驗表明,語塊是整體表征和加工的(詹宏偉,2012;鐘志英、何安平,2012;易維、鹿士義,2013;桑紫林、張少林,2013;王啟,2015;許瑩瑩、王同順,2015a;許瑩瑩、王同順,2015b)。研究者聚焦于語言的不同層面(語音、語義、結構等),采取多種不同的實驗范式(反應時、眼動、ERP等),證實了語塊的心理現實性(黃四宏、詹宏偉,2011)。本文將采用黃四宏和詹宏偉(2011)的分類框架,結合國外的實證研究,分析國內研究的現狀并進行展望。
三、相關研究
(一)語塊的語音加工研究
語塊在語音方面的優勢主要體現在理解和口頭產出。學者普遍認為,學習者在使用語塊的情況下,理解更加快捷,口頭產出更加流利、表達更準確地道(Wood,2004,2006;Lancker,2004;Schmitt,2004;Kormos,2007等)。國內有學者對此提供了相應的實證依據。
鐘志英(2015)從聽覺在線語法判斷任務和在線朗讀錄音任務的實驗中,從理解和產出兩個視角,考察了中國中級英語水平學習者對英語高頻程式語的加工優勢。結果表明,在語法判斷任務上,被試對三類語塊(高頻程式語、低頻程式語和非程式語)的聽覺加工有顯著性差異,表現在高頻程式語的加工時間最短,其次是低頻程式語,加工非程式語的時間最長,證實了程式語的聽覺加工優勢,且受程式語的頻率調節。在在線朗讀任務上,得出了相同的結論。這充分說明了中國英語學習者在聽覺上對語塊的認知加工優勢,為Wray(2002)的觀點提供了實證支撐:語塊不僅減輕了說話者產出的認知加工負荷,也減輕了聽話者理解語言的加工負荷。(轉引自鐘志英,2015)
詹宏偉(2012)采用音素監控任務(在線)和句子判斷任務(離線),從聽覺加工的角度證實了語塊的心理現實性。在線實驗基本流程是:被試在聽句子時,需要對其中一個特定的音素進行監控,即當被試聽到該音素時,就立刻按鍵反應。離線句子任務要求被試辨認出是否聽過相應的句子,以檢驗是否認真完成在線任務。音素監控任務的基本原理是通過被試對目標音素的監控,推斷出該音素的上下文特征。比如,在被試所聽的句子中,目標語素之前的單位是語塊,如果它的監控反應時較非語塊條件下時短,則可以說明語塊是被整體提取的,即證實語塊的心理現實性,因為在過程中節約了一定的認知資源,可以加快后面音素的加工。實驗確實證明,被試在有語塊句子的條件下,對目標音素的反應時更短,從而為語塊的心理現實性提供了聽覺證據。該實驗設計的不足在于沒有對被試外語水平,尤其是聽力水平進行控制。實驗材料的分組也有缺陷:所有實驗材料分成兩組,一組是語塊句和填充句,另一組是非語塊句和填充句。這就出現一個問題:被試在語塊句上反應時快或在非語塊句上反應慢,可能是個體聽力差異導致的。未來相關的研究應當嚴格控制無關變量,如控制好被試的聽力水平,實驗材料采取交叉平衡(counterbalanced)的處理方法,適當增加句子的數量等。
(二)語塊的語義加工研究
語塊是處于詞匯和句子之間的多詞單位,有其自身的語義。語塊的語義可以是由其組成單位語義的簡單相加(即字面意義),如“for example”這類語塊的語義透明高,易于習得。另外一類語塊的語義不能由其字面意思推導出來,即語義透明度低,如:jump on the wagon。語義透明度低的語塊意義復雜,兼有字面意義和修辭意義,因而常被研究者涉及。endprint
國外的學者也對語塊的字面義和非字面義激活進行了一番探索。Gibbs等人(1997)比較了習語與意義相當的非習語的在線閱讀時間,并考察了各自的語義提取。他們以若干篇英語小故事為實驗材料,其中分別包含一些習語(如:“It was a shot in the arm.”)和與之意義等同的非習語(如:“It was very encouraging.”)。被試(本族語者)要求閱讀故事,并完成一系列詞匯意義判斷任務。研究結果表明,被試在閱讀意義相當的習語句和非習語句上的時間并沒有顯著差異,即加工速度上沒有任何差異。但在語義提取上,習語句中相關詞的反應時比非習語句中的更短,這說明習語語義的理解、提取更加快。Conklin & Schmitt(2008)采用自定步調速閱讀范式,比較了習語與非習語分別在字面義和非字面義上的加工差異。例如,“a breath of fresh air”的字面義是“breathing clean air”,非字面義是“a new approach”。他們將兩種語義分別放入不同的語境中,要求被試(本族語者和高水平二語學習者)閱讀,并設置控制詞串。研究發現,對于本族語和二語學習者而言,無論是字面義還是非字面義,習語的閱讀時間均比非習語短。Siyanova,Conklin & Schmitt(2011)利用眼動技術(eye-tracking)進一步考察了語塊的語義加工優勢。他們比較了高頻習語和非習語分別在字面義和非字面義上的閱讀時間和注視次數。研究表明,無論是字面義還是非字面義,習語的閱讀時間均少于非習語段,注視次數也比非習語少。這進一步表明,語塊具有語義加工優勢。但黃四宏和詹宏偉(2011)在文中指出,這些研究只能在一定程度上說明語塊的心理現實性。因為如果習語在詞庫中是以整體形式存儲和提取,那么習語的非字面義應該是優先得到提取,即閱讀非字面義的速度要快于字面義。顯然,目前還缺少相關的實證研究。
國內這方面的研究還非常匱乏,現在還沒有研究觸及二語語塊的語義加工。但有學者對漢語語塊做了開創性的嘗試,起了很好的鋪墊。張輝(2006)采用事件相關電位技術(ERPs)和語義啟動的范式,考察了漢語熟語語義的在線加工,并把熟悉度和語境這兩個變量納入到研究范圍。具體地講,他的研究考察了熟悉熟語和不熟悉熟語在字面義/非字面義,在正確/不正確匹配語境下的語義加工。其研究發現,熟悉熟語和不熟悉熟語的字面義在任何語境下都能被通達,也就是說熟語的字面義的加工是不可避免的,即使熟悉的熟語也是如此。他還發現,熟悉熟語的加工在FZ引起明顯的P600(與語義加工有關的指標),并有明顯的額葉區電極點被激活。這是由于熟悉熟語的編碼意義總是可以形成適合某一語境(無論是否正確匹配)的心理空間,并與啟動句所形成的心理空間進行對比、重新分析和語義整合。而不熟悉熟語的語義沒有儲存在長時記憶中,被試只好在字面義的基礎上進行分析和加工,無法及時形成心理空間,因此無法與啟動句所形成的心理空間進行重新分析和語義整合,故加工不熟悉熟語在FZ上沒有明顯的P600。因此,某種程度上可以看出,漢語熟語在語義加工上具有一定的心理現實性,并且受到了熟悉度這一變量的調節,表現在熟悉熟語具有明顯的語義加工優勢,而不熟悉熟語卻不明顯。
(三)語塊的內部結構加工研究
語塊是由多個單詞組成的合乎語法的多詞單位,因此有其自己內部的構造。有些學者對語塊的內部結構做了深入的探討。語塊(多詞單位)本身就可以組成一個微型語境,如果某單詞有充分的上下文提示,在閱讀過程中,被試會形成一種閱讀期待,很容易猜測出該詞,因此研究者常采用語塊的末尾詞作為研究對象,因其有足夠的語境提示。Underwood(2004)用眼動記錄儀來研究語塊,其實驗假設為:如果語塊具有心理現實性,語塊末尾詞的注視時間和注視次數都會有所減少。他們讓兩組被試(本族語者和學習者)分別閱讀一些帶有語塊和非語塊的故事,并記錄下同一個單詞(末尾詞)在語塊語境和非語塊語境下的注視時間和注視次數。結果發現,總體上,語塊中的末尾詞注視和注視時間明顯減少。對于本族語者而言,這種差異很顯著;而對于二語者來說,這種差別卻不顯著。這與Conklin & Schmitt(2008)的語義加工得出的結論矛盾:語塊語義加工的優勢在二語學習者身上也能得到印證。但總的來說,整個研究也證明了語塊具有整體加工的優勢,即心理現實性。
除了末尾詞較易識別之外,研究者還認為,語塊中可能存在某一單詞,它會自動激活整個語塊的意義,從而加快了語塊其他單詞的加工速率。Conklin & Schmitt(2008)做了成功的探索,驗證了這一觀點。他們以一些自編的故事作為實驗材料(其中包括一些語塊和非語塊),考慮了多重因素,如語塊和非語塊成分詞基本保持一致(個別單詞由于語法、語義等方面的原因做了適當的替換,替換時必須考慮兩個詞的詞頻、長度、音節數等),這樣就可以保證差異的來源是否是語塊造成的。實驗采用自定步調速的閱讀范式,為了不破壞語塊語境的完整性,句子通過逐行呈現給被試。研究表明,即使由相同的成分詞組成,語塊的閱讀時間也比非語塊要快,即語塊的提取速度快于非語塊,這充分說明了語塊的整體加工優勢,語塊是一個單獨記憶的單位。
(四)語塊的整體視覺加工研究
總體而言,大部分研究都證實了語塊加工的整體性。在視覺(閱讀)加工方面,國內學者也同樣做了很多積極有益的嘗試,并取得了豐碩成果。鐘志英和何安平(2012)采用在線語法判斷任務,考察了中國非英語專業學習者對高頻非習語英語程式語的心理表征,并將語言水平(中國英語學習者、在美國的英語學習者和英語本族語者)和性別(男和女)納入學習者變量進行考慮。研究表明,整體表征現象存在于這三種不同語言水平的人群。語言水平越高,加工時間越短,整體表征的程度越高。在中國的英語學習者中,性別的差異未能導致心理表征上的差異,即性別未能作為一個影響整體表征的學習者因素。桑紫林和張少林(2013)也采用了在線語法判斷的任務,考察了中國的英語學習者(高水平組和低水平組)對語塊短語和非語塊短語的加工差異。結果表明,在對語塊進行處理時存在一定的優勢,即提取速度快、錯誤率低。且這種優勢在高水平組上更能得到體現,說明語言水平會影響語塊的整體表征,這與鐘志英和何安平(2012)的結論一致。周榕和李麗娟(2013)探討了影響二語語塊加工優勢的因素。他們發現,語言水平、語義透明度、熟悉度都會調節被試的整體加工效應。語言水平越高、語義透明度越高、熟悉度越高,語塊的提取加工就越快。不同于之前的研究,王啟(2015)聚焦于中低水平二語學習者對高頻普通搭配的心理表征,發現中低水平的學習者對這些語塊都有加工優勢,但就被試而言,語言水平(中下水平和初級水平)對加工優勢并無影響。此外,該研究反駁了Wray(2002)的觀點:非高水平學習者不能習得二語搭配知識(王啟,2015)。許瑩瑩和王同順(2015a,2015b)通過類似的研究方法,引入了語塊結構類型(短語類語塊:on the other side;非短語類語塊:one of the most),也得出了一致的結論:語塊頻率、漢英一致性、結構類型、語言水平(高中低)都會影響學習者對語塊的表征和加工。具體表現在,不論語塊的漢英一致性和結構類型,不同語言水平的學習者對語塊加工都具有頻率效應。總體而言,高水平的學習者比低水平學習者更有加工優勢。endprint
四、結語
綜上所述,國內外的研究者主要從聽覺(聽力)和視覺(閱讀)任務考察了語塊的語音、語義、內部結構和整體表征,得出了較為一致的結論,即語塊具有心理現實性,也就是說在語塊以整體為單位進行存儲和提取。縱觀國內外研究,國內的研究涌現了一系列問題。首先,國內的研究大部分方法、手段單一,基本上以在線判斷任務為主。在線判斷等行為實驗(behavior experiment)是被試經過一系列思維認知活動綜合的結果,從中我們無法知曉加工的實時進展,因而無法揭示二語語塊的本質。國外有部分研究采用眼動儀,該技術可以實時抓捕眼睛的運動軌跡,從中可以窺探被試認知的全過程,有助于厘清語塊心理表征的本質。隨著認知神經科學的發展日益完善,事件相關電位(event-related potentials,ERPs)和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fMRI)等手段技術的運用可以進一步完善語塊的心理加工機制,如可以進一步明確哪些腦區參與了語塊提取的過程。其次,國內研究的層面比較單薄,多數停留在語塊的整體識別。眾所周知,語言是由音、形、義等組成的一個層級系統,語塊作為一種常見的語言現象,也有其本身的語音、語義等方面的屬性。未來的研究可以深入到語音、語義等方面,從這些方面證實語塊的心理現實性,有助于我們全方位地了解語塊的表征和加工機制。
附注:語塊種類繁多,如習語、程式語,但本質上都具有心理現實性,因此本文不對其做具體的劃分。
參考文獻:
[1]丁言仁,戚焱.詞塊運用與英語口語和寫作水平的相關性研究[J].解放軍外國語學院學報,2005,(3):49-53.
[2]繆海燕,孫藍.非詞匯化高頻動詞搭配的組塊效應——一項基于語料庫的研究[J].解放軍外國語學院學報,2005,(3):40-44.
[3]李太志.詞塊在外貿英語寫作教學中的優勢及產出性訓練法[J].外語界,2006,(1):34-39.
[4]王立非,張巖.基于語料庫的大學生英語議論文中的語塊使用模式研究[J].外語電化教學,2006,(4):36-41.
[5]衛乃興.中國學生英語口語的短語學特征研究——COLSEC語料庫的詞塊證據分析[J].現代外語,2007,(3):280-291.
[6]廉潔.詞匯短語對第二語言習得的作用[J].外語界,2001,(4):29-34.
[7]姚寶梁.預制語塊與中學英語口語教學[J].課程·教材·教法,2004,(4):33-38.
[8]原萍,郭粉絨.語塊與二語口語流利性的相關性研究[J].外語界,2010,(1):54-62.
[9]陳偉平.增強學生詞塊意識提高學生寫作能力[J].外語界,2008,(3):48-53.
[10]陳東嵐.語言意識驅動下的語塊教學法在大學英語寫作教學中的運用[J].外語學刊,2015,(2):112-115.
[11]Tremblay A,Derwing B,Libben G,et al.Processing Advantages of Lexical Bundles:Evidence From Self-Paced Reading and Sentence Recall Tasks[J].Language Learning, 2011,(2):569–613.
[12]Chomsky N.Syntactic structures.[J].Mouton the Hague,1957,(3):174–196.
[13]Van Lancker Sidtis,D.Two-track mind:Formulaic and novel language support a dual-process model.In M.Faust (Ed.),The Handbook of the Neuropsychology of Language(pp.342–367).Oxford:Blackwell,2012.
[14]詹宏偉.L2語塊的心理現實性研究——來自語音加工的證據[J].外語與外語教學,2012,(6).
[15]鐘志英,何安平.中國英語學習者對高頻非習語英語程式語的心理表征研究[J].外語教學與研究(外國語文雙月刊),2012,(6):886-898.
[16]易維,鹿士義.語塊的心理現實性[J].心理科學進展,2013,21,(12):2110-2117.
[17]桑紫林,張少林.中國英語學習者語塊認知加工優勢研究[J].外語教學理論與實踐,2013,(2):36-41.
[18]王啟.中低水平二語學習者高頻普通二語搭配的心理現實性[J].現代外語,2015,(2).
[19]許瑩瑩,王同順.語塊頻率、結構類型及英語水平對中國英語學習者語塊加工的影響[J].外語教學與研究,2015,(3):393-404.
[20]許瑩瑩,王同順.頻率、一致性及水平對二語語塊加工的影響[J].現代外語,2015,(3):376-385.
[21]黃四宏,詹宏偉.語塊認知加工研究的最新進展[J].外國語:上海外國語大學學報,2011,(2):64-71.
[22]David Wood.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into the facilitating role of automatized lexical phrases in second language fluency development[J].Language Learning Journal,2004,(1):27-50.endprint
[23]Wood D.Uses and Functions of Formulaic Sequences in
Second-Language Speech:An Exploration of the Foundations of Fluency[J].Canadian Modern Language Review/La Revue Canadienne Des Langues Vivantes,2006,(1):13-33.
[24]van Lancker Sidtis,D.When Novel Sentences Spoken or Heard for the First Time in the History of the Universe Are Not Enough:Toward a Dual-Process Model of Language.[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anguage & Communication Disorders,2004,(1):1-44.
[25]Schmitt,Norbert.Formulaic sequences:acquisition, processing and use[M].John Benjamins Pub.,2004.
[26]Kormos J.Speech production and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ilingual Education & Bilingualism,2006,(2):246-248.
[27]鐘志英.中國學生英語高頻程式語的視覺和聽覺加工優勢研究[J].現代外語, 2015,(3):396-406.
[28]Wray A.Formulaic Language and the Lexicon.[J].Adolescents,2002,(3):332.
[29]Gibbs R W,Bogdanovich J M,Sykes J R,et al.Metaphor in Idiom Comprehension[J].Journal of Memory & Language,1997,(2):141-154.
[30]Conklin K,Schmitt N.Formulaic Sequences:Are They Processed More Quickly than Nonformulaic Language by Native and Nonnative Speakers?[J].Applied Linguistics,2008,(1):82-89.
[31]Siyanova-Chanturia A,Conklin K,Schmitt N.Adding more fuel to the fire:An eye-tracking study of idiom processing by native and non-native speakers[J].Second Language Research,2011,(2):72-89.
[32]張輝.漢語熟語語義加工的認知與神經機制研究[C]//全國認知語言學研討會,2006.
[33]Underwood,G.,Schmitt,N.,& Galpin,A.The eyes have it:An eye-movement study into the processing of formulaic sequences.In N.Schmitt(Ed.),Formulaic sequences:Acquisition,processing and use.Amsterdam,Philadelphia: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2004.
[34]周榕,李麗娟.語塊在二語認知加工中的優勢及其影響因素研究[J].華南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1):42-49.
(孫寒忠 廣東廣州 華南師范大學外國語言文化學院 510631)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