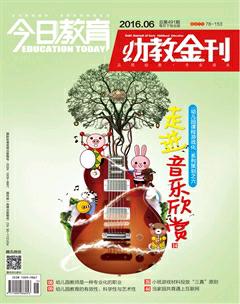老師,為什么剝奪我的權利?
潘曉冬
最近,我有幸參加一個優課展示活動,三節不同科目的優課,不同的老師,相同的展示臺,相同的孩子。12個孩子,這所幼兒園的大班就只有12個孩子嗎?為什么這三位優課展示的老師如此偏愛這12個孩子呢?因為今天她們把這些能說會道的孩子當成了自己表演的工具。在這些孩子的配合下,老師們將自己精心設計的活動展現得淋淋盡致,師幼互動相當融洽,不時引發臺下聽課者的歡呼與喝彩。
那么,那些被滯留在教室內的孩子呢?他們在干嘛?帶著疑問,我暫時離開“展示廳”,找到了這個班的另一半孩子。他們坐在教室里,自己捏著橡皮泥,見到我的到訪,沒有任何表示,看了看我,繼續搓著手頭的橡皮泥,沒有任何交流,顯得很“投入”、很“乖巧”,老師也很挺省事地坐在一邊寫著自己的教案。似乎他們已經習慣了,看著老師把聰明、能干、能說會道的同伴領走,只有他們才有權利去參加高大上的活動,而自己就只能在這兒坐等他們回來講故事。這樣的場景讓人看了很心酸,當參加上課的孩子像快樂的小鳥飛奔回教室,興奮地講述剛才發生的趣事時,滯留在教室的孩子們睜著大大的眼睛認真地聽著,不時也陪同著一起歡笑,卻不知他們內心的真實感受是什么?羨慕?嫉妒?或許他們沒有能力去責問老師:“為什么剝奪我的權利?”又或許他們只能在心里默默地想:“我不行!”“老師不喜歡我!”久而久之,等級之分在孩子們心中逐步形成,后果不想而知。
相信在大力倡導課程游戲化的今天,尊重幼兒、人人平等是課程游戲化的最根本的出發點。評課的老師、聽課的老師似乎都被一塊神奇的布遮住了自己的視線,完全沉浸在臺上精彩的表演,對于背后的那一半孩子卻無動于衷。并且對老師的教案設計、課堂表現力、活動組織、幼兒互動等都給予了高度的肯定,殊不知這背后剝奪了諸多默默無聲的孩子的參與權利,相比之下,這樣的成果有意義嗎?如果你覺得舞臺有限,那你至少可以把這個班的所有孩子都帶進來看一眼,哪怕就以抽簽的方式決定誰留下來,出局的孩子帶著棒棒糖去玩游戲,他們的內心也會得到最起碼的尊重。當然對于離開的孩子,老師你也不要吝嗇自己寶貴的時間,得給他們補上一課,讓他們知道這才叫公平。蘇聯著名教育家、心理學家贊可夫說:“請您不要忘記,孩子們受到不公平的待遇,特別是這種待遇來自一個親近的人的時候,他的痛苦心情會在心靈里留下一個長久的痕跡。”
面對班上的“領袖人物”,老師們看在眼里,喜在心頭,尤其是在展現自己的教學功底的時候,這些“領袖人物”更能助老師“一臂之力”,于是他們自然成為老師們的寵兒。老師們,角落里的那些孩子雖然不愛講話,但是他們也有自己的內心世界,他們更渴望著你能用扎實的教學功底開啟他們智慧的大門。評課者們,你們在為優秀老師點贊時,也要多一項評價指標:班上的另一半孩子在忙什么?他們在同樣的活動中目標達成情況如何?聽課者們,你們不要完全陶醉于臺上精彩的表演,以傾聽者的身份進入這個班級,聽聽孩子們之間的交流,解讀他們的一舉一動、一顰一笑,走進他們的內心世界,換位思考:假如你是孩子,你希望老師怎么待你?
優秀的課堂,尊重是起碼的要素,教師應該發自內心地尊重孩子,公平地對待孩子,尤其是那些“跟不上隊伍”的孩子。誰最需要你?往往就是那些“差一點”的孩子才最需要你。要幫助那些“不愛講”“講不對”的孩子講對了,要明白那種“一時有效”的價值遠遠遜色于“一世有效”的價值。今天,寫下此文,就是想替那些“跟不上隊伍”“差一點”“不愛講”“講不對”的孩子們問一聲:“老師,為什么剝奪我的權利?”
(作者單位:江蘇省海安縣曲塘鎮雙樓幼兒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