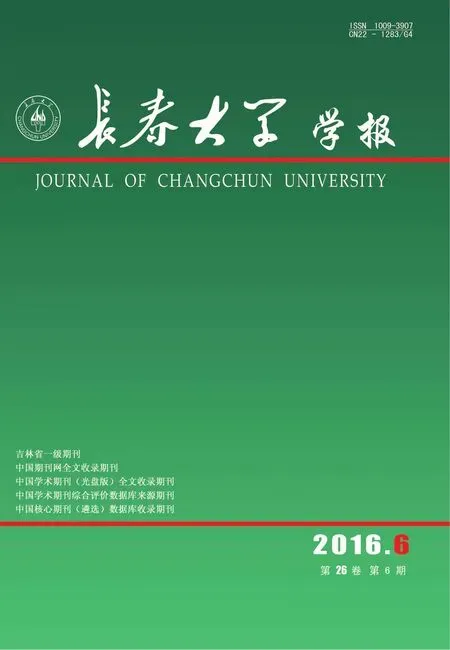以致使范疇為例談?dòng)h對(duì)比的研究方法
王 蕾, 李 濤
(1.上海海事大學(xué) 外國(guó)語學(xué)院,上海 201306;2.朝陽師范高等專科學(xué)校 外語系,遼寧 朝陽, 122000)
?
以致使范疇為例談?dòng)h對(duì)比的研究方法
王蕾1, 李濤2
(1.上海海事大學(xué) 外國(guó)語學(xué)院,上海 201306;2.朝陽師范高等專科學(xué)校 外語系,遼寧 朝陽, 122000)
摘要:英漢對(duì)比無論對(duì)語言本體研究還是應(yīng)用研究都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語言對(duì)比的研究方法越來越引起人們的重視。本文以關(guān)于致使范疇的英漢對(duì)比研究為例,分別從對(duì)比基礎(chǔ)、對(duì)比對(duì)象、對(duì)比程序、對(duì)比理論框架四個(gè)層面結(jié)合具體研究案例闡述了目前英漢對(duì)比研究在研究方法上存在的一些不足。最后,文章提出了一條新的英漢對(duì)比研究路徑,從語言事實(shí)出發(fā),通過實(shí)證研究得出結(jié)果。同時(shí),該路徑也十分強(qiáng)調(diào)理論的應(yīng)用與建設(shè)。
關(guān)鍵詞:英漢對(duì)比;方法論;致使范疇
近些年來,一些學(xué)者重新審視了語言對(duì)比的研究方法,指出了目前研究的一些弊病。許余龍[1]曾介紹Chesterman[2]對(duì)TC(對(duì)比基礎(chǔ))及其分類的質(zhì)疑。衛(wèi)乃興[3]242也對(duì)對(duì)比出發(fā)點(diǎn)的問題提出了類似的質(zhì)疑。沈家煊[4]提出,“有些英漢對(duì)比得出的結(jié)論缺乏說服力,主要原因有兩個(gè):一是不重視語言內(nèi)部的證據(jù),三是不重視證據(jù)的系統(tǒng)性。”
這些意見反映出目前英漢對(duì)比研究無論在理論建設(shè)還是操作方法上仍存在一些不足。這些不足不但不利于具體研究得出可靠的結(jié)論,長(zhǎng)此以往,更會(huì)使整個(gè)對(duì)比研究陷入停滯不前的局面。本文主要收集了近年來發(fā)表的涉及致使范疇的英漢對(duì)比研究,其中包括專著、博士論文、碩士論文、期刊論文、會(huì)議論文等,旨在通過對(duì)這些研究的梳理、討論,發(fā)現(xiàn)對(duì)比研究在對(duì)比基礎(chǔ)、對(duì)比對(duì)象、對(duì)比程序、對(duì)比理論框架等方面容易出現(xiàn)的問題,并試圖提出一條更有效的研究路徑。
1對(duì)比基礎(chǔ)
Chesterman、[2]衛(wèi)乃興[3]242等認(rèn)為“對(duì)比基礎(chǔ)”的概念易導(dǎo)致循環(huán)論證。以下轉(zhuǎn)引衛(wèi)乃興(同上)的有關(guān)論述:“過去的對(duì)比研究多以一些抽象的概念為出發(fā)點(diǎn),如語言系統(tǒng)、對(duì)比基礎(chǔ)(tertium comparationis)、語言對(duì)應(yīng)(linguistic correspondence)、對(duì)等(equivalence)等等。在現(xiàn)今的語境下,較多研究者趨于將這些概念視為研究活動(dòng)的終端追求,而不是出發(fā)點(diǎn),因?yàn)樗鼈儽举|(zhì)上是一些理論構(gòu)想而非可觀察的實(shí)體。比如對(duì)比基礎(chǔ),意即兩種被比語言中存在的有關(guān)范疇間的共同點(diǎn)或共同基礎(chǔ)。就詞語對(duì)比而言,對(duì)比基礎(chǔ)即兩個(gè)被比詞項(xiàng)應(yīng)表達(dá)的相同意義和功能。唯有此,被比者才具有可比性。然而,這個(gè)所謂的對(duì)比基礎(chǔ)從何而來?我們?nèi)绾未_定兩種語言的兩個(gè)詞語間存在對(duì)比基礎(chǔ)?從抽象的語言系統(tǒng)出發(fā)?從假定的普遍概念或普遍特征出發(fā)?這些一直都是語言學(xué)理論長(zhǎng)期爭(zhēng)而未果的問題,而由這些抽象概念驅(qū)動(dòng)研究并不可行,且易導(dǎo)致循環(huán)論證。
本文所調(diào)查的研究大部分都是以“致使”這一抽象范疇,或者說以“致使義”為對(duì)比基礎(chǔ)來展開研究的。調(diào)查發(fā)現(xiàn),強(qiáng)調(diào)對(duì)比基礎(chǔ)確實(shí)容易陷入循環(huán)論證。如,“致使義視角下的‘把’字句及其英語表達(dá)形式”一文[5],其對(duì)比基礎(chǔ)為致使義,文章利用Talmy[6]的致使義理論分析“把”字句及與其有翻譯關(guān)系的英文句子,最終確定“把”字句在英語中的表達(dá)形式。從有翻譯關(guān)系的英漢文本中抽取“把”字句的英語對(duì)應(yīng)項(xiàng)同“把”字句進(jìn)行對(duì)比研究,其對(duì)比基礎(chǔ)即為二者所表達(dá)的語義。然而,整個(gè)研究從共同語義出發(fā),經(jīng)過分析又驗(yàn)證了英漢一些語言形式具有共同的語義。這樣的研究也許對(duì)翻譯實(shí)踐有一定的指導(dǎo)作用,但對(duì)于語言研究來說,不利于發(fā)現(xiàn)兩種語言在致使表達(dá)上的差異及其內(nèi)在原因。
如果對(duì)比的起點(diǎn)不宜以抽象的語法、語義、語用范疇為基礎(chǔ),那么對(duì)比研究應(yīng)該從何做起呢?Chesterman[2]認(rèn)為“對(duì)比功能分析的出發(fā)點(diǎn)是語言學(xué)家、譯者和二語學(xué)習(xí)者覺察到的兩種語言之間在實(shí)際使用中的某種相似性。從這種語言實(shí)際使用中的相似性,我們可以進(jìn)一步推斷兩種語言在抽象語言系統(tǒng)中存在的某種相似性。這種覺察到的相似性可能是模糊的,或者僅僅只是一種臆測(cè)。但正是這種覺察到的相似性,為對(duì)比研究提供了最初的可比性標(biāo)準(zhǔn)。”(轉(zhuǎn)引自許余龍)[7]由于這種相似性是通過觀察語言現(xiàn)象推測(cè)出來的,這實(shí)際就把研究的起點(diǎn)從一個(gè)抽象的概念推到了具體的語言現(xiàn)象。衛(wèi)乃興[3](P242)曾提到,可以“從平行語料庫(kù)或可比語料庫(kù)的證據(jù)出發(fā),探討被比對(duì)象相關(guān)層面上的異同”。
用可以觀察到的具體語言現(xiàn)象作為對(duì)比的起點(diǎn),而不是以抽象的范疇作為對(duì)比基礎(chǔ),不僅在操作層面上易于執(zhí)行,有利于確定對(duì)比對(duì)象,而且有助于發(fā)現(xiàn)更多的語言事實(shí)從而獲得系統(tǒng)的全貌,并由此展開全面深入的對(duì)比研究。還以上文討論的研究[5]為例,如果不以致使義為研究的基礎(chǔ),而是從觀察“把”字句及與其有翻譯關(guān)系的英文句子入手,可以發(fā)現(xiàn)大部分“把”字句和英語的SVOA/SVOC句式相對(duì)應(yīng),以此可推斷“把”字句同英語的SVOA/SVOC句式在表達(dá)功能上具有相似性。這種相似性為對(duì)比“把”字句和英語SVOA/SVOC句式提供了理據(jù)性,但這種相似性具體落在什么地方,不必匆忙下結(jié)論,可以通過從多個(gè)維度進(jìn)一步挖掘、觀察語料一層層推進(jìn),這樣得到的結(jié)論也許更有意義。
2對(duì)比對(duì)象
沈家煊[4]曾指出,對(duì)比研究不重視語言內(nèi)部的證據(jù)。這與不重視對(duì)比對(duì)象的選擇不無關(guān)系。下面,我們以“英漢致使結(jié)構(gòu)的最簡(jiǎn)句法研究”[8]為例,說明選擇對(duì)比對(duì)象時(shí)容易出現(xiàn)的問題。

圖1 雙向性理論語言對(duì)比模式(轉(zhuǎn)引自許余龍)[9] (P12)
該論文的對(duì)比的基礎(chǔ)仍是抽象概念致使義,研究范圍是英漢致使結(jié)構(gòu)。按照以往的研究模式(見圖1),應(yīng)該從致使義(X)出發(fā),找出英、漢(A、B)兩種語言中能夠表達(dá)此語義范疇的各種結(jié)構(gòu)形式(Xa、Xb),再分別進(jìn)行對(duì)比研究。然而,Xa、Xb分別是兩個(gè)復(fù)雜的系統(tǒng),如果對(duì)Xa、Xb的認(rèn)識(shí)不夠充分,則會(huì)導(dǎo)致對(duì)比研究的結(jié)果有失偏駁;如果刻意地選取系統(tǒng)中的某些形式而無視其他形式來進(jìn)行對(duì)比,則很可能得出不實(shí)的結(jié)論。
本節(jié)所討論的研究采用了Comrie[10][11]對(duì)致使表達(dá)形式的分類體系,并以此為基礎(chǔ)在英漢兩種語言中確定了幾種形式作為對(duì)比對(duì)象。Comrie[10][11]提出的致使表達(dá)形式包括:詞匯型(lexical type)、形態(tài)型(morphological type)、分析型(analytic type)(又稱為句法型或迂回型)三種。按照這三個(gè)類型的定義,分別找到的現(xiàn)代漢語致使結(jié)構(gòu)包括:
2.1詞匯型:由不及物動(dòng)詞或形容詞轉(zhuǎn)變而來的致使動(dòng)詞,如:
(1)一只蛐蛐發(fā)了兩戶人家。
羅維民的發(fā)現(xiàn)激動(dòng)了兩個(gè)人。
其中,“發(fā)”是由不及物動(dòng)詞轉(zhuǎn)變來的,“激動(dòng)”是由形容詞轉(zhuǎn)變來的。
2.2形態(tài)型:通過添加詞綴而獲得致使義的動(dòng)詞,漢語當(dāng)中,典型的此類詞綴包括“-化”,如:
“美化、綠化、城市化、現(xiàn)代化、工業(yè)化”等。需要指出的是,其實(shí)只有當(dāng)“化”加在形容詞后面才構(gòu)成致使動(dòng)詞,如:
(2)美化城市
加在名詞前面仍不能用作致使動(dòng)詞,如:
(3)使國(guó)家現(xiàn)代化
*現(xiàn)代化國(guó)家
另外,作者還提到了一類非典型的詞綴,如“弄-”“搞-”“打-”“開-”等動(dòng)詞,加在其他動(dòng)詞或形容詞前可使新的結(jié)構(gòu)帶有致使義,如“弄臟”、“搞砸”、“打破”、“開開”等。在這些致使結(jié)構(gòu)中,“弄-”“搞-”“打-”“開-”等動(dòng)詞的具體意義較模糊,這大概是作者視其為詞綴的理由。這里我們姑且不論如此處理是否合適。
最后,現(xiàn)代漢語還存在少量的通過語音變化而形成的致使動(dòng)詞,如“飲(yǐn)”為及物動(dòng)詞,而“飲(yìn)”則是致使動(dòng)詞。
2.3分析型:主要指帶有“使”、“叫”、“讓”、“得”等致使標(biāo)記的兼語式,如:
(4)姐姐讓我打掃衛(wèi)生。
你逼得我沒有一點(diǎn)路可走了。
略去文章對(duì)英語致使結(jié)構(gòu)的分類描述不說,下面單看漢語的情況。Comrie[10][11]對(duì)致使結(jié)構(gòu)的分類框架是從語言類型學(xué)的視角提出的,面向所有的語言。他指出所有語言的各類致使結(jié)構(gòu)形成了一個(gè)連續(xù)系統(tǒng),其中詞匯型、形態(tài)型、分析型結(jié)構(gòu)各有其典型的和非典型的形式,在這三種結(jié)構(gòu)類型中間也有其他的形式存在。這就是說,可能存在這樣的情況:某一語言中的致使結(jié)構(gòu)不一定全部表現(xiàn)為詞匯型、形態(tài)型和分析型,可能是其中的一種或兩種,甚至可能表現(xiàn)為三者之外的其他形式。所以,在對(duì)漢語的致使結(jié)構(gòu)做分類描述時(shí),大可不必拘泥于詞匯型、形態(tài)型和分析型三類,而應(yīng)該立足于漢語的事實(shí),重視而不是忽視其他類型的存在。就漢語而言,動(dòng)結(jié)式是一種非常重要的致使結(jié)構(gòu),使用相當(dāng)廣泛。本節(jié)討論的案例研究把一部分動(dòng)結(jié)式,如“弄臟”、“搞砸”、“打破”、“開開”等看作是非典型的形態(tài)型致使結(jié)構(gòu),[8]36而把其他動(dòng)結(jié)式,如“敲碎”,看作是連續(xù)統(tǒng)中間的其他結(jié)構(gòu)類型。[8]55但由于動(dòng)結(jié)式不是類型學(xué)框架中列出的典型致使結(jié)構(gòu),因而未受到重視,在具體的對(duì)比分析中也略去不談。如此“選擇”對(duì)比對(duì)象,對(duì)漢語中常見的一類致使結(jié)構(gòu)不予詳細(xì)討論,從而得出英漢兩種語言“大同小異”的結(jié)論,就不足為怪了。可見,對(duì)比對(duì)象選擇的重要性。
3對(duì)比程序
一般的研究在選定了對(duì)比對(duì)象之后,即在一些層面,如語法結(jié)構(gòu)、語義特征等開展對(duì)比分析,往往依據(jù)一些例證得出結(jié)論。如此程序,往往由于無法保證語料的代表性,而使得結(jié)論不能使人信服。下面以“漢語和英語的致使句”[12]一文為例說明此程序的弊端。該文從語義類型、形態(tài)標(biāo)志、語法表現(xiàn)形式等方面對(duì)漢語和英語的致使句進(jìn)行了對(duì)比研究。這里,我們僅討論其在語義層面的對(duì)比分析。在語義層面,作者區(qū)分了兩類語義特征。一類根據(jù)致使主體對(duì)致使客體施加外力導(dǎo)致的結(jié)果是否實(shí)現(xiàn),分為“實(shí)現(xiàn)”和“未實(shí)現(xiàn)”兩種;另一類根據(jù)致使主體對(duì)致使客體施加外力的方向,分為“正方向”和“反方向”兩種。其中,“正方向”是指致使主體對(duì)致使客體施加外力,“反方向”是指致使客體接受致使主體的施力。“反方向”致使的英語例子包括:
(5)He gave in to Harry(‘s pressure on him).
He resisted Harry(‘s pressure on him).
He withstood Harry(‘s pressure on him).
作者認(rèn)為“正方向”的致使句在漢語和英語中都有較多出現(xiàn),而“反方向”的致使句只在英語中存在。實(shí)際上,由于缺少對(duì)大量語料的觀察,以上的結(jié)論并不準(zhǔn)確。我們通過查閱《漢語動(dòng)詞用法詞典》[13],發(fā)現(xiàn)至少以下例子表達(dá)的是“反方向”致使:
(6)人們拿起武器共同抵抗起來(抵抗起敵人的進(jìn)攻來)
廣大農(nóng)民反抗起地主階級(jí)壓迫來
經(jīng)受巨大壓力
為了和(5)對(duì)應(yīng),以上例子可改寫為:
(6’)人們拿起武器共同抵抗起敵人(對(duì)他們的進(jìn)攻)來。
廣大農(nóng)民反抗起地主階級(jí)(對(duì)他們的壓迫)來。
甲板經(jīng)受住了成千上萬只的集裝箱(對(duì)其的巨大壓力)。
由此可以看到,脫離對(duì)大量語料的觀察,僅憑語感或片面的語料主觀臆斷的研究方法是相當(dāng)靠不住的。那么采用什么樣的程序可避免得出這樣的結(jié)論來呢?呂叔湘[14]3曾說過,“不管做哪種學(xué)問,總不外乎‘?dāng)[事實(shí)、講道理’六個(gè)字”。“進(jìn)行語言研究,語言事實(shí)是第一位的。”[15] (P31)沈家煊[16] (P63)也曾強(qiáng)調(diào),“擺事實(shí)是講道理的基礎(chǔ),要十分重視擺事實(shí)。”下面介紹一種從語言事實(shí)出發(fā)的研究程序[2]:
1.觀察基本語料;
2.提出可比標(biāo)準(zhǔn)(語言 A 中的某一語言現(xiàn)象X和語言B中的某一語言現(xiàn)象Y具有相似性);
3.提出問題:這種相似性的本質(zhì)是什么?
4.初始假設(shè):X與Y是等同的;
5.驗(yàn)證假設(shè):為什么初始假設(shè)可以得到支持或推翻? 在什么條件下(如果有的話)可以維持初始假設(shè)?
6.修正假設(shè):(在等同假設(shè)不成立的情況下):X 與 Y 的關(guān)系是這樣的(具體表述);或X和Y的使用取決于這樣的條件(具體表述);
7.驗(yàn)證修正的假設(shè)。
(轉(zhuǎn)引自許余龍)[7]
可以看到,與一般程序不同,Chesterman[2]提出的研究步驟強(qiáng)調(diào)了實(shí)證研究的作用,也正是實(shí)證研究保證了研究結(jié)果的信度。在我們調(diào)查的研究中,郭印[16]的研究嚴(yán)格遵循了此路徑。
4對(duì)比理論框架
許余龍[18]認(rèn)為,“較為系統(tǒng)的語言對(duì)比研究,無論是理論對(duì)比研究,還是應(yīng)用對(duì)比研究,通常都需要選用某一理論或分析框架對(duì)兩種語言進(jìn)行統(tǒng)一的平行分析描述,以確保分析結(jié)果的可比性和結(jié)論所應(yīng)達(dá)到的某種程度的周延性。”
在我們所調(diào)查的研究中,雖然大部分研究都有理論框架的支撐,但是在進(jìn)行具體的對(duì)比分析時(shí),所采取的觀察維度仍較為任意,觀察維度之間缺少理論聯(lián)系。
沈家煊[4]指出有些英漢對(duì)比得出的結(jié)論缺乏說服力,主要原因有兩個(gè),其中一個(gè)就是“不重視證據(jù)的系統(tǒng)性”。怎樣才能系統(tǒng)地發(fā)掘證據(jù),這離不開理論的探照燈。
另一方面,國(guó)內(nèi)的研究往往不重視理論的建設(shè)。習(xí)慣為西方的語言學(xué)理論做嫁衣,而不重視,甚至不正視漢語的特點(diǎn)。英漢對(duì)比研究最能夠發(fā)現(xiàn)漢語的特點(diǎn),也最應(yīng)該為理論建設(shè)做出貢獻(xiàn)。如第三節(jié)中提到的對(duì)英漢致使結(jié)構(gòu)的分類描述,假如能夠重視動(dòng)結(jié)式在漢語致使表達(dá)系統(tǒng)中所占據(jù)的位置,認(rèn)真分析動(dòng)結(jié)式的結(jié)構(gòu)特點(diǎn),弄清楚動(dòng)結(jié)式與詞匯型、形態(tài)型、分析型致使結(jié)構(gòu)的區(qū)別與聯(lián)系,就可以嘗試提出一套更為細(xì)致的形式-語義特征用以分析描述各類致使結(jié)構(gòu),從而推進(jìn)語言類型學(xué)的研究。
5一種新的研究路徑
通過以上的討論,我們提出如下的對(duì)比研究路徑:
(1)確定可比對(duì)象:通過觀察語料,尤其可以利用平行語料庫(kù)或可比語料庫(kù),捕捉到兩種語言間的某種相似之處,并將相似之處提煉為兩種語言系統(tǒng)中的語言現(xiàn)象或用法Xa和Xb,從而確定可比對(duì)象;
(2)提出初始假設(shè):Xa和Xb是等同的;
(3)確立理論框架,用以描述語言現(xiàn)象,并設(shè)計(jì)實(shí)證研究檢驗(yàn)初始假設(shè);
(4)分析檢驗(yàn)結(jié)果:初始假設(shè)成立/不成立,如若不成立,則要修正假設(shè),并進(jìn)一步驗(yàn)證修正假設(shè);
(5)結(jié)合對(duì)比結(jié)果,反觀理論框架,進(jìn)行理論探究。
這條研究路徑從語言事實(shí)出發(fā),假定兩個(gè)具體的跨語言現(xiàn)象有相同的語義、語用功能或語法特征,然后再進(jìn)行細(xì)致地觀察與分析,驗(yàn)證或修正假設(shè)。而目前很多的對(duì)比研究,從某一抽象范疇出發(fā),不僅容易使整個(gè)研究陷入循環(huán)論證,而且在選擇對(duì)比對(duì)象時(shí)容易出現(xiàn)“以偏概全”、或“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現(xiàn)象。另外,本文提出的研究路徑強(qiáng)調(diào)對(duì)理論的應(yīng)用和建設(shè)。沒有理論的引領(lǐng),就很難系統(tǒng)地觀察語料,也就很難得到有價(jià)值的語言事實(shí)。但是應(yīng)用理論,仍要以語言事實(shí)為本,避免“削足適履”,而要“量體裁衣”,不斷修正完善現(xiàn)有的理論。
6結(jié)語
我們結(jié)合與致使范疇相關(guān)的一系列英漢對(duì)比研究,探討了語言對(duì)比研究中對(duì)比基礎(chǔ)、對(duì)比對(duì)象、對(duì)比程序、對(duì)比理論框架等問題,并試圖提出一條新的研究路徑。此路徑是否可行,是否能有效避免現(xiàn)有對(duì)比研究的一些弊端還有待實(shí)踐的檢驗(yàn)。
參考文獻(xiàn):
[1]許余龍. 再論語言對(duì)比基礎(chǔ)的類型[J]. 外國(guó)語, 2007 (6): 21-27.
[2]Chesterman, A.ContrastiveFunctionalAnalysis[M].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1998.
[3]衛(wèi)乃興. 詞語學(xué)要義[M]. 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 2011.
[4]沈家煊. 怎樣對(duì)比才有說服力:以英漢名動(dòng)對(duì)比為例[J]. 現(xiàn)代外語, 2012(1): 1-13.
[5]王蕾. 致使義視角下的“把”字句及其英語表達(dá)形式[J]. 外語教學(xué)與研究, 2008(1): 37-44.
[6]Talmy, L. Semantic causative types. [A]. In M. Shibatani. (ed.).SyntaxandSemantics:TheGrammarofCausativeConstructions[C].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43-116, 1976.
[7]許余龍. 對(duì)比功能分析的研究方法及其應(yīng)用[J]. 外語與外語教學(xué), 2005(11): 12-15.
[8]安璐. 英漢致使結(jié)構(gòu)的最簡(jiǎn)句法研究[D]. 鄭州大學(xué), 2012.
[9]許余龍. 對(duì)比語言學(xué)[M]. 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 2001.
[10]Comrie, B. Causative verb formation and other verb-deriving morphology [A]. In Shopen T. (ed.).LanguageTypologyandSyntacticDescription.Vol.III. [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309-348, 1985.
[11]Comrie, B.LanguageUniversalsandLinguisticTypology[M]. Oxford: Blackwell, 1981.
[12]周紅. 漢語和英語的致使句[J]. 煙臺(tái)師范學(xué)院學(xué)報(bào)(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版), 2003 (1): 105-110.
[13]孟琮等. 漢語動(dòng)詞用法詞典[K]. 北京:商務(wù)印書館, 1999.
[14]呂叔湘. 把我國(guó)語言科學(xué)推向前進(jìn)[R]. 呂叔湘. 呂叔湘語文論集[C]. 北京:商務(wù)印書館, 1980/1983.
[15]王菊泉. 什么是對(duì)比語言學(xué)[M]. 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 2011.
[16]沈家煊. 談?wù)劇皵[事實(shí)”和“講道理”:語法研究方法示例[R]. 沈家煊. 語法六講[C]. 北京:商務(wù)印書館, 2011.
[17]郭印. 漢英致使交替現(xiàn)象的認(rèn)知功能研究[D].上海:上海外國(guó)語大學(xué), 2011.
[18]許余龍. 語言對(duì)比研究是否需要一個(gè)理論框架[J]. 寧波大學(xué)學(xué)報(bào)(人文科學(xué)版), 2009 (4): 32-38.
責(zé)任編輯:劉琳
A Discussion on Methodology of Contrastive Studies between English and Chinese by a Review of Contrastive Studies on Causation
WANG Lei1, LI Tao2
(1.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Shanghai Maritime University, Shanghai 201306, China;2. Foreign Language Department, Chaoyang Teachers College, Chaoyang 122000, China)
Abstract:Contrastive studies between English and Chinese are of great importance in the study of language as well as in the field of applied linguistics. And how to conduct contrastive studies has been drawing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from the academic circle.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discussion of some specific contrastive studies between English and Chinese concerning causation, elaborates on the shortcomings of the current methodology commonly adopted in contrastive study in terms of its research basis, objects, procedure and theoretical framework. In the end, an alternative approach to the contrastive studies between English and Chinese has been proposed, which begins with a tentative hypothesis about certain linguistic facts and comes to a conclusion based on empirical study. This approach also values the application and modification of linguistic theories.
Keywords:contrastive study between English and Chinese; methodology; causation
收稿日期:2016-5-30
基金項(xiàng)目:上海市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規(guī)劃青年課題(2015EYY005)
作者簡(jiǎn)介:王蕾(1982-),女,河北邯鄲人,講師,博士,主要從事語言學(xué)研究。
中圖分類號(hào):G642
文獻(xiàn)標(biāo)志碼:A
文章編號(hào):1009-3907(2016)06-0098-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