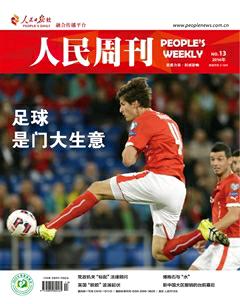槍支文化與美國的暴力噩夢
美國的槍支暴力已經(jīng)產生了浸泡在血泊中的文化,這種文化從偶然死亡、自殺、家庭暴力蔓延到大規(guī)模掃射,從而給所有人都帶來威脅。
單2015年就爆發(fā)了超過270起群眾性槍擊案,再次證明了支持暴力的經(jīng)濟、政治和社會條件根本沒有解決。令人感到悲哀的是,這些槍擊案并非孤立的偶然事件。每隔一天就有一名12歲以下的兒童被槍殺,在過去3年里被槍殺的兒童達555人。更加令人恐懼的統(tǒng)計數(shù)字和令人震驚的道德和政治變態(tài)的例子是,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CDC)提供的數(shù)據(jù)稱:“2014年,美國有2525個兒童和少年被槍殺;每3小時28分死一個孩子,或一天死將近7個孩子,一周死48個孩子。”這些數(shù)字說明美國太多的年輕人處于槍支和暴力泛濫到可以被稱為戰(zhàn)區(qū)的地方。
在美國,如果不思考軍事國家的成熟就無法理解槍支文化和暴力文化的崛起。自從冷戰(zhàn)結束后,美國就已經(jīng)建立起“世界上最廣泛和強大的軍隊”。自“9·11”以來,美國已經(jīng)強化了在海外的軍事力量范圍,同時進一步加劇了美國社會一直進行中的軍事化。
戰(zhàn)爭價值觀不再意味著與瘋狂非理性或危險病態(tài)糾纏在一起的東西,反而成為一種常識。比如,美國政府為了抓住恐怖分子或防止恐怖分子襲擊,寧愿把像波士頓這樣的大城市封鎖起來,卻拒絕通過能顯著減少每年死于槍支暴力的美國人數(shù)量的槍支控制法案。政客們昏了頭,只考慮恐怖主義威脅,寧愿犧牲公民自由也不愿意承認“每年死于槍支暴力的美國人有3萬人”(2012年死于恐怖分子襲擊的人總共是17人)的事實。
美國患上了暴力傳染病,結果是大量兒童被射殺。在宣布減少槍支暴力的一攬子行政行動時,奧巴馬總統(tǒng)專門挑出槍支游說團和國會拒絕作為執(zhí)行哪怕是溫和槍支控制改革的罪魁禍首。
隨著暴力進入美國人生活的中心,它變成社會的組織原則,進一步導致民主肌體的瓦解。在此情況下,美國開始把每個人都當做潛在的罪犯,美國發(fā)起了針對自己國民的戰(zhàn)爭,開始不惜犧牲兒童及其未來。政客出于狹隘自我利益和金融利益的需要拒絕鏟除制造暴力的條件,他們必須為槍支暴力的破壞性文化中的受害者承擔責任。我們對暴力的譴責不應該僅僅局限在警察的殘酷無情上,暴力并不僅僅來自警察。塔竹·科爾在《紐約客》指出,美國還存在源自國家權力的其他危險,如懲罰告密者,情報機構幫助逮捕那些抗議企業(yè)和國家權力濫用的人。
但是,我們聽到的唯一改革是更安全的槍支政策,強制性地要求警察戴著照相機和更多背景核查。這些改革或許意圖良好,但它們沒有抓住問題的根本,那就是利用死亡發(fā)財?shù)纳鐣徒?jīng)濟制度。我們聽不到出賣良心支持槍支游說團尤其是全國步槍協(xié)會的家伙如何為自己辯解。同樣是這群政客支持日常生活的軍事化,鼓吹虐囚,對軍工產業(yè)卑躬屈膝,以此換取軍事、企業(yè)、學術聯(lián)合體獎賞的幾根骨頭。
這些徹底腐敗的政客是身著便服的殺手,其大膽和強硬體現(xiàn)在共和黨總統(tǒng)候選人近期的一場辯論中,反動的右翼脫口秀主持人休米·休伊特向候選人神經(jīng)外科醫(yī)生本·卡森提問,是否愿意以殺掉數(shù)千名兒童展現(xiàn)強硬領導力,似乎殺掉無辜兒童是對領導力的合法考驗。這就是歇斯底里的恐懼政治和戰(zhàn)爭煽動,這是不受約束的恐怖主義焦點造成的必然結果。
顯然,美國的暴力起因不能僅止于問責政客。我們需要做的是發(fā)起政治運動,愿意挑戰(zhàn)和取代這個賦予腐敗無能和煽動戰(zhàn)爭的政客過多政治和經(jīng)濟權力的千瘡百孔的制度。民主和正義依靠生命來維持,其挑戰(zhàn)在于恢復它的生命力,不是改革而是徹底砸碎這個制度。這種革命只有在政治發(fā)展到一定程度之后才能發(fā)生,正義的實現(xiàn)必須依靠集體斗爭的無限責任來配合才行。
(作者:亨利·吉魯)
(人民網(wǎng)輿情檢測室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