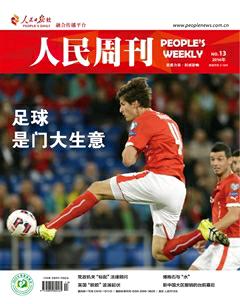五花八門的國民黨稱呼
無論是第一手的電文、日記、書信,還是回憶錄,像師座、旅座、團座等叫法鳳毛麟角,幾乎不見于記載。至于什么“局座”“處座”之類,更像是導演編劇們腦洞大開的產物。
在民國題材影視劇中,國民黨內部的稱呼一直是個頗具時代感的元素,看得多了,觀眾也摸清了門道。領導一律稱某座,如“師座”“處座”,“局座”甚至被頑皮的網友用在了當代某著名軍事專家身上;同輩官員間喜歡稱兄道弟,關鍵時刻可要“拉兄弟一把”;“校長”就是蔣介石的代名詞,有時還叫“總裁”。
這些今天看來帶著幾分喜感的稱謂是怎么來的?最低要達到什么級別才能被稱為“座”?什么人可以叫蔣介石校長?什么層次的關系可以稱兄道弟?這些問題理一下頭緒,會發現影視中很多叫法其實是以訛傳訛。實際上在當時國民革命軍的將領之間,稱呼是非常講究的,不但“校長”不能亂叫,兄長也不能隨便認的,套近乎也要按規矩講輩分。
從黨員“總理”到全民“國父”
說起“國父”,大家都知道指的是孫中山,在電視劇里,會發現很多國民黨員稱之為“總理”。“國父”與“總理”這兩個稱謂都是孫中山逝世之后才有的,“國父”這一稱謂的出現要晚得多,直到1940年4月1日,國民政府才正式尊孫中山為中華民國國父。此后,許多叫法也有微妙變化,例如《總理遺囑》開始被改稱《國父遺囑》,《總理紀念歌》改為《國父紀念歌》,就連原歌詞中“我們總理,首創革命”也改成了“我們國父,首創革命”,其實都只改動了兩個字,其他均未變。“總理”是政黨的職位,而“國父”則上升到了國家層面。看似僅僅是稱呼變化,背后伴隨的是一系列強制性政策,例如學校學生必須背誦《國父遺囑》,政府公職人員必須穿中山服等。兩字之差,“黨員必讀”就變成了“全民必讀”。
從委員長到總裁
孫中山被尊為國父時已去世多年,實行這一系列措施的是蔣介石。和孫中山比起來,蔣介石的專有名詞更多,例如委員長、總裁、校長、蔣公等等,這些稱呼又是怎么來呢?
先說人盡皆知的“委員長”。打完中原大戰,蔣介石平定了黨內幾支實力較大的軍閥,黨、政、軍大權越來越集中于他手中。1926年至1936年這10年間,張靜江、胡漢民、蔣介石在黨內都擔任過執行委員會主席之職,但這個職位的權力非常有限。那時候“主席”這兩個字實在不怎么值錢,不要說黨內的主席,即使是國民政府的主席也只是個名頭。既然主席是虛的,那就必須另設機構集權。
1932年3月1日,國民黨四屆二中全會召開,這次會議正式通過軍事委員會組織大綱,恢復了之前二屆五中全會后被撤銷的軍事委員會,并提名由蔣介石擔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不久后就正式任命。根據四屆二中全會的議案,軍委會委員長一職統率全國海陸空軍,總管軍令、軍政等事項,實際上就是國家最高統帥,婦孺皆知的“蔣委員長”就此誕生。1945年抗戰勝利后,軍事委員會這個機構被撤銷,也就是說,“蔣委員長”這個稱呼只存在于1932年到1945年之間。現在不少電視劇中,明明已是國共內戰時期,國軍將領們還一口一個“委員長”地叫,實在是嚴重穿幫。
除了“委員長”這個特別著名的稱呼之外,蔣介石在國民黨內還有個專有稱謂——總裁。1937年抗戰全面爆發后,為應對復雜的形勢,國民黨于1938年3月29日至4月1日,在武漢召開了臨時全國代表大會,最重要的內容就是修改黨章,增設了《總裁》一章,與原保存的《總理》一章并存,規定:“總裁代行總理職權。”
“領袖制度”確立后,國民黨自孫中山逝世以來實行的委員制名存實亡,蔣介石成了黨內的最高領袖。1975年4月5日,蔣介石在臺北逝世,不久后,蔣經國擔任中國國民黨黨主席。蔣經國告誡國民黨黨員:以后不要稱“蔣經國時代”,也不要稱他為領袖。從此以后,黨主席一職便是國民黨中的最高職位,但這個職務沒有任何領袖色彩,并定期通過選舉換屆,至今如此。
國民黨的主席有很多,包括連戰、馬英九、吳伯雄等人都擔任過,但總理與總裁卻是獨一無二的。言“總理”特指孫中山,言“總裁”則特指蔣介石。但二者又有本質區別,總理一職成專屬是在孫中山逝世后才被賦予,是黨員對先行者功績的彰顯行為。總裁則不同,這個職務以最高領袖的形式出現,可以代行孫中山之后黨內再也沒有人擔任過的總理一職的職權,并且幾十年不換屆,等同于終身制,可以說不是黨魁,勝似黨魁。
除了委座,其他長官很少被叫“座”
如今大眾對國軍部隊中的稱呼還有這么個印象,那就是軍長不叫軍長,而叫軍座;師長不稱師長,稱師座。在老電影《南征北戰》中,國民黨的張軍長麾下的參謀就以“軍座”稱呼長官,此后但凡涉及國民黨時代的影視作品中,什么委座、總座、軍座、師座、團座、局座、處座?層出不窮。當下不少民國將領的粉絲們也很喜歡用“座”來稱呼自己的偶像。在百度百科輸入“軍座”,詞條顯示的解釋是“在國民黨的部隊中,各級人員都有著嚴格的官職稱謂甚至是尊稱”。我不知道這個詞條的依據到底是什么?
先從這個“座”字來看。“座”是敬辭,取寶座之意,可以是下級對上級的尊稱,也可能是對沒有隸屬關系的人的敬辭。但若是將“座”視為國軍的專利,那可就大錯特錯了。從正式軍職來說,在國民革命軍中沒有“某座”這個職務,有的只是和解放軍一樣的軍長、師長、團長等。當然,“座”這種稱呼在民國軍隊中的確存在,例如解放軍的將軍陳銳霆就曾稱呼在萊蕪戰役中被俘的國軍將領李仙洲為“軍座”,這顯然只是一種表示尊敬的稱呼,用或不用完全看個人習慣。其性質與北洋軍閥頭目之間喜歡稱“帥”,民國老百姓叫軍人“老總”一樣。其實翻開民國第一手史料(書信、日記、電報等),見得最多的“座”恰恰不是軍座、師座、團座,而是“委座”與“鈞座”。先說“委座”,這個稱呼在抗戰期間出現得較為頻繁。舉兩個例子,一例是南昌會戰期間,薛岳發給陳誠的電報中提到“現迭奉委座電令”之語。另一例出自戴安瀾日記,有一次他在緬甸迷了路,見到有車駛來以為是當地英軍,便將車攔下。戴安瀾上前用英語問路,結果車中下來一位國軍同僚,見面就說:“老戴,你發什么瘋?此乃委座乘車也。”兩個例子的不同之處在于,薛岳發的屬于正規的電文,戴安瀾日記中的場景則屬于生活日常,兩處皆出現“委座”稱呼,可見是國軍將領對蔣介石比較普遍的尊稱。顧名思義,這個稱謂是根據委員長一職而來,在抗戰勝利后就不用了。
“鈞座”就是另一碼事了。“鈞”是古代的重量單位,衍生為敬辭,也就是說“鈞”和“座”兩個字都不是指職務,這一點和“委座”有很大區別。1944年8月,衡陽城陷落前夕,國軍第10軍軍長方先覺給蔣介石發出“最后一電”:“職等誓以一死以報黨國,勉盡軍人天職,決不負鈞座平生作育之至意?”其中出現的“鈞座”一詞,用在這里可看作下級對上級的尊稱。接下來看另一例,湖南在驅逐軍閥張敬堯斗爭期間,毛澤東的老師徐特立寫了一封《致張敬堯的公開信》中提到:“鈞座為地方長官,似應一查真象。”這封信至少可以證明兩個問題。其一,“鈞座”一詞不僅是軍中下級對上級可以用,民間人士對軍政人物同樣適用,有點類似古時“大人”的叫法。其二,驅張運動時,國民革命軍還沒有誕生,可知“鈞座”并非國民黨的專利,早在北洋時期就有了,充其量只能說是民國軍隊中常用的尊稱之一,不是什么國軍特色。
無論是第一手的電文、日記、書信,還是回憶錄,像師座、旅座、團座等叫法鳳毛麟角,幾乎不見于記載。至于什么“局座”“處座”之類,更像是導演編劇們腦洞大開的產物。總而言之,國軍中稱“座”的叫法的確存在,但遠遠沒有影視劇中那么頻繁,也沒有那般標準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