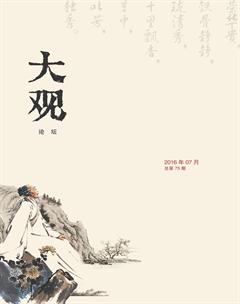博物館陶瓷文物英譯
摘要:本文以博物館陶瓷名稱英譯文本為研究對象,通過對陶瓷名稱結構與翻譯要求的分析,提出翻譯建議或參考譯文,以期實現文物譯名的規范和統一,提高國際游客對博物館陶瓷文物的欣賞和認知度。
關鍵詞: 陶瓷文物;英譯
一、引言
陶瓷作為“物化的文化”,是中國古代文明的集中體現。陶瓷文化作為中國獨特的文化形態,歷史悠久,底蘊深厚,已然成為國外游客了解中國的“名片”和“窗口”。 博物館陶瓷文物承載的豐富的文化信息,是中國文化展示的重要媒介。然而,陶瓷器物名稱英譯現狀卻不盡如人意,英譯實踐在國內尚缺系統的理論指導,陶瓷文物名稱翻譯欠缺規范,出現譯名混亂甚至錯誤,在一定程度上妨礙了中國陶瓷文化的對外譯介和宣傳。
二、博物館陶瓷文物名稱特點及英譯要求
博物館的瓷器文物名稱一般出現在宣傳冊(leaflets)、目錄 (catalogues)、段首解說板(interpretive panels)、標識牌 (labels)以及指示牌 (signposts)等博物館文本材料中。博物館陶瓷文物名稱的信息性非常強,其主要功能是向博物館游客提供所標識瓷器物的主要信息,便于游客識別、理解其包含的文化元素,更好地欣賞展品。
從瓷器名稱的結構看,漢語瓷器器物名稱從結構分析主要由通名和屬性名稱兩部分構成,通名和屬性名為并列結構。通名(通用名稱)指某類事物及其中的一個,表示不同類型的器物,此處的類型主要指造型的分類,例如:琢器類——尊、瓶、罐等;圓器類——碗、盤、碗等。屬性名是名稱的重要組成部分,通常表明器物特點,包括釉彩、紋飾、器形、產地、年代等信息。陶瓷文物名稱的表達更為繁雜,它不但包括一般陶瓷器物涉及的幾個方面,還包括器物的窯口、制作時代等內容。例如: 宋代白釉黑花牡丹紋枕,標明了其制作年代 (宋)、釉彩 (白釉)、紋飾(黑花牡丹)、器型 (枕)。
博物館陶瓷文物展品名稱英譯的目的是要讓外國游客看懂,并獲得中國陶瓷文化相關知識。為使陶瓷文物展品名稱英譯有的放矢,譯者應充分理解翻譯目的與要求。否則,翻譯就成了漫無目的盲目行為。博物館陶瓷文物名稱翻譯要求可設想如下:
(一)譯文的預期功能
德國Katharilla Reiss根據文本交際功能將文本劃分為信息型(informative)、表情型(expressive)和操作型(operative)。其中信息型文本主要提供“純粹”事實,目的是將信息傳遞給接受者,語言邏輯性強[1](108-109)。陶瓷文物名稱的信息功能指名稱主要介紹陶瓷的類型、釉彩、紋飾、年代等方面的相關知識,應以信息型文本為主。由于陶瓷文物名稱英文譯文的讀者大多為外國游客,他們主要是想了解有關旅游地的實用信息,所以譯文更側重信息功能。
(二)譯文的預期讀者
譯文的讀者是來中國旅游觀光的國外人士。根據Newmark對讀者的分類方法[2] (15)陶瓷文物名稱英譯的預期讀者可以分為三類:學者型讀者、受過良好教育的普通讀者、受教育程度不高的讀者。無論哪種類型的譯文預期讀者和原文讀者相比,他們的認知結構缺乏有關中國語言、文化和社會等方面的預設知識,這就要求譯者對譯文進行適當補償操作,如補充相關背景知識,作解釋性翻譯等。另外,由于譯文和原文的交際環境完全不同,原文中的某些內容如果直接移植到譯文,可能和譯文讀者的文化期待相異,有可能產生價值觀沖突,從而影響譯文的可接受性,所以譯文應盡可能順應譯語的文化風俗習慣。
(三)譯文的傳播媒介
原文和譯文的傳播媒體一般是博物館文物、宣傳畫冊,大多圖文并茂,外國游客能從實物和精致的照片中領略到陶瓷文物的美。因此譯文要盡可能簡潔、清楚、不宜過長,任何對預期讀者無用的多余信息都應該刪除,這也正是譯文需要強化信息功能的原因。
(四)譯文的要求
由于東西方文化的巨大差異,英漢兩種語言形成了各自不同的特征。漢語詞匯表意,句法結構松散,是意合語言(parataxis);英語形態表意,句法結構嚴謹,是形合語言(hypotaxis) [3](62-64),加上兩種語言的詞義不對等、文化背景差異等因素,給陶瓷文物名稱的音譯帶來巨大挑戰。另外,博物館陶瓷文物名稱有空間限制,需考慮游客的閱讀環境,因此源語言信息應當重新整合,突出重點、便于游客在較短時間內獲取信息。從心理學角度上來講,顏色、形狀是游客遠觀文物最先獲得的信息,因此,英文中應將此類修飾語前置,紋飾、工藝等可用With結構綴于通名之后。年代和產地信息可單獨分離換行,避免譯名過長,達到有效傳遞信息的目的。
三、博物館陶瓷文物名稱英譯實例分析
目前,平頂山市共發現唐、宋、金、元時期各類窯口一百多處,其中魯山段店窯、寶豐清涼寺汝官窯、汝州張公巷窯是平頂山市的典型代表。平頂山博物館展現了陶瓷文化的璀璨歷史。遺憾的是,館內陶瓷文物英譯情況不容樂觀。茲將一些英譯文本,擇要評點,以供商榷。
(一)瓷器文物名稱組成部分翻譯
1.器形的翻譯
隨著中國陶瓷制作工藝的不斷發展,陶瓷顯示著特定時期制作工藝的風格和特點,器形是瓷器式樣傳承演變的直接反應。瓷器名稱通名下的眾多子分類通常都表明式樣繁多瓷器的器形,其名稱起源、用途不同,譯時需謹慎。例如:二里頭文化中的“觚(Gu Vessel)”,恐怕部分中國讀者也不知此為何物。觚是漢族古代一種用于飲酒的容器,盛行于商代和西周,圈足,敞口,長身,口部和底部都呈現為喇叭狀。音譯在某種程度上有利于傳播中國文化,但需要加注外國游客才能知道其真實含意。不妨譯為“Gu,Pottery Wine Vessel”。同樣,陶豆(Pottery Dou Container)、黑釉盂(Black Glazed Yu Vessel)、白陶鬶 ( White Pottery Gui Cauldron)罐形鼎(Jar-Shaped Ding)中,盛器盂和豆、炊具鬶和鼎,在英譯中都應有所體現。故將上述譯文試譯如下:
陶豆 Pottery Dou, Food Vessel
黑釉盂 Black-glazed Yu, Water Vessel
白陶鬶 White Pottery Gui,Cooking Vessel
罐形鼎 Jar-Shaped Pottery Ding,Cooking Vessel
在瓷器命名中,屬性名中也可出現表明器形的詞匯,如花口、八角等,具體描述瓷器的細節形狀。對于此類信息,應核對實物,確認指示的器身的具體位置,選擇相應的詞匯表達。例如:花口(指磁器口為花瓣狀)——with Petal-Shaped Mouth,花口碟應為Dish with Petal-Shaped Mouth,而不是Dish with Flower-shaped Mouth。
2.釉彩的翻譯
中國瓷器釉彩的發展,是從無釉到有釉,是從單色釉到多色釉,又由釉下彩到釉上彩,逐步發展成釉下與釉上合繪的五彩、斗彩等[7](29-33)。從翻譯的角度看,顏色的認知是中西方讀者共有的,單色釉的譯法擬采用直譯,如:黑釉、白釉、綠釉、黃釉直譯為Black-glazed、White-glazed、Green-glazed等。
青釉作為中國瓷器主要釉色之一,始見于商代中期,以汝窯青瓷最負盛名。宋徽宗指天為色,“雨過天青云破處,著般顏色做將來”,說它的青色仿佛雨過天晴后的明朗天空。汝瓷以釉色取勝,基本色調為青色。但是,除了天青色以外,還有天藍、月白、豆青、粉青等。這些復合的釉色是以中國人常見的事物形容的色彩,翻譯時需要考量。直譯可能導致讀者因為地域文化差異而影響理解。例如:沒有釉色常識的中國游客尚且難以辨別的天青釉、天藍釉、豆青釉三種釉色,被譯作Light Sky Blue Glazed 、 Sky Blue Glazed、 Light Bluish Green Glazed 。外國游客就更難分辨這三種色彩。因此,我們可以采用漢語拼音加英文注釋的方法命名這類釉色。這樣對陶瓷文化感興趣的游客可根據英文注釋或學習陶瓷相關知識深刻的認識釉色,普通游客可通過文物領略陶瓷的釉色之美,簡潔的拼音也將作為新的詞匯逐漸被接受。例如:三彩由原來的Tri-color ,發展到現在的Sancai與Tri-color兩種譯文并存。另外,對于流傳西方較廣的釉彩名稱,應盡量保存已被西方讀者接受的譯本,遵從約定俗成原則。
3.紋飾的翻譯
陶瓷的裝飾花紋、圖案,不僅題材豐富、技法巧妙,而且“圖必有意、意必吉祥”,是展現陶瓷文化的重要窗口。絕大多數紋飾是中國獨有,如:牡丹紋、菊花紋,典故圖案或詩詞等寓意吉祥,展現當時的文化生活。由于英漢文化語言差異容易導致詞義空缺或文化確性問題。例如:珍珠地“齊壽”字瓷枕,了解文化背景的中國人對這兩個字的寓意非常熟悉,它們表達了長壽的意愿。而西方游客卻缺乏了解,因此,譯文應適當彌補目標讀者缺失的相應文化背景,要盡量將其具體事物所指代抽象寓意翻譯出來。該例可翻譯為Procelain Pillow with “Qi Shou”(indicating longevity)on Pearl-patterned ground。
4.年代和產地的翻譯
陶瓷的產地和窯口一般被視作補充信息,為了方便目標讀者在閱讀時獲取有效信息,可將該信息獨立整理換行標注。對于地名、朝代或年代直接音譯,以便西方游客在熟悉的時間體系產生時間概念。另外,年代和產地信息單獨分離換行,更符合信息文本簡潔的特點,達到有效傳遞信息的目的。為博物館游客減少每行的信息量,使其在瀏覽過程中迅速讀取有用信息。
(二)譯文不統一
博物館內文物英文表達需統一規范,同一器型用相同詞匯翻譯,相似展品用相似的語言表達;譯文提供信息與中文提供信息一致。但是,博物館中文物的英漢名稱存在諸多問題。例如:陶豆(Pottery Dou Container)和觚(Gu Vessel)同為容器,卻北分別用“Container”和”Vessel”表示;白釉和白瓷應為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白瓷盞被譯為“White-glazed Cup”, 白瓷燈被譯為“White Porcelain Lamp”;珍珠地“齊壽”字瓷枕中“齊壽”二字英譯為“Shou Qi”。
為了便于外國游客了解陶瓷文化,不但具有相同特點的文物在同一博物館譯名應統一,相同文物在不同博物館的譯名也應統一,與已有標準保持一致,即遵循約定俗成的翻譯原則,以期逐步統一、規范中國陶瓷文物英譯。
(三)文字錯譯
調查中,筆者發現陶瓷文物名稱中存在多處文字錯譯,比如:白釉黑花“忍”字碗(White Glazed Jar with Foral Design In Black and Inscription “ren”)的翻譯中,器型“碗”譯為了“Jar”,黑陶瓶被譯為Stone Arrowhead,完全風馬牛不相及;“珍珠地劃花腰園形枕”被寫成“珍珠底劃花腰園形枕”和珍珠地牡丹紋枕同時出現,并且英譯都采用了over a Pearl-patterned ground這一形式,錯誤明顯。
四、結語
博物館陶瓷文物英譯雖然不同于文學語篇的翻譯,但同樣存在美學標準和文化觀念的問題,同樣需要思考文本的功能特征和翻譯策略、形式和內容的關系,也同樣需要完備的理論知識和翻譯技巧。因此,博物館陶瓷文物的翻譯應該把握其特點,以游客獲取信息為目的,根據博物館陶瓷文物名稱的翻譯要求和譯文讀者的對象,采取適當的翻譯策略,突現信息功能,達到文化交流之目的。
文物英譯不僅是翻譯問題,更關系到一個城市甚至一個國家對其歷史史實的尊重,涉及城市形象、文化交流等。博物館建設是城市重要的文化活動,文物展品英譯問題不可小覷。從文中可以看出,翻譯時,如果譯者多一分責任感與使命感,諸如選詞錯誤、拼寫錯誤、不一致等都可以避免。誠然,本文的觀點存在一定的片面性和主觀性,希望同行專家批評指正,也希望引起相關部門重視,共同促進博物館陶瓷文物英譯的統一與規范。
【參考文獻】
[1]Katharilla Reiss. Text Types, Translation Types and Translation Assessment. Readings in Translation Theory. Ed. Andrew Chestreman. Filand: Oy Finn Lectuta Ab, 1977/1987.
[2]Newmark, Peter. A Textbook of Translation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3]趙善青.漢英語言的意合與形合[J].青島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09(2):62-64.
作者簡介: 王潔輝(1979- ),女,河南舞陽人,平頂山學院副教授,研究方向:翻譯理論與實踐。工作單位:平頂山學院。